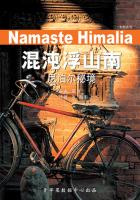通往瓦切的路正在修整,漫天的灰尘弄得人灰头土脸,于是大家看风景的兴致逐渐减弱,都窝在车里昏昏欲睡。正在迷糊中,不知道谁突然哇了一声,一声惊呼惊醒梦中人,大家都睁开眼睛,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红的、黄的、蓝的、白的经幡,铺天盖地扑进眼帘,经幡背后有白色的塔尖耸立,有金光闪烁的屋顶若隐若现,经幡在风的鼓动下,一齐唱着雄浑的颂歌,在空中舞动飘荡。那里,就是瓦切,那,就是瓦切的经塔林!
一行人不待车停稳,纷纷像兔子一样拉开车门,蹿向塔林。铺天盖地的瓦切塔林,由无数座帐篷式的经幡塔组成,每一座经幡塔又由无数的经幡条组成。一页页经幡、一根根经幡条、一座座经幡塔,仿佛一座座巨大的帐篷,绵延不绝站立在大地上,像一座彩色的城,又像一座复杂的迷宫。这些五彩缤纷的经幡,在风中不断舞动,在我们视野里跳跃。印着经文的经幡,直接把我们带回到传说中去。据说当年佛祖坐在菩提树下,手持经卷闭目思索,忽然一阵大风刮来,将佛祖手中的经书席卷而去。经书被风撕成千万片随风飘散,许多遭受苦难的人,突然被天空中飘洒下来的经书碎片击中,所有得到佛祖经书碎片的人从此都得到了幸福。人们为了感谢佛祖的恩赐,便用彩布印上经文和佛祖的像,把它挂在风吹得着的地方,让风替自己吟诵祈福,保佑自己及家人平安健康。
瓦在藏语里为帐篷,切就是大,因此“瓦切”就是大帐篷。在当地牧民中,流传着这样一个美丽的传说:藏族英雄格萨尔王征服了大小列国以后,从岭国向东前往汉宫,来到瓦切附近,被两个妖魔挡住去路,于是双方展开大战,格萨尔王最终施法将两个妖魔击倒,并唤来两只乌龟天将负责看守。为了使妖魔永世不再兴风作浪,这一大一小两只乌龟各负责压住一个妖魔,久而久之,两只乌龟变为两座小山包,好似两顶帐篷静静卧在那里。于是人们便将大的山包叫做“瓦切”,小的山包叫做“瓦穷”,随着光阴流逝,瓦切就渐渐成了这里的地名。
我和芝麻一起走进塔林,经幡深处隐藏着一个小小的院落,院落被无数的白塔围合,走进院子,里面有两个小殿堂,三层重檐如宝塔般耸立,但是殿堂只有一层,空间非常狭小,人也无法上去。走出院子,塔林四周摆满了“擦擦”,它们很可能是前来祈福的藏族同胞临时制作的,“擦擦”上面无一例外地印着不同姿态的佛像,这引起了我们的强烈兴趣,忍不住一个一个仔细看过去。据说“擦擦”是来自古印度的方言,是藏语对梵语的音译,意思是“复制”,就是用模具统一印制出的泥佛或泥塔。我此前曾在藏地多次出入,知道除了眼前的泥擦,藏地还有比较稀少的骨擦与布擦,骨擦是用圆寂活佛、高僧的骨灰混合泥土制成,因其成分中有骨灰而得名。而布擦则更为稀有,藏语“布”意为法体,根据藏传佛教仪轨,历代达赖喇嘛、班禅大师及少数大活佛圆寂将实行塔葬,塔葬之前,须将大师法体用藏红花等珍贵药品进行脱水处理,脱水处理时流出的大师体液混合泥土制成的擦擦就叫“布擦”。藏地传说,布擦可医百病,可避邪恶,可得平安,甚至刀枪不入,因此人们常将布擦作为护身符挂在身上。
大伙纷纷学藏族同胞绕着经幡塔转。每座帐篷式的经幡塔,中间立一粗大的树干,无数经幡条从树干顶端放射状延伸至四周,酷似一顶顶巨大的帐篷,又像一座座经文覆盖的金字塔。经幡塔下绿草如荫,各种野花竞相盛开,将这些庄严肃穆的经幡塔装点出几分妩媚。从塔下抬头仰望,几丝天光透过经幡条,在地上拼成斑驳的光影,风儿在此处已销声匿迹,只有几只蜜蜂在盛开的花朵间嗡嗡地忙碌。那些高处的经幡在风中舞动,模模糊糊的经文随风翻飞,如我们那些虔诚而执著的旅行梦想,虽不清晰却一直没有消失。一个接一个的经幡塔,如迷宫一样排列在一起,大伙在这迷宫中各自忙碌着,有人在拍照,有人在欣赏擦擦,有人在看经幡上的佛像,有人在看经幡塔下的石刻。
赶上草原赛马会
出红原,车沿着白河在广袤的草原上一路前行。起起伏伏的山头上毫无例外都是草,在天地间拉伸出舒缓柔和的线条,让山也变得柔美。转过一个小小的山头,眼前突然开阔,一片广阔的草原在山谷间绵延伸展,像绿色的地毯,柔软而梦幻地铺展在大地上,清澈的白河缓缓流淌,在草原上划出一道道舒缓优美的弧线,恰似一轮轮弯弯的月亮,这就是有名的“月亮湾”。那些如弯月般的河流,其实是白河留给这片草原的遗迹,其实它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河流,它们早已成了静水湖泊,只能被称做牛轭湖或者月亮湖。
一群人在绿草与野花丛中随意地释放着自己,有人躺在山坡上晒太阳,有人摆着不同的造型忙着拍照,有人在采摘漂亮的野花,有人在山坡上打闹嬉戏,有人面对白河对岸的月亮湾静静发呆。站在山头远远望去,河对岸的草原上,羊群在绿色的草地上移动,黑色的牦牛群在悠闲地吃草,马儿在草地上轻快奔跑。夏日的清风徐徐吹来,将山头上的隆达轻轻卷起,在空中打几个滚,又轻轻落下,重进草丛。这些印着飞马、虎、狮、鹏、龙等图案的隆达,也叫纸风马,是当地藏族老乡路过此地时,撒向空中祭祀而留下的。它们层层叠叠躺在这绿色的大地上,卧在野花的怀抱里,静静呵护着这方丰饶的土地。路顺着山势盘旋,车顺着路一直蜿蜒向上,那大团大团的洁白云朵,似乎就搁在山头上,草地上的野花越来越密集,大伙越来越兴奋。翻上一个海拔4000多米的垭口,满车的尖叫变成了“停车”的呼喊,让司机吓了一大跳,刺耳的急刹车声尚未消失,一车人早已连滚带爬跑上了垭口的山坡。没有人想过是否会有高原反应,也没有人担心自己是否会呼吸不畅,因为眼前这大气磅礴的美丽景色,已经让每个人忘乎所以。站在垭口四望,灰白色的公路忽隐忽现,如一条细细的丝线顺着高低起伏的山脊蜿蜒飘浮。远处的大山上绿草如荫,洁白的云团涂抹在山脊上,黑色的牦牛群与白色的羊群星星点点,好似在天空中游牧。回望身后,逆光的云团立体而凝重地挡在垭口与蓝天之间,构成一幅苍茫浑厚的背景。长长的山坡从垭口向下延伸,各种色彩、不同大小的野花仿佛从云团中倾泻而下,滚满整个草地,把草原染成了斑斓的织锦。芝麻与几个女同胞在花海上奔跑跳跃,整个人随风飞舞,尽情放飞在这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花海中,放飞在这纯净的高原阳光里。老杨坐在草地上,默默看着远方。我闭着眼睛,仰面朝天躺在草地上,呼吸着带青草气息、野花香味的空气。还有几个人卧在草丛中,用微距镜头拍摄着不同形状的野花。甜筒则干脆趴在花海里晒太阳睡大觉,每个人都深深在一起,能展示自己与马的速度之美,赢得旁人的赞誉,才是最重要的。如果能得到冠军,将是这些高原汉子一生的荣耀与骄傲。
比赛已经正式开始,随着裁判的哨声响起,10匹一字排开的马儿突然加速,从我们面前掠过,不一会儿就急驰到了草原的另一边。远远看去,那些马儿好似在彩色的海洋上飞翔,马蹄踏碎的野花,又顺着飞奔的马蹄抛洒起来。一圈下来,第一组比赛队伍已经分化成三个梯队,一匹白色的马与它年轻的主人一直冲刺在前,另外几匹异常健壮的马儿组成了第二梯队,其余的则远远被甩在了后面。三圈之后,比赛队伍首尾相接,不仔细看或刚挤进来的人,根本不知道谁在前谁在后。围观的人群纷纷为这些选手鼓劲助威,掌声、口哨声、加油声、呼喊声,一时之间响彻草原的上空,只是跑在第一的那匹白马却后劲不足,渐渐被一匹黑色的骏马超越,任凭它的主人怎么挥鞭始终未能赶上去,一匹黄色的马则直接开了小差,它的主人还没来得及反应,它已经一溜烟离开赛道跑进了草原深处,等被勒转马头重回赛场时,比赛已经完毕,引得众人大笑不止。
一个蹒跚学步的藏族小女孩仰起小脸,在草地上摇摇摆摆,大伙忍不住纷纷想过去抱一抱,小家伙在芝麻的怀抱里竟然露出了笑脸,让我们不禁想起了在远方的小薏米。草原上的比赛依然在热火朝天地进行,只是我们还要继续未来的旅程,看过几组比赛后,我们不得不告别这开满鲜花的草原,告别这热闹异常的赛场。旅途与人生何其相似,不管前方还有什么,他们对于我们,不过是小小的插曲,我们对于他们,不过是不经意的过客,然而这大河蜿蜒、经幡猎猎、鲜花盛开的阿坝,虽踏花归去,却马蹄留香。
年宝玉则,神山不在天尽头
在四川、甘肃、青海三省交界的高寒草原深处,有一座尚不为大多数人熟知的神山——年宝玉则。翻过一个海拔4000多米的垭口,一排犬牙交错参差不齐的山峰突兀地立在天边,那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年宝玉则。经过连续几天的长途奔波,我们的车队终于来到了年宝玉则脚下。车只能到湖边,要进年宝玉则一号营地、二号营地、冰川和垭口,要么徒步,要么骑马,13个人中有4个选择了徒步,9个选择了骑马,所有人的大背包统一租用了三头牦牛驮运。我、芝麻、老杨、十月背着各自的相机、脚架、水壶、食品等,开始徒步开拔。刚出发我们就遭遇下马威,需要涉水过河,我们每人都只穿了登山鞋,不脱鞋是不可能的,虽艳阳高照,但冰川融化的湖水依然冰冷刺骨。走在河道里,尖砺的石头滑过脚心,一种说不出的疼,让人既不敢快速地跳跃前进,又无法停留片刻喘息。过河上了岸,也不平坦,到处是密布的沟壑,人只能沿着湖边绕行,既要提防虎视眈眈的牦牛,又要时刻警惕不知道会从哪个角落窜出来的藏獒。即便这样的路,也只短短一段,随后便进入沼泽与灌木丛。沼泽地看上去十分平坦,底下却泥水横淌,一踏上去就落入淤泥坑,鞋子湿透不说,脚也会意外崴伤。那灌木丛则更费劲,枝繁叶茂的灌木丛有两米多高,人一进去就看不到影子,几个人只能沿着马道前进,否则一钻进树丛就会迷失方向。有时费半天力气却可能还在原地打转。从马道上抬头,只能见一线窄窄的天空,马道极其难走,水、泥、马粪、大大小小的水坑、高高低低锐利的石头、长长短短的树枝,一会儿需要像猴子一样抓住树枝跃到远处凸起的石块上,一会儿又像青蛙半蹲在原地四处寻找可以落脚的点,然后飞快地连续跳跃找到下一个立足之处,一会儿四肢并用爬上光滑的大石头,又顺着石头溜下去。无数蚊虫云集头顶,时不时一个俯冲,或撞进正在喘气的嘴巴,或被吸进鼻子,或者猖狂地钻进耳朵,又或者不小心弹进眼缝,让人烦不胜烦。不大一会儿,几个人便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而年宝主峰仍是遥不可及。
老天此时却故意开起玩笑,一团墨黑的云飘过来,悬挂在头顶,开始下大雨。回首看去,湖的那边白云朵朵,阳光耀眼,头顶却大雨如瓢泼,噼啪作响,远处云雾茫茫,山影全无。雨里的路更加难走,每个人全身都是泥水,冲锋衣、冲锋裤、登山鞋与普通的衣服已无两样,让人分外沮丧。
年宝玉则是青海果洛草原的一座神山,平均海拔4800米,最低海拔为3568米,最高海拔为5369米。它是长江黄河流域的重要分水岭,其西与南为长江水系,东面和北面则属黄河水系。年宝玉则的神秘,莫过于变幻莫测的天气,现在应是酷热难耐的季节,在这里却能领略春夏秋冬四季变迁。常常夜里满天星斗凉爽无比,凌晨却大雪纷纷寒气逼人,等到清晨一轮红日却从东方冉冉升起,不到片刻整个山谷浓雾弥漫云蒸霞蔚,日出一小时后,金色的阳光洒满大地,再过两小时又浓云密布,顷刻间下起倾盆大雨;等到正午时分,云开雾散烈日炎炎,才让人回到盛夏的酷暑季节;可在午后不久,却突然狂风四起,雷鸣电闪,冰雹从天而降。待到傍晚时分,夕阳西下,整个山谷恢复宁静,主峰往往也会在这个时刻揭开神秘的面纱,婀娜多姿地出现在世人面前。
几个人在山坡上上上下下,忽左忽右,忽前忽后,体力消耗非常严重,好在大雨持续时间不长,远远地望见其余9人的马队正在向我们走来,我们又鼓足信心,继续前进。不久,9人马队和马夫一起,赶着三头驮着公用装备与物资的牦牛赶上了我们,骑马的人看到我们的狼狈样,居然还说骑马比走路吃亏,令我们四个走路的人义愤填膺。不过好在走路可以走走停停,看到美景能尽情拍照,令一堆骑马的人羡慕不已。3个小时后,我们几个徒步的人终于走到仙女湖北岸,路变得平坦而干燥,主峰上的冰川在眼前高耸,整个峡谷中,以山谷冰川与悬冰川为主,冰雪融化后,在雪峰周围的山谷中汇成大大小小360多个湖泊。雪山镜湖辉映,绿草茵茵繁花如梦,牛羊和马群散落山谷,宛如人神共守的净土。嶙峋的峰林倒映在碧蓝的湖水中,仙女湖与妖女湖之间的草地上,铺天盖地的野花肆意地怒放,五颜六色的花朵小的如米粒,大的如半个手掌,单瓣的、簇团的、椭圆的、不规则的,一齐在视野里舞蹈,华美得令人窒息。如此壮美而绚丽的花海,自然让人不忍踏上去,和芝麻一起脱下鞋子,摆在石头和花海里拍了照片,权当是这次徒步的纪念。在温暖的阳光下,几个人到底没抵御住诱惑,疯狂地跑进花海,打滚、拍照、发呆,后来干脆什么也不做,头枕着双手,闭着眼睛,睡在花儿铺成的地毯上,静静地聆听着阳光温柔地抚过大地。几只土拨鼠悄悄从窝里溜出来,直立着身子,站在高高的土堆上向我们偷望,然后相互侧头互视,好像在议论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