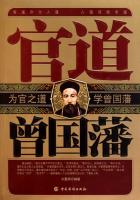看着柳因风逐渐恢复清明的眸子,我悬着的心慢慢落回原地。倘若他一直这么痴傻呆愣着,估计只能再叫晔清出手了……
想到晔清,我不禁抬头四顾,发现他不知什么时候出了屋子,此刻正倚在树下。身子倾斜,背靠着树,腿支在地上,与树之间形成好看的弧度,下巴微扬着,唇角也牵起,一派恣意率随。
“咳!”一声轻咳将我思绪拽了回来,就见颜钰朝我挤眉弄眼,笑的促狭。
我一副正常无比的样子将目光重新聚集在柳因风身上。
“若絮,若絮……”他嗓音嗬嗬嘶哑,断断续续,目光渐渐清明。
“柳因风?”我试探一声。
他缓缓转过头,目光渐由涣散聚集在我脸上。轻吁一口,果然有反应了。
“你是?”足有一盏茶功夫,他才出口问道。
看他这样子,我也没指望他能记住我,“坐下谈,坐下谈。”
将他拉到椅子边按坐下去,左手取了茶杯,右手执了茶壶,哗啦啦,一杯茶便倒的正正好好,多一分则溢,少一分则亏。不经意间指尖状似如常的在杯身摩挲了一圈,将茶杯送至他右手侧桌子的边沿,不多一寸不少一寸,正正好好的卡在桌子的边沿。
“喝杯茶,润润嗓子吧。”我坐在他的一旁。
他迟疑片刻,道,“不了,谢谢,我不渴。”
我扯开笑脸,温温柔柔,“你还是喝几口吧,这里是哪,想必你也看清了吧。既是请你来喝茶,那便免不了要说的口干舌燥,喝几口,总归没有坏处不是?”
柳因风轻蹙眉头,看来是完全清醒过来了,果然,“方若絮”三个字,比“柳因风”更好用么。
他看了我片刻,“如此,多谢。”
便伸了手去拿那茶杯。
“啪啦”一声,茶杯落地,温热的茶水浸湿了他的衣袍。
我凝眉,意料中的打破了茶杯,但心底有种说不出的失望和放松。
“真是不好意思,刚刚没拿稳。”他神色如常。
先头我说了,不管是分尸还是抛尸,都是体力活,当然这不排除若是凶手精通人体肌理脉络或许出的力气会小一些,但总的来说,力气那是万万少不得的。
方才在茶杯上摩挲了一圈,便暗暗将一个斧头的重量加到了茶杯上,卡到桌子边沿,让他不至于完全拿不起来。
结果显然易见,柳因风他没拿起来。
失望是他力气不够,十有八-九他不是凶手,放松也是他力气不够,十有八-九他不是凶手。这样或许有些矛盾,但一个有着大好时光的青年若真是如此残忍的凶手,真是……
可是他的表现又是可圈可点,没有丝毫讶异,堪称波澜不惊,这又不禁令人怀疑,他是真的没拿起来,还是假装没拿起来,还是他行事本就如此如此镇定异常?
“没关系,重新倒一杯就好,柳因风,”我顿了顿,“还是叫你柳公子吧,你衣服湿了,不然去换一下?衙门应该能找到适合你的衣服……”
“多谢好意,不用了,我穿不惯旁人的衣服。”
“那,你这衣服湿着……”你这身子如此单薄,病了怎么办……
“无妨。”
我那后半截的一串话,直接被他干净利落的两个字扼杀在喉咙中……还真是不客气。
如果不是必要,真不想同他说话,晔清都比他好说话!
气氛有点尴尬,但我就是不想理他。
“不知阁下请我来有要事?”没事的话我就走了。
读懂他的潜台词,一股怒气在五脏六腑四处乱窜。奇怪了,平时我可不是如此暴躁的。
秉承着良好的素养,我还是……比较尖锐的问,“叫我予婳便可,不知柳公子同方若絮是什么关系?”
“方若絮?不认识。”
妈的,我忍不住要学颜钰骂人,老娘刚刚用“方若絮”三个字治好你的痴傻呆愣的病,病好了这下就翻脸不认人?!就连一旁的颜钰也开始咬牙切齿准备骂人了!
“不认识,呵呵呵,”我挤着脸笑着,“那柳公子看看这幅画是出自谁手?”说着便将最早前的那张方若絮的画像递了过去,上面“柳因风”三个大字,总不能抵赖吧。
他接过去瞧了半天随意道,“不知多少年前的戏作了。”
完了?这就完了!
柳因风字画的一大特点就是没有题字,或寥寥几笔的几句话,还有角落里的名字,至于作于何年何月何日连提都没提一下,是以这画到底是他什么时候作的完全不可考,完全就是他一句话的事。
“那这画上的人你总该认得吧。”
他又将画执起,遮在眼前,以我的角度看过去,他好似在细细欣赏着自己多年前的得意之作,然却没人瞧得见他眸中深深的眷恋之色,“记不大清了,应该是长寿县里的人。”
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嘴硬的很啊。我只得又将那幅柳絮翩飞的图拿了出来,“那这副呢?”
或许他与方若絮只是普通朋友泛泛之交,或许只是点头之缘,但这景这字,再配上二人的名字,让人不多想都难。
这次他没了什么耐心,简单扫了两眼便道,“阁下找我来到底有何事,仅仅是叫我来欣赏我早年旧画?”
话中不客气之意十足十,连我的名字都不叫!这个柳因风还真油盐不进,有个性得很啊。
“既然如此,”我定定看向他,“咱们也没必要兜圈子了。清风楼的方若絮,想必柳公子应该不陌生吧,别说什么你不认识他,将自己裹得脸如此密实,我理解,翩翩佳公子去那种地方总会被人说三道四。但是若絮他并不接客,他是堂堂正正的以自己的才华营生,没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也不愧对任何人。”
一想到那幅方若絮的画,心头便有些怜惜这个冰雪般的青年。柳因风一定是对他熟悉至极,才能将方若絮那独特的气质,透过画纸,准确的传递出去。
他愣了愣,唇角微不可查的抽了抽搐,拳头缩在袖中,狠狠的握着,指甲深深掐入肉中。
许是我的话太长他有些反应不过来,许是我的话触动了什么,他眼底有些动容,深深呼吸,轻叹一口,“我与若絮,彼此欣赏。”
精简的八个字,却裹涵着无数的信息。
默了片刻,他继续,“若絮他,不是被赎走了么?”
“你信?”
“……我不想信。”
这么说,他就是不信了。
“还记得你是如何来衙门的么?”
“……不记得。”迟疑的语调。
“那你是怎么了?”
“不知道,这些天总有时候浑浑噩噩,好像没有任何感觉。”
“这症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大约……小半月前?记不清了。”
小半月前?这么巧?
“为什么不卖扇了?”
“太累了,不想卖了。”声音带着丝疲惫。
“这些天都在干什么?”
“……不记得了。”
“什么意思?”我愕然。
“有时候觉得身体不是我自己的,有时候好像是在睡觉但好像又是醒着的……”
这是他目前为止说的最长的一句话,然,我完全不明白他在说什么。
“你的意思是,”我尝试理解他的话,“你的身体不受你控制?”
他缓缓点头。
“你一直住在巷子里?”
聪慧如柳因风,一下子就明白我的意思,“嗯,虽然那地方偏僻简陋,却正是胜在它偏僻。”
说的跟绕口令一样,我却一下子明白了。依他那冷淡的性子,住的偏,才叫一个爽快自在。
“那么你与方若絮……”
这次他善解人意的接过了话头,“我与若絮互相欣赏,琴棋诗画,他样样精通,我去清风楼寻他,大多时间,不过是他奏曲我作画。”
叫了两个衙役将柳因风送回去,聪慧如他没有拒绝。我嘱咐那两个衙役务必将柳因风安全送至家门口。
这厢我还在苦思冥想柳因风话中的真假,那厢名为“护送”实则监视的两个衙役不过片刻功夫就将柳因风送到了那四通八达的巷子口。
“劳烦二位了,剩下的路就无需相送了。”
“那怎么行,公子特意嘱咐过一定要将柳公子送到家门口,柳公子身体如此虚弱,若是这半途出事了,公子可要赖上我们了。”
“公子?”
“对啊,就方才一直跟你说话的那个。”
“如此,便麻烦二位了。”
“不麻烦不麻烦,不过几步路而已。”
于是乎,这两个衙役亲眼看着柳因风进了自家的大门,才离开。
柳因风在门里静静的听着,待脚步声远去再听不到,才将门打开,步入巷中,七拐八拐,钻进一个角落,步伐娴熟,显然是经常来此。
他抬手轻扣墙面,“笃笃笃”三声不甚沉闷也不甚清越声音静静响起,传到墙的另一头。
“如何?”片刻后,墙那头传音过来。
若叫别人看到定会诧异不已,巷中的墙就算再薄,也不至于将墙两面的说话声传递的如此清晰。
“照你的吩咐,一切正常。”柳因风淡淡的答。
两人对话,即便是柳因风听命于墙另一侧的人,可那语气丝毫不显自己低人一等。
“那就好。”
半晌,柳因风这边没动静,也没有脚步离去的声音,墙另一边又出声,“有问题?”
“……没有,”柳因风迟疑片刻,“你不是说……那个人是女子么?”
很快,回答传过来,“不该你管的事不要多管,记住,知道的越多,死得越快。”
脚步声渐渐远去,柳因风抬手轻抚了下墙壁,唇角勾起冷冷的弧度,嘲哂一声,大步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