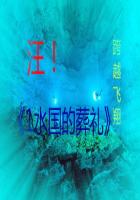神秘的柳因风,古怪的缠雪,失踪的宋郎中,接二连三死去的万家家仆,城门上悬着的剑,树上挂着的麻袋,缺失的手指,挖去的心脏……一个个疑问在脑海中飞速的闪过,令我应接不暇。
仅仅凭一幅画作,我就揣测柳因风与这起案子有关系,是不是我太武断了?可他的行为举止的确又处处透着不正常,令人怀疑。
宋郎中到现在还没找到,是不是已经遭遇不测了?
缠雪说总有一个人裹着严严实实的去找方若絮,这个人是谁?脸都不曾露过一下,真的是因为觉得逛花楼没面子么?如果是这样,那到底是什么引诱着他一次又一次的去清风楼?是仰慕方若絮的才华还是倾慕他的为人?
一系列的事情看似没有线索,可处处又透着破绽。凶手就像一个任性的孩子,躲在暗处和我们玩着躲猫猫,每当觉得案情没办法继续时,就会有看似不相关的小事情发生,比如柳因风的那幅画。
我从不认为这世界上所有事情的发生都是偶然,一切的偶然,就是必然。此生遇见的所有人,发生的所有事,都不是毫无理由。“若无相欠,怎会相见!”司命星君如是说。
万千世界若什么都随心而为,这个世界大概早就乱套了,除非是司命星君琼露喝多醉了出错,而这个时候就需要司命星君及时拨乱反正。但这种情况大概千年难遇,毕竟这是他的司职么,若这些事都做不好,早就该收拾铺盖走人了。
东想西想的想了这么多无非就是要说服自己不要乱,所有的一切都是有迹可循。我堂堂一届前仙女,还怕区区一个凡人?
啊,可是好乱,好烦,好难啊。
要是晔清在就好了……
然后晔清就出现了……
风掀起他月白的袍角,精秀的碧纹隐约其中,偶或间一闪而过的绿芒。唇角勾着浅笑,眸中星芒流转。他身后的小路一下子无限延长、模糊,所有的一切都成立他的陪衬,包括他身旁的颜钰。
“大人!不好了,出大事了!”一个衙役慌慌张张的跑进来,见只有我在,愣了两愣,“大人不在?”
我自桌上拈起一张纸条递给那衙役,衙役却嗫嚅着,“公,公子,小的不识几个字……”
我只得收回手,念,“因昨日腹中绞痛,浑身乏力,是以今日所有之事均交与公子处置。”
先前就晓得这长寿县县令是个不靠谱的主,却没想到已经不靠谱到如此“惊艳”地步。这纸条一瞧就是今日现写好放下的,除非他昨日就以今日的口吻写下纸条。
衙役见状双手抱拳单膝跪下,“禀公子,出,出大事了!”他颤着音,打了个哆嗦。
“怎么了?”
“城,城门口发现,碎,碎尸……”
“什么!”
城门口现在已被好信者围的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
此刻已快到巳时末,正值人流量最多的时候。
费力的拨开人群,就见城门守将几个努力的将人群与抛尸的地方隔开。领头的见到我几步跨上前,抹了把头上的大汗,秋高气爽的天气,却是满头大汗,围观群众的实力可见一斑。
“公子,您可算来了!”
“先将尸体搬回衙门,余下的话等会再说。”
在衙役与守将的一同推搡威胁下,好容易在人群中冲出一条路,将那一大兜黑布包着的东西带回了衙门。
经过人群时,听到他们议论纷纷。
一个道,“你看着了么?”
“没看到!听说血腥的狠,身子都被切的一块一块的,我不敢看,怕晚上做噩梦。”
“你听说了没,据说咱们县这几天已经死了好几个人了!”
“什么!我怎么都不晓得!凶手还没抓到?”
“这肯定是没抓到了,不然这死人是怎么回事。”
“这个也是同一个人杀的?”
“不然呢,我觉得就是一个人,哎,也不知最近是怎么了,感觉县城不太安全,我准备带上我的婆娘出去避一阵子……”
“这么严重?说的有理,那我也出去避一避吧……”
回到衙门只留下了几个管事的守将,余下都叫下去喝杯茶歇歇脚。
“怎么回事?”我抿了口茶,润了润有些干燥的嗓子。
“具体怎么回事我等也不清楚,兄弟几个照例守着城,查来往人的通关文牒,就听一阵骚动喧哗,赶过去一看就瞧见这么堆东西。”
他称那黑布里的包着的东西为“东西”一点都不过分……这大概是我活了千年来见到的最难以置信的残忍画面了。
黑兜子一解开,便是被肢解的乱七八糟的胳膊腿身子头颅。浓重的血腥味猛然钻进鼻腔,令人作呕。
实则,我也的确是呕了。
连颜钰都不忍的别过了头,而晔清仍是一副外人在我自淡漠的样子。
若说比这更血腥更腌臜的场面我也不是没见过,毕竟在忘川河里漂了这么多年,没经历过点腥风血雨那还能有脸说自己在忘川河里混过么。
只是那里是没有善恶之分,没有情谊可言,只有弱肉强食,只有你死我活的忘川河,而这里却是活生生的凡间。
这个凶手在杀这些人的时候,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哆哆嗦嗦犹犹豫豫下不了手?亦或是干净利落冷酷无情的挥刀斩下?害怕无比亦或是残忍无比?
纵然我已经活了很久很久,今后仍要活很久很久,可不代表我对生命的漠然。不然我早就不知被哪知水鬼游魂拆吞入腹了,哪还有现在的我?
“残忍,丧心病狂!”颜钰怒骂,“抓到凶手一定要对他施凌迟,叫他体会一遭什么叫千刀万剐!”
那守将也不知不觉握紧了拳头,将手指捏的咯吱咯吱作响。
“来人!将东……死者抬下去,命仵作验尸,查查死者身份。”我看向守将,“这么说,你没看到是谁抛的尸?”
“予婳!”没等守将回话,颜钰怒向我,“你怎么能这么冷静!”
我淡漠的看了他一眼,他应该是想说“你怎么能如此冷漠”,晾了他片刻,“不然呢,向你这样悲天悯人,愤怒狂躁,凶手就主动出现在你面前了么?”
他一愣,不在说话。
我瞧了眼呆愣的守将,他回过神来,开口,“没看到抛尸的人,这个时间段正是人来人往最杂乱的时候,若不是人群中出现骚动,怕是我还不知此事。”
想着方才人群中那几个人的交流,压力不禁更大,民心不稳,城之将乱!
“现场就没有什么古怪的人?”问这话,我也不抱有什么希望,毕竟那乱成一锅粥的场面,没有人趁机生事已经很不错了。
果然,那守将答,“没能注意到。”
凝眉轻叹,在场的所有人眉头皱的都跟一座小山似得。
一时间,沉默竟然开始蔓延。
不是没有问题要问,只是突然觉得无从问起。
我想问,城墙上那把剑留下的窟窿有没有线索,想问城外树上那么明显的地方为什么没能发现麻袋,就像今天,为什么连这么显眼的大黑袋子躺在城门口不远的地方,都没能发现。
然,问不出口。
寂静中,稚嫩的童声在围墙外响起,俏生生的唱着:大兔子病了,二兔子瞧,三兔子找药,四兔子熬……
带着奶声奶气的童音此刻却有种说不出的毛骨悚然,心惊肉跳。
一个激灵自脚尖蹿起,大脑不受控的跟着唱了下去……九兔子坐在地上哭,十兔子问他为什么哭,九兔子说:五兔子一去不回来……
童声结束,思绪却没有结束,脑海中有个声音继续唱了下去:大兔子病死,二兔子惨死,三兔子逃跑,四兔子吓疯,七兔子断手,八兔子瞎眼……
“是宋郎中!”我猛然站起突然出声,这绝对是最惨的死法了。
一众人被我突然的动作都吓得一愣。
“什么?”颜钰问。
“死的是宋郎中!”
这时门外响起了匆匆的脚步声,仵作惨着张脸进来,微一弯腰,拱了拱手,递过整理好的尸格。看着他那苍白的脸色,我有些于心不忍,毕竟这样血腥暴力的场面,不是谁都能接受的,但他是仵作,这是他的责任,是他的义务,死人不能说话,他就是替死人说话的人。
“说说吧。”我坐下来,揉揉眉心。
“经核实,死者宋年,生前是一名郎中。”
“给万银看病的郎中?”
“是。”
“继续。”
“经检验,死者死于昨日子时至丑时间,死因为肢体被切断,失血过多。死后被挖去心脏,十只手指均被割去……”
“你是说,这个人被活生生的割去了四肢?!”守将愕然,难以置信。
仵作点头,“伤口不平整,肉上有锈迹,像是被钝了的斧头之类的铁器一点点砍开。”
宋郎中死前,备受折磨。
“但是凶手力气好像不够大。”他补充道。
“怎么说?”
他眼中闪过一丝疑虑,还是说道,“我不是很确定。”
“但说无妨。”
“斧头很钝,因此砍断骨头时,需要很大的力气,有些骨头的断裂处不全似斧头所为,还有鞋印手印,凶手似是极尽了全身的力气,摔打踩折,能想到的方法全都用上了。”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如此惨绝人寰!”颜钰骂道。
守将却皱眉问道,“公子,在下并无冒犯之意,可是您是如何知道死者是宋郎中的?”
“童谣。”我答。
“童谣?”
“方才那几个儿童唱的童谣。”
“那首童谣怎么了?”
我心思一动,“守将可曾听过这首童谣?”
没想到守将竟然摇头,“不曾听过。”
“守将不是长寿县本土人?”
“怎么可能不是!在下是土生土长的长寿县人。”
“那这首口口相传的童谣,守将怎么没听过?”
“真就没听过!”他也来了脾气,为了证明他的话,他扭头问旁边他的兄弟,“你们听过么?”
那几人也摇头,纷纷表示自己没听过。
这是怎么回事?
为何衙门里的人都表示自己从小听到大,而守将他们却根本没听过?想到那孩童对我说的话,那童谣是一个大哥哥教他的。
难道,整个衙门的人都在说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