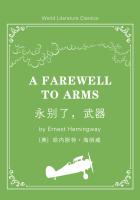在香榭丽舍大道上的一家爱敲竹杠的旅店的遮阳篷下邓菲喝着浓缩咖啡,盘算着如何出境。问题在于边境。克莱姆和他可以搭乘出租来到边境。可过境是个麻烦。邓菲的照片估计已经张贴在法国的任何一个出入境口岸。简单地说,他可以化装。但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在任何情况下,乔装都会让人对企图掩藏的身份深感愧疚。另一个因素就是穿干净内衣,以防万一,假如有人要杀他,他可不想带着难看的假发或者更遭,穿一身穆斯林妇女的装扮死去。现在看来只剩下唯一的一条出境路径。
驾着奥迪A6驱车向南前往美肯,然后东行来到安纳西路行程大约三百五十英里。午夜过后他们乘坐租来的奥迪A6,连夜行驶,黎明前来到桑萨瓦,天边挂着火焰般的云彩,他们已经进入了阿尔卑斯山区,到处弥漫着清新的空气。
寒冷,干爽,晴朗。在安纳西边界的一个工人咖啡店,他们喝着浓浓的咖啡嚼着脆脆的面包,如同刚刚睡了个好觉,顿时变得神清气爽。
早饭后,他们驾车穿过山区来到了日内瓦湖南岸的传奇旅游胜地埃维昂莱班。邓菲租了一个小型套间,站在凉台可以俯瞰下面的湖泊以及周边宽阔的草坪。就在湖的北岸,洛桑与其遥遥相对。
他们入住的是皇家宾馆。邓菲建议克莱姆趁他去城镇的时候去乘船出游或是下水游泳。她高兴地同意了,转眼她就已经裸着身子躺在了浴场,浑身上下裹满了来自死海的泥巴。
邓菲来到附近的港口,想要寻租一只帆船。为防天气有变,他想要一只带船舱的。就在此时,堆积的乌云已像棉花球般聚拢在阿尔卑斯山后。
找到一只介于普通帆船和豪华游艇之间的船有些困难。船要性能稳定,而且便于掌控,这对他来说很关键。他向码头的船商解释说,他可不是瓦斯科·达·伽马类的航海高手,驾着一个J-24型的帆船不会坚持太久。然而他也不想要码头出租的十四英尺长的豪华游艇。他想要一个大一点,能抗暴风雨的帆船。
最后,船商打了几个电话后同意为邓菲租用一只原本用来售卖的一条二十三英尺长的帆船,只是租金贵得出奇,一天一千法郎,外加五千法郎的安全抵押金。不过这船很合邓菲心意。不但大小合适,还有双铺位的船舱,充足的备用帆和自动排水功能的驾驶员座舱。船商问他什么时候需要,邓菲告诉他马上就用。
那人面露疑色。已是下午4时,天空阴云密布,太阳很快就要下山。
“我们想乘船赶往托农,”邓菲告诉他,随便说了一个十英里开外的小镇。
“我们的朋友在湖上有座房子。我妻子想这样坐船过去会更有趣。我想她是对的,我们和朋友毕竟多年未见。”
邓菲匆匆赶回旅馆,看到克莱姆正在温泉浴场,身子裹在一个加热塑料单子里,像一根沾了巧克力的谷物热狗。他说服服务生用软管帮她清洗干净后,拉着她进了房间。
“我们现在要去哪里?为什么这么着急?”她要求道,“我还没有来得及修脚呢。都已经付了费。”
“我们要乘帆船航行。”邓菲告诉她。
“什么?”
“我租了一只帆船。”
她看着他,仿佛他脑子出了问题。“可我现在不想乘帆船出航。”
“我们必须这么做。”
“天已经晚了,”她埋怨道。可看着邓菲主意一定,几乎没有让步的可能,便问道:“你知道怎么开船么?”
“当然知道,”邓菲告诉她,“我可是一名了不起的水手。”
大雨还没有真正下起来。点点滴滴的水花跌进湖面,水纹一点一圈地晕开,形成一轮轮的水晕在整个湖面扩散开来。邓菲拉起船首的三角帆,固定在挽缆柱上。从身前推开舵柄,打开主桅帆。
克莱姆一脸怀疑地看着他。“马上要下雨了哦。”她说。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有个船舱。”邓菲告诉她,“还有面包、奶酪、红酒。放心吧,我们会很安全。这将是一次有趣的航行。”
“马上要下大雨了。”
“你已经说过了。”他说。
“是的,但我想你也一定知道接下来还会刮大风吧。”她停了片刻,然后补充说,“就像传说中的女妖精。”
邓菲坐在驾驶舱内,背靠着舱口栏边,希望事情不会像她说的那样。他正舒服自在呢。“你的根据是什么?”他问道。
“血红的朝霞。”
“哦?”那会有什么含义?
克莱姆摇摇头,“水手都会听取警告的。”
邓菲咕哝着表示接受她的观点。她还在想他们离开安纳西时那个壮观的拂晓。
“现在依然如此。”克莱姆继续说。
“天啊,又来啦。”邓菲咕哝着。
“风若向北吹,渔夫不向前。嗯。”她说着,舔湿了手指,晾在空气中,尽管这没有必要。起风了,方向毫无疑问是从对岸洛桑的方向吹来。“哪里是北?”她害羞地问道。
“真有意思。”邓菲说,船一直加速,开始有点晃动,“哇哦!”他说道,有些吃惊。
克莱姆咯咯笑了起来。“我马上拿救生衣。”她说着,横着身子进了船舱。“我们真应该穿上它们,这湖太大啦。”
不一会她从船舱里钻了出来,已经穿上了橘色救生马甲,手里还拿着一套。把它抛给了邓菲。
邓菲眉头一皱。他可不想自己看起来像个懦夫,但是——哇!船开始加大马力,滑过水面时舱口边翻卷着泡沫,脚底传来轰轰的振动声,船突然开始摇晃起来。也许穿上马甲不是坏事。把舵交给克莱姆,马甲有些小,他费劲地把它穿在了身上。
“我们现在开往什么地方?”风很大,克莱姆不得不提高嗓门问道。
“对岸。”邓菲回答道。
“哪儿的对岸?”
“湖对岸。我可不想过海关。我的照片说不定还张贴在那里呢。”
“所以你想开船到那里——还选择晚上?”
邓菲点点头,“没错,我是这么打算的。”
“很远啊,”她说,“你打算在哪儿靠岸?”
“洛桑附近,”邓菲回答,“而且已经不远了,就在那边。”
“你是说风吹过来的地方?”
“正是。”
“看样子,接下来有罪受了。”
天黑了下来。气温越来越低,雨下得更大。他们依稀看到洛桑的灯光近在咫尺,却似乎又遥不可及。直吹而来的劲风使得邓菲措手不及,船不停地失速,以至于无法行进。
起初,事情只是令人恼火,可情形渐渐开始变得危险。原本黑色的湖面被风吹着泛起一层层白浪。浪越来越大。邓菲吃力地掌控帆船的行进方向。这时船上的感觉如坐过山车一般,不时地失去重心,被抛向空中,接着又被重重地摔了回来。
“开始有点棘手了。”克莱姆说道,语气里的镇定让邓菲颇感意外。她蹲在那里,笑着。水不时地冲进舱口,邓菲则在船头上坐了下来,试图用自己的重量使船保持平稳。
他也不太确定他们现在什么位置。一手掌舵,一手拉着帆绳,雨浇在脸上,顿时眼前一片模糊。船在风雨中不停地颠簸摇晃偏离航向,偶尔也会向前行驶一段。
克莱姆冻得瑟瑟发抖,“水有点刺骨哦。”她说道。
邓菲无奈地点点头,“山里雪化带来的寒气。”邓菲说。
“嗯,这样下去我们坚持不了多久,”克莱姆告诉他,开始用一个塑料瓶子往外舀水。
“有自动排水装置。”邓菲说,“我检查过。”
“是么,不过这装置现在需要帮忙。”克莱姆回答说。过了一会,她抬头看了看帆,似乎快要被风撑破的样子,然后转向邓菲,“我提个建议你不介意吧?”她一边喊道,一边往船外舀水,“趁我们现在还有索具。”
“什么?”风吹得更猛烈了,伴随着阵阵的咆哮声。
“收起主帆,放开三角帆,向右转舵。”她命令道。
他惊讶地看着她,“什么?”话刚出口似乎就被吹散在了风里。
“我说,收起主帆——”
“好吧,就这样,我总算听到了。”把帆绳咬在嘴里,他打开了链接吊索和系绳栓的八字结,把主帆降了下来。接着升起三角帆,一切完毕,邓菲转向她,一脸的羞愧和窘迫。这时船才开始平稳行驶。
“哪边是右舷?”他问道,心想这次是绝不会忘了。
克莱姆舀着水,灿烂地笑着说:“那边。”头发在风中左右摇曳。
从胸前推开船舵,三角帆于是扬了起来。船终于借着风力优雅地朝洛桑方向顺利行进。雨似乎也减弱了。
一切趋于平静,邓菲问她:“你什么时候学驾驶帆船的啊?”
克莱姆笑笑,放下瓶子,“我父母在金塞尔有栋别墅,每年夏天我们都会去那里度假。经常是我开船。”
“你什么?”
“开船,”她说,“就像你现在这样。”
“只是确认一下。”
“我那时开得相当不错呢。”
“这我相信。”
“如果你让我试一把,”她说,“我估计我们可以和风赛赛跑。你有地图吗?”
“没有。”
“聪明的小伙啊,地图都不用。”她皱了皱眉,“那边应该就是罗拉镇,”她说,“瑞士,没问题,我们可以到达……”
邓菲不再言语,把舵交给克莱姆。
10点过后,他们上岸把船拖到一所房子前的草坪上,这个房子又大又黑,离罗拉镇大约还有十五英里远。搭一位货车司机的便车来到日内瓦,直接登记入住了一家他们看到的旅馆,并告诉前台服务生说他们的车不巧在半路抛锚。
早上,邓菲找来这家“老乡村”旅馆的商业登记簿,在一个友善的服务生帮助下,查寻墨洛温机构,不过资料不是太多。
据文献记载,机构建于1936年,是一位叫伯纳德丁·戈梅勒兹的巴黎市民作为礼物捐赠的。旨在慈善赞助、普及教育、弘扬宗教。1999年,机构宣布资产“大于十亿法郎”,也就是七亿美圆。但是还会有更多么?大于到底是什么意思?
是多于。那么,邓菲想,二十亿瑞士法郎就是多于十亿瑞士法郎。一百亿也是多于十亿瑞士法郎。等等,具体数目谁也说不准。
换句话说,这个机构无疑很富有,但到底有多富,无从知晓。它的董事长看来会是戈梅勒兹的儿子或是孙子。至少,他们的姓都一样:伯纳德丁·戈梅勒兹。
机构的地址和董事长的住址在簿里都显示为策尔内茨的拯救之山山庄。
帮忙的服务员六十来岁,一头金发,戴着泰迪卡通耳饰,眼角布满深深的笑纹,当邓菲问她策尔内茨在哪里时,她笑了起来。
“这里是格劳宾登,”她感叹道,好像这个行政区坐落在斐济淤的某个地方,“你问的镇子还很远呢。我想,那里的人大都说罗曼斯语,不是德语,也不是意大利语。”
“可是它在哪儿?”邓菲问道。
她转动着眼睛。“东边。奥地利南边,过去圣莫里茨。”她又想了一会儿,“不过,当然,”她说,想要进一步澄清问题,“就是海蒂·卡拉姆住的那个地方。”
飞往策尔内茨似乎不太可能。他们在苏黎世机场租了辆车次日早晨出发。
大约二百英里的路程,横穿瑞士东西,他们预计七八个小时就可以到达目的地。不管怎样,一路景色宜人,他们早已忘了时间概念。曲折的小路盘旋而上,远处绵延着依山的美景。象牙色的河水在山谷间潺潺流过。仿佛置身仙境。和家乡的多尼哥一样绿的山间到处开满野花。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冰川、湖泊和牛颈上清脆的铃铛。
在人口只有三万三千的瑞士小镇库尔、阿尔卑斯山的哥谭镇,他们向南开往左兹,沿着一条狭窄的小道穿过假日峡谷,恰巧在太阳落山前赶到策尔内茨。
策尔内茨镇子很小,却充满生气,那些徒步前往瑞士国家公园并作短暂的停留的游客都聚集在这里休息调整。这里是瑞士唯一的国家野生保护区,方圆六十四平方英里的松林植被,并有大批的野山羊、岩羚羊和红鹿栖息于此。
和美国的公园不同,瑞士国家公园绝少人工雕琢的痕迹,除了一家简单的饭店和瑞士标志性的荒原小径,完全保持了生态的原貌。
在策尔内茨,杂货店里到处涌动着日本游客和穿着格劳宾登休闲服饰的徒步旅行者:登山靴、羊毛袜、短裤、工作装。再配上昂贵的太阳镜、背包和书袋。
镇里到处洋溢着节日气氛。甚至显得有些喧闹。游客们赶在6点打烊之前都在拼命地采购啤酒、瓶装水、熏肠、面包,还有奶酪、完美的拐杖和强效防晒乳。
出乎邓菲意料,找住处竟然遇到了麻烦。镇里的几家旅店都已客满。不过离开镇里的主要街道,运气就来了,他们看到一家传统农舍,窗口里打着售卖助行金属架的广告牌。五十美圆他们就租到了一个二室一厅的套间。起居室里摆放着一个装满小饰品的玻璃橱,其中五英尺长的木质号角和布谷鸟自鸣钟他从来没有见过,其他的家具都来自宜家。
他们在一家松木灰泥风格的饭店吃了晚饭。桌子上装饰有蜡烛和鲜花。食物也很可口。饭后他们来到隔壁的斯图比利酒吧点了杯酒,在火炉旁的座位上坐了下来。
酒吧舒适宜人。邓菲和一个女招待搭话聊了起来。时不时拿她的传统服饰开玩笑。接着,他说,“我们在找一栋房子,就在这儿,策尔内茨。”
“房子?”她问道,“你是说,租的房子?”
“不是,”邓菲告诉她,“我们在找一个很特别的房子。”
“哦?具体地址是什么?”她问道。
邓菲耸耸肩,“没有门号,什么也没有。我知道的就是拯救之山庄园。你知道这个地方么?”
“不知道。”
“一位叫戈梅勒兹的先生住在那儿。”
“是西班牙人么?”
邓菲摇摇头,“法国人。”
“我估计他不住这儿。”女招待说,“至少不在策尔内茨,不然我会知道这个人。自打出生我就在这里。”听了邓菲的建议,她又问酒保是否知道一个叫戈梅勒兹的先生或是拯救之山的地方。酒保摇摇头接着到隔壁问另一个人,这人恰是这里的镇长。两分钟后,他带着信儿回来,“早上到邮局问问,他们一定知道。”
他们照酒保说的,第二天一早就来到邮局。问询此地是否有一位戈梅勒兹的先生和拯救之山庄园的地方。柜台后的职员马上表示知道他们说的是谁,“是的,当然——戈梅勒兹,他从这里拿信的,自从我是孩子的时候。大部分是杂志。”
“那么你认识他了?”邓菲问道。
这个人摇摇头,“不认识。”
“那——”
“他有很多人为他工作。他们一星期来两次。每次都是那辆车,你喜欢车么?”
邓菲耸耸肩,“当然。”
“那你一定也喜欢那辆车。经典的车款。奔驰敞篷车,当年希特勒的座驾。”
“你知道他的房子在哪儿吗?那个叫……”
“拯救之山,”那个职员宣布说,笑着。接着又变得严肃起来,“我从没去过,不过其中的一个管理员说过那房子四周为公园环绕。——所以可能在公园里,而不是公园,你明白么?富人都策划能……”
邓菲点点头,“他们什么时候拿邮件?”他问道,“也许我能和他们聊聊。”
职员耸耸肩,“周四周五。”
“今天?”
职员点点头,“如果你下午来,也许你就能见到他们。”
街对面有个小的咖啡厅。桌子和椅子都在露台上。他们喝着咖啡,读着《先锋报》,一边盯着对面的邮局。空气清新刺骨,太阳很强,被云彩遮住时,温度会骤然下降达二十多度。中午到了,他们点了三明治和啤酒。1点钟,克莱姆出去散步,邓菲独自做起了《先锋报》上的填词游戏。奔驰车一旦出现,他说,他会冲到租来的车上,按响喇叭,虽然这在瑞士不太好,但这样她才能听到。可奔驰车却迟迟没有出现。
克莱姆半小时后又回到桌前,拿着一张公园的等高图。他们把图在桌面上展开,试图找到戈梅勒兹别墅可能位处的空地。可什么也看不到。
就在邮局快要关门的时候,邓菲突然注意到街角转过几个身影。于是噌的站起身来,接着看到一个身穿黑色西服,打着制服领带的黑发男人开着一辆老式奔驰。他抓起克莱姆的手腕,在桌子上扔了一张一百法郎的纸币就冲向了租来的汽车。一个街区的距离,当他们赶回邮局的时候,奔驰车已经向东驶出了镇子。
他们在远处悄悄地跟着,尽量不引起注意。地图搁在克莱姆的大腿上。“没有进入公园的路啊,”她说道,“只有骑马和徒步的小径。我真不知道他会朝哪儿开。”马路边一条阴郁且水流湍急的小河撞击着砾石发出轰轰的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