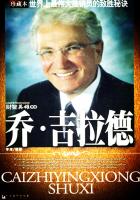五
也不知是天真的快亮了,还是土豆的香味叫醒了我。我坐在地上,身体一歪,头从膝盖上滑到一边,便醒了。火差不多熄了,土豆正香,天正蒙蒙亮,路上没有一个人。我随手捡起根木棍,往带着余火的草木灰里拨弄出土豆,拍了拍,剥去烧糊的皮,吃了起来。真香,比监狱里的饭好吃多了,要是再有点盐,或是有碗汤,就全了。我对自己说。这一夜,太值了。我不仅恢复了自由身,还不用受猪三的气。就是刚才这一会儿觉,也睡的好。这头往膝盖上一放,就沉沉的睡过去了,不仅没梦见监狱里的事,连娘都没梦到。他突然记起了上学时,老师讲颠沛流离这词时举了个例子,差不多就是自己现在的情况,老师说的多么苦,多么难熬,我怎么觉得这日子过的很舒心?难道这就是人的身份不同,对事情出现完全相反的感觉吗?这样说来,自己又增加了一些生活体会,要不是当了逃犯,这辈子哪来这种体验?我苦笑了一下。
填饱了肚子,我又出发了。继续顺着路往前骑,不大会儿,来到一个小集镇。向人打听后,知道再骑个把小时就到了县城,于是我真奔县城而去。越接近县城,衣着光鲜的人越多,我也找了个清水塘,用手当毛巾认真洗了把脸,再拢了拢头发,等水面平静下来,再低头一照,感觉还过得去,就精神抖擞的进了县城。
顺着人流,我来到自由市场,叫卖起自行车。现在我用不着自行车了,丢了也可惜,再说自己正差钱。这是辆八成新的永久牌,再怎么着也能卖个一百五六十块,于是我说家里急用钱,叫价一百六。不大会儿,围起一圈人,经过几次讨价还价,最终以一百三成交。打听到长途汽车站的方向后,我来到汽车站。看到车站贴在墙上的各种图表,我才知道这是九合县,刚才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我装作路过这里的外地人,多一句话都没问。仔细看了地图,才知道九合县与我的家留陈县一个在东,一个在西,相差好几百里,而且中间还隔着省城。关键是,从九合县没有直达留陈县的车,最近的路线是先从这里到省城,从省城再搭到留陈县的车。这样得两天时间才能回到家。问题是,我不能这么走,我知道,现在监狱正四处追捕我,省城的各汽车站肯定是重点盯控地方。从九合往外的车除到省城外,还有相邻的几个县,再就是往外省几个城市。如果走邻县,再从邻县到邻县的邻县,这样一直转下去,时间太长,而且其中有些县离监狱不太远,说不定也有追捕的警察盯在哪个地方等着自己呢?干脆,直接到邻省,再从邻省回家好了。这样尽管路远一些,但安全性高得多,而且需要的时间会更短。
打定主意后,我买了最快,也就是一小时后发车到邻省的票。然后到候车区找了个候车座位躺下,拿捡来的报纸盖在脸上,补起了瞌睡。我知道,从现在起,我必须抓紧每一点空隙时间来睡觉,因为我随时都有可能连着几天几夜睡不成觉。起码现在,我是安全的,我相信说破天监狱也不会想到我会在这里。睡前,我还十分礼貌地请周围的乘客到时候叫醒自己。
上车后,我与人换了最后排靠窗户的座位。车开动后,我继续打瞌睡。尽管车晃晃悠悠的,睡不踏实,但总比睁大了眼睛熬精神强。睡不死也好,这样也有个警惕,好让我一到停车的时候就醒了,以防万一有事,我可以及时跳窗户逃跑。
经过一整天的晃悠,天快黑的时候我才来到了邻省。一下车,我就来到购票厅研究地图,寻找合适的路线。从这里也没有到留陈的车,只有到离留陈最近的地级市新会有车。我就买了明天早班到新会的票,凌晨四点半发车。然后我到附近找了个小吃点,花一块五毛钱,来了份盒饭。饭后又找了家私人旅社,花二块钱,要了个通铺。告诉老板早上四点钟叫我,便脱了衣服,钻进被窝蒙头便睡。
这一夜我睡的很实,但并不妨碍我同时做了一个梦。在梦里,爹让我照顾好娘和弟弟妹妹,我也争气,靠自己的双手把他们养得好好的,但是突然来了个警察,要把我抓到监狱里。我极不情愿,极力反抗,还是被人从床上抓起来了。我极伤心极绝望地哀号了一声,却把整间房里的人人都吵醒了。这才发现原来是老板叫我起床,见老板一脸诧异地看着我,我不好意思对大伙点了点头,说:“对不起,做了个恶梦。”
六
从这里到新会比昨天的路程更远,路上要吃两餐饭,要深夜十一点才能到。但我不打算到新会,我下午五点半在中途一个小镇下了车。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新会离家乡不太远,沿途可能已经被监狱的人盯上了,不安全;二是我研究过地图,从这里下车,往东翻过几座大山,再有半天的路程,就可以回家了。这样算来,如果路途正常,我最晚明天下午可以回到娘身边。想到娘,我又揪心了,娘病重了,我就这样回去,又能解决什么问题?17岁的弟弟原本明年高中毕业,但随着自己犯罪入狱,他的学也上不成了,听说也随着别人一起去南方打工了。也不知他的运气怎么样,能不能找到合适的工作,能不能遇到有良心的好老板,能不能寄点钱回家给娘看病。13岁的妹妹在上初一,也不知现在能不能继续上下去。该死,该死啊,该死的周扒皮,该死的自己,害得一家老小无依无靠。前天从别人家里顺来的钱,和那辆自行车换来的钱,两天来已花了三十多块,现在口袋里不到一百二十块钱,哪能够娘看病?
就这样心事重重的,边打听路向,边往前走。我觉得有一种重担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来。钱,我需要钱,现在说什么都没用,只有钱能帮助娘和妹妹。但上哪儿找钱?我又不会变戏法,空手变钞票。又往前走了几里路,天完全黑透了,面前的山也越来越大。我要找个地方住下来,养好精神,明天不还知有什么等着自己呢。但这山野乡村,哪里有住的地方?记得小时候,倒是经常有过路的人上家里来借宿,爹娘总是很客气的让人家进来,给弄吃的,烧热水烫脚,把家里的床让给人家,让我和弟弟妹妹睡地铺。但是现在这年月,自己这身份,我下意识地摇了摇头,径直往一个小村头的稻场走去。
稻场推满了草垛,历来是冬天逃难和要饭的人落脚的地方。那时候民风纯朴,见到这样的人,老太太和小嫂子们都会剩上一碗半碗饭送过去。今天轮到我了,我不指望有人给送吃的喝的,也不想引起人家的注意,我希望就象徐志摩在诗中写的那样,悄悄的来,悄悄的去好了。
走到草垛边,我扯了些草,给自己弄了个背风的,还算舒适的窝,再弄些草,把自己厚厚的盖上。刚躺下去,才想起晚饭还没吃。尽管一餐不吃饿不死人,但这一餐不吃,谁知道下一餐要等到什么时候,在哪儿吃呢?我知道,逃难在外的人,但凡有一点可能,就得把自己的肚子给填饱。只有这样,他才有更大的生存空间。想到这里,我又从草窝里钻出来。转头看看面前的小村子,差不多二十户人家,只有不多的几处灯光从门或窗户里透出来,显得格外死气沉沉。这是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农村只剩下6061部队的结果。6067这番号也不知是谁总结的,精妙!现在对我来说,这村子只有6061部队好,在全部由老人和小孩组成的村子里,我找点吃的应该不成问题。我站起身,拍了拍头上和身上的草屑,往村子里要紧不慢的走过去。
没想到刚露了个头,就被眼尖的狗看见了,一只狗一叫,立即引来一片狗叫声。我从小就是伴着乡村土狗长大的,太熟悉这伙伴了。我仍旧要紧不慢的往村子里走,也不拿正眼瞧那些迎面而来的狗。只在狗们张牙舞爪的呜到跟前时,我才轻轻地端起右手,用食指轻轻比划了一下,两眼和善的看着狗们,嘴里配合着轻轻的温柔的嘘嘘一两声,狗们的叫声立即稀疏了。离我最近的狗仍警惕地看着他,不再叫,也不马上表示友好的动作。我半弯着腰,嘴里发出一种只有狗和我自己听得懂的声音,仍旧把右手伸出去,伸到狗脑门上的骨线处,轻轻的抚摸,狗立即换出了友善的面部表情,很温柔地配合着。其他的狗见状,也不再叫了。它们要么各自回去睡觉,要么继续忠实地蹲在自己的岗位上。
还是转了关圈,我摸进一家的厨房,弄了点剩饭剩菜,躲在角落里填饱了肚子,又顺手从墙上拿来一串麻绳,往腰间一扎,再往稻场转回来。途中,我对一只在我附近转悠的狗又做了个动作,把它引致稻场上来。我再次把手伸向狗的脑门,当狗同样温顺地配合平躺在地上时,我另一只手迅速把自己的上衣蒙到狗的头上,迅速拿脚跟狠狠地往狗的耳朵处猛踩几下,狗一声不吭就伸直了腿。我边对狗说,对不起了伙计,我要救娘,只好牺牲你了。又拿绳子死死地往狗脖子缠上几道,把狗丢草堆里埋起来,再起身往村子里走去。
不到一个小时,我轻松结果了四只狗。明天五更出发,到小镇上把狗卖了,又可以给娘多准备一些钱。我满意的想着,再一次钻进他的草窝里,美美地睡上了一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