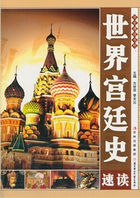骆荼一愣,难以置信地盯着拓尔诺,拓尔诺这才意识到自己语气重了,连忙解释:“荼儿我不是这个意思。”
骆荼一言不语起身走出军营,面上倔强地不让眼泪掉下来。拓尔诺见状急忙将骆荼搂进怀里,他的确是喜欢这个女子的:“是孤错了!”
战兴北回到军营中,在宿印怀面前单膝下跪:“草民战兴北参见国师!”
“快快请起。”战兴北起身后,脱下铠甲换上了那件粗布短衣。看着宿印怀浅笑的脸庞,战兴北依然不知道为什么他硬要他穿上将衣铠甲去见拓尔诺。
“拜托了!”
战兴北点头:“草民定当竭尽全力!”
肆水院的后山上,司路不再坐在湖前打坐,她慢慢转移了位置,开始坐在瀑布边缘,汹涌澎湃的水流一泻而下。不断有水珠溅在司路身上。久而久之,也便习惯了。她日复一日地反复打坐,几近走火入魔。岑九站在远处看着这样的司路,摇着头走出了肆水院。
短时间内,她定是走不出来了!
惹怒了骆荼的拓尔诺自知是他有错在先,不断哄着直到后者渐渐露出一丝笑容。假借应敌之名,骆荼道:“大王,荼儿觉得战兴北所说的三万大军必是未到,不然他不会只带着少数精兵前来此地。荼儿认为,大王可借这几日,养兵蓄锐,并且给我些时间和长老调动兵权。届时,就算洛薛的援兵真的到了,大王也不足为惧了!”
拓尔诺不由一愣,喜出望外地抱住骆荼:“你是我拓尔诺的福星!”
骆荼娇笑起来:“能成为大王的福星是荼儿的荣幸!”
拓尔诺愈发地对骆荼爱不释手起来。
姚甫灵正想吩咐士兵们在前线多加些人手,以提防拓尔诺的突袭。宿印怀拦住她,对武诚说:“留下几个人在前线,其他人全部休息。”
姚甫灵惊道:“你这是做什么?”
“这几日无需严加防守,拓尔诺不会派人前来突袭。”
“你怎么知道?”
宿印怀望着被沈汉等人簇拥在中间的战兴北,笑道:“一切都是他的功劳。”
姚甫灵却并不领情:“你究竟让他做了什么?”
宿印怀遥望着北荒的方向,心下暗忖:骆荼,你可莫要让我失望。完全忽略了姚甫灵的他转身走进军营。姚甫灵气得要跳起来,好在她是个了解他的,不屈不挠跟在他身后,他不说没关系,她可以烦他。
夜深人静,战兴北坐在军营外,看着洛薛的安宁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沈汉拿了瓶酒递给战兴北,一屁股坐在他身边。身为将军的沈汉不能喝酒,这瓶酒是他拿给战兴北的。
接过酒瓶,后者调侃道:“你小心我告诉姚老将军!”
沈汉眼一瞪:“混小子,给你的!”
战兴北笑着拧开,浓郁的酒香随着北风远去,他喝下一口,淡淡的思绪萦绕在心头。
“你知道我爹的旧疾是怎么落下的吗?”战兴北仰头又喝了一口酒,他当初一直在想如果有朝一日他能见到这个人一定要质问他为什么当时不去。可是,其实是不当的,他没有义务也没有理由一定要这么做。
沈汉想了想:“战争。”
“是的。”战兴北抿唇,添净唇角的甜味,“六年前,国师回帝都不久,离这里大概三十里路的边关,爆发了战争。我爹连日赶去救急,在边关苦斗了三个月,战争告捷。”
战兴北指着洛薛继续北去的方向,那里是大舜国的方向,六年前那一战,就是和大舜开的战。大舜国是北方最强盛的国家,那一战的残酷,不难想象。战勇就是在那时留下的旧疾。
“父亲一直以为会是大义将军北上前来支援,那么那一战,定不会死伤那么多人。但是没有,他像是贪上了帝都的安详和奢侈华贵,但这仅是我的一意认为,我爹并不相信。到死,他都只在遗憾,没能和大义将军再见上一面。”
“我听说六年前大义将军连和陛下上奏北上都没有,我知道这不能怪他,却还是无法原谅他身为一名护国将军,却没有丝毫保护百姓的责任心。今日一见,其实不然。是我太过偏激了。”无论是谁,都不能因为本身是怎样的身份就被冠上一个“必须这样做”“你不做就是你不对”的虚有罪名。
一个人最委屈的时候,是当他身不由己的时候。宿印怀在见到战兴北的第一眼就知道了些什么,但骄傲如他是不屑于解释甚至是认为没必要解释的。他只说了四个字“身不由己”,他说出口时的重重无奈和沉痛着实震惊了战兴北。个中缘由,如何理得清呢?他又如何能肯定,当年的他就没有一丝想要北上的心呢。
沈汉沉默地听着,他是个粗汉,不知道什么拐弯抹角拍马屁。他所知道的宿印怀和战兴北都是一等一的硬汉,宿印怀更是其中佼佼者,所以他才会如此敬服他。在视人命如草芥的战场他依然秉持能救一命是一命的原则,固执地不肯放过任何一个有可能活下来的生命,就这一点,沈汉甘拜下风。
沈汉看着战兴北清明的眼神,虽不知道二人交谈过什么,却是明显地感觉到了后者的变化。他嘴角笑意更深,果然,一定要让他们二人见上一面是对的。至少,这种他看见的变化,是好的。
一连三天下来,拓尔诺果然没再来突袭,这不得不令姚甫灵再次震惊于宿印怀的本事。与刘抑的通信中,他们已是再过几日便能抵达洛薛。
三天下来,拓尔诺听了骆荼的话,没有进行突袭计划,而是命所有士兵回军营休息,养兵蓄锐。但令他不安的是骆荼传信过去骆族的信却是宛如石沉海底,没有一丝消息。三天下来骆荼也连写了三封。一封回信也没有。骆族向来视族长为天,也怪不得拓尔诺会如此不安。
骆荼的脸色比他好不到哪里去,她神情极度慌张,她决定再写一封。她拿起狼毫笔时手抖了一下,她停下来,强制自己的手也要镇定下来。沾了沾墨水,她刚写了一个字,那一笔就划坏了纸张,一笔长长的黑色突兀地打乱了纸字的顺序。拓尔诺拿走骆荼手中的狼嚎笔,将她抱在怀里:“不要担心,骆族会没事的。如果,明天还没回信,我们就去诺北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