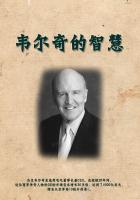怕影响他的婚礼,所以没有告诉他,她难产而死的消息,这是他的好助理,钟离岳的手指抖动着,最后狠狠松开了他。
在他的婚礼上,众目睽睽之中,他飞跑了出去。一身洁白婚纱的云熙哭着喊他的名字,可是他头都没回。
陈波也拔腿跟了出去。
钟离岳的车子一路开得风驰电掣,横冲直撞,最后停在了伊千夏住过的地方。这里,此刻正被一片肃穆和悲伤笼罩。
他一脚蹬开了那院门,冲了进去。低垂的挽幛,四处飘散的纸钱,一片肃穆的空气,他的步子忽然间变得沉重,越来越近的视线里,一身白色的伊千月慢慢转过身来,她的怀里,抱着一个小小的,骨灰盒。
他的目光死死地定在那小小的盒子上,那一刻,所有的人都看到他脸上的惨白。
他忽然间拔腿冲过去,一把夺过了千月怀里的骨灰盒,用力地去掰盒盖。
“钟哥!”陈波飞奔过来,手忙脚乱地去抢他手里的骨灰盒。可是他不肯松手,他目眦欲烈,双手死死地把着那个骨灰盒,非要把盒子打开不可。
“钟哥,你不能这样,钟哥!”陈波吓坏了,“钟哥,这里面是千夏小姐的骨灰,你不能把它弄撒了。”
骨灰盒被陈波抢了过去,钟离岳面目狰狞无比,忽然间一把将伊千月扯了过来。他的青筋暴跳的大手掐住她的脖子,不顾她脸上惊恐的表情,发出撕心裂肺的声音,“为什么!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为什么,你告诉我她没有死――”
……
昏迷中的钟离岳四肢猛地一挣,所有的记忆悉数拉回,他醒了。眼前,是云熙泪汪汪的眼。
而他,却在努力地寻找着另一个人的身影。
“夏夏?夏夏?”
他急切地呼喊着,很怕在他昏迷的时候,她便消失不见。
“钟哥,千夏小姐和小瀚都在外面,你放心,他们没事。”陈波忙说。
钟离岳似是放了心,缠满纱布的头缓缓地落在了枕头上。
“陈波,别让他们走。”他费力地对他的助理吐出一句话来,陈波点头,眼睛里像是咯进了石子,难受。
而坐在旁边的云熙,此刻,她的心里酸涩无比。五年了,她在他的心里,终是比不过一个伊千夏。
走廊里,千夏仍然搂着小瀚坐在那里,钟离岳没有醒之前,她不会离开,她在等待他平安的消息。
陈波出来了,千夏的眸光望了过去,这个男人,在五年前,曾经处处维护她,并且帮着她一起做了一出好戏,后来,又是他,在像父亲一样的照顾着她的儿子,千夏对他,心里的感激无法用言语表达。
“钟哥醒了。”陈波走过来说。
千夏放下心来。
“他的伤怎么样了?”她又问。
陈波道:“没有致命伤,医生说,很快就会好的。”
千夏轻轻松了一口气。
她拉着小瀚的手站了起来,“陈波,既然他已经没有危险,我也该离开了。”
她拉紧小瀚的手,转了身。可是陈波拉住了她的胳膊,“千夏小姐!”
“你不能走,我跟钟哥保证过,不能让你们离开。”
千夏回头,眸光含了几分怒。陈波低下了头,“千夏小姐,五年前,是我帮着你欺骗了钟哥,五年后,请允我一个请求,千夏小姐,不要离开!”
陈波又抬头,满含期翼。
千夏嘴唇哆嗦,可是无言以对。望着陈波那真诚的目光,千夏无法拒绝他的请求。
对于陈波,千夏心里有愧。
她攥紧了小瀚的手,“我不走,但我想离开这里。”
这里有云熙,她和小瀚都是多余的。
陈波说:“我去给你们找住的地方。”
他把千夏和小瀚带去了一处新开发的楼盘,“这是我的房子,一直没住过,你们先委屈一下,住在这里吧!”
他推开门的时候说。
千夏看看眼前干净整洁的房子,嘴里说道:“谢谢。”
陈波道:“千夏小姐能不走,就是对陈波最大的感谢了。”
千夏望着陈波干净真诚的目光,只觉得心里头泛起一丝惆怅。
陈波临走时,帮他们带上了房门,千夏拉着小瀚的手在房子里四处转了转,三室一厅,装修简单,家电齐全。
她拉着小瀚的手在沙发上坐下,轻轻捧起他的小脸,“小瀚,从今以后,跟妈妈住在这里好吗?”
“嗯。”小瀚点头。
大眼睛忽闪了两下,小胳膊忽然扬起来抱住了她的脖子,“妈妈,你真的是我的妈妈吗?你为什么现在才来找我?”
千夏听着儿子委屈的声音,心里柔肠百结,她把他细瘦的身子放到腿上,轻声说道:“小瀚,妈妈以前,有不得以的苦衷,但是妈妈以后,决不会再丢下小瀚了。”
“嗯……”
小瀚把头,埋进了母亲的怀里。
医院里,云熙仍然守在钟离岳的床边,这个女人,他爱钟离岳爱到了骨子里,这么多年,她知道,他的心里一直都没有忘记过那个女人,可是她却在给自己催眠:伊千夏,她已经死了,即使他的心里永远都忘不了她,她云熙,也是人生的赢家。因为,陪在他身边的那个人,终究是她。
“云熙,你先回去吧!”钟离岳醒来后,眸光没有往日的柔软,而是淡薄的让她害怕。
云熙在帮他擦脸的手僵了一下,手里捏着那白色的手帕,此刻僵硬地,望着他。
“陈波,送太太回去。”钟离岳见她没有离开的意思,便吩咐陈波。
陈波嗯了一声,对云熙道:“太太,我送您回去吧,钟哥需要休息。”
云熙冷笑,他才醒来,就要她离开,她捏紧了手帕,慢慢站起身形,却俯身过来,在钟离岳的脸上吻了一下,“我走了,哥哥,你好好休息。”
钟离岳没有应声,云熙便转身离去了。
钟离岳起身要下床,陈波急切地喊了一声,“钟哥,你做什么?”
“我要去找她!”钟离岳说。
陈波忙过去按住他,“钟哥你才刚醒过来,不能下床走动,千夏小姐我都安顿好了,你放心好了。”
钟离岳抬头看了看他,却忽地冷冷地吐出一句话来,“陈波,你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陈波怔住了。
夜色渐深,小瀚在千夏的怀里打起了哈欠,千夏便帮小瀚脱衣服,“小瀚乖,上床睡。”
她把小瀚的白色卡通T恤撩了上去,可却在小瀚的胸口发现了一处隐隐的疤痕。
千夏吃了一惊,“小瀚,这伤疤是怎么回事?”
小瀚困得眼睛快要睁不开了,喃喃地说:“钟叔叔说我小的时候,做过一个手术。”
千夏惊愣地瞪大了眼睛,“手术?什么手术?”
可是小瀚已经困得脑袋都歪到了一旁,千夏压抑住心底无比的疑惑,把儿子抱上了床,让他躺下,把被子盖好,她却坐在床边,心底强烈的疑惑让她在下一刻,拨打了陈波的电话。
陈波正垂头站在钟离岳的床前。
刚刚,他把帮着千夏隐藏了五年的秘密,都说了出来,如何把她送到医院,又如何在她的恳求下,制造了她难产而死的消息,以及那盒骨灰,都是他买来的别人的。
而她,却被他偷偷地送上了火车。
去了那个遥远的山间小镇。
他把这个秘密藏在了心底,一藏就是五年。
钟离岳一个巴掌煽了过来。
“陈波,你真是我的好兄弟!”
面对着他扭曲的面容,陈波低头不语。
千夏电话打过来,陈波兜里的手机响了,可是他没接。他低着头,不管钟离岳怎么对他,打他、骂他、哪怕是让人砍了他,他都不会动一下。钟离岳阴沉的眼睛瞪着他,时间凝固了一般,只有兜里的手机在不停地响。钟离岳终于迈步离开了。
陈波接听电话。
千夏担忧的声音传过来,“陈波,小瀚的伤是怎么回事?胸口上?”
陈波沉默一刻回道:“小瀚很小的时候肝出了问题,是钟哥把自己的肝切了一部分给了小瀚。”
千夏愣住了。
她回头瞅了一眼睡在床上的小人儿,他侧着身子睡的很安稳,可是千夏的心,再也找不回来刚才的平静。
她离开的这五年,到底都发生了些什么?她的小瀚,怎么会有肝病?而且严重到,竟然要换肝的地步?
她捏着手机,可是手指在发抖。她一直以为,他会平安长大,可是没有想到,才很小的时候,就做过那样的手术。而换肝给他的人,正是待他一向冷漠无情的父亲。
千夏难以接受这样的事实,她跌坐在床边。
钟离岳来到外面,随便找了一辆出租车钻了进去,那司机看看钟离岳那满头绷带的样子,满脸惊疑,但钟离岳眉眼之间散发出来的那种凛冽气势让他不敢问什么。钟离岳上了车,他便载着他去了陈波的住所。
只是钟离岳没敢敲门,只一个人上了楼,站在陈波的寓所外面,抬手想叩门,可是手抬到半空,又贴着那门滑了下去。
他终是没有勇气敲那门。
多年前,他年轻气盛,恨伊千夏入骨,以至于,伊千月打电话说她要生产的时候,他竟无动于衷。
他不知道她会出意外,更想不到,她会“死”。
他让陈波去,因为他知道,陈波但凡千夏的事,定会百倍尽心,有他在,千夏不会有意外,可也正是陈波,他和千夏一起,弄出了假死的戏码,他帮着她假死脱身,并且瞒着他一瞒就是五年。
而他,就在这五年里,受尽了内心的煎熬。
他常常想,如果自己那个晚上过去了,是不是她就不会死?或者她从来没有怀孕过的话,是不是她就不会死?
他的身形缓缓地坐在陈波寓所的外面,多少的往事纷至沓来:
“先生,你去看看吧,小少爷不肯喝奶粉呢……”李嫂惊惶惶地找来。而他,呆呆地坐在卧室的床上,这些日子以来,他最怕的字眼,就是别人跟他提起“小少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