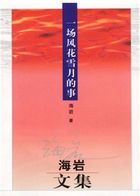上海。中国电报总局。
“杏荪这步棋走得妙!”经元善把手里的一张报纸冲着郑观应和同为会办的谢家福抖了抖,笑着说,“你们看,汇丰已经登报,正式取消了‘1元存款’。”
谢家福冲着盛宣怀哈哈一笑:“这也算是为‘胡大善人’出了一口胸中的恶气。”
盛宣怀兀自微笑不语。
经元善放下报纸,把目光转向郑观应:“陶斋向来喜兵事,好奇计,也来评说一下杏荪这手棋走得如何?”
“这便是大展阳谋。所谓绵里藏针,刚中带柔。”郑观应淡淡一笑,“汇丰若不废除此项存款,我便把这500元取后再存,存后复取,周而复始,搅得他做不成生意。”
谢家福说:“嘉谟伦这个人也不能小看。一接招,就知道这里头还有后手。”
“小胜不足为喜。”盛宣怀收起笑意,慎重地说,“我是万万没有料到,外国银行竟然会有这么大的力道——银根齐收,上海市面便几近崩塌。”
“不错。这些外国银行将银根一紧,中国钱庄、商号便如摧枯拉朽一般纷纷破产关张。”经元善也长叹了一声,“中国钱业还是禁不得风浪啊。”
盛宣怀说:“中国钱庄资本通常不过二三万,放款则高达十几万甚至数十万,通过眼下这件事来看,只要稍有倒欠,便岌岌可危。倘不筹集巨款,创设中国自有之银行,则不能挽救商情而维系市面。”
“杏荪所言,方才道出商务之枢要。”郑观应在一旁说,“洋务之兴虽莫过于商务,但商务之本还在于银行。”
“对!办我们自己的银行,要不然中国利权迟早要被外国银行一网打尽。”经元善也积极响应道。
“办银行可没那么简单。”谢家福摇了摇头,“要是没有五六百万的巨资恐怕难以成事。”
“绥之谢家福,字绥之。兄说得对,眼下办银行还真是不容易。”郑观应一副满怀心事的模样,“市面一溃而不可收,并已波及我招商、矿务、织布三局……虽说商局获得颇丰,其余二局经此一变,已然举步维艰……”
郑观应的话刚说到这,就见徐润一个人孤零零地走了进来。
“想不到,大伙儿都在。”徐润冲着几人哈哈一笑,抱拳拱手。
“雨之……”几人也面露笑意,纷纷起身离座。
“雨之兄,快请坐。”经元善指着身旁的一个座位。
“今日就不坐了,我有事找杏荪。”谁知平日里喜好热闹的徐润竟然破天荒地摆摆手,把目光转向盛宣怀,把头朝外面偏了一下,“杏荪,借一步说话。”
徐润的表现让几人为之一怔,就连盛宣怀也是疑惑不已。徐润说完这句话,便朝门外走去。
“雨之今天是怎么了?”谢家福一副懵然之态,望了望经元善。经元善也是一脸困惑地摇摇头。
郑观应见到徐润的反常之态,心里则蓦然一震,一种不祥的预感油然而生。
“我去看看。”盛宣怀对几人说了一句,便跟在徐润的身后走了出去。
徐润走到院外的天井中,停下脚步,对盛宣怀说:“杏荪,你虽已不涉商局事务,但这件事我思来想去,觉得还是告诉你最为妥当。”
盛宣怀见徐润一副严肃之态,虽不免有些诧异,却还是问道:“雨之,到底是什么事?”
徐润叹了一口气,就把自己亏挪局款的事一五一十地叙述了一遍。
盛宣怀越听越是吃惊,徐润说完之后,他已怔在了原地,待他缓过神来,不禁顿足道:“雨之,你好糊涂!”
朝鲜。“庆字营”营盘。
张詧怒气冲冲地走入张謇的营帐,往他对面一坐,虎着脸,一言不发地看着正在低头处理文书的张謇。
“三哥,您这是怎么了?”张謇停下手里的工作,一脸诧异地问。
“还不是你的好学生!”张詧重重地哼了一声。
“您是说慰亭?”张謇忙起身给张詧沏了一杯茶,“三哥,到底出什么事了?”
“袁世凯今日去我那提领海防经费,却不按格式填写领结,我让他改正,谁知他却大为光火,说什么小小的支应所竟敢如此荒唐,过去领款也未遵照什么统一格式。还说我故意为难于他,一副嚣张跋扈之态,真是气死我了。”
“三哥,喝口茶,消消气。”张謇把茶碗放到张詧的手边。
“季直,你来说说,我平素与他交情如何?想不到他竟摆出如此面孔对我?他在军中也不是一天两天,他能不知支应所的规矩?还说我荒唐,我看他才荒唐至极。”张詧越说越气,“刚靠上李中堂这棵大树,就忘本了。我看呐,你这个当老师的,也该好好管教管教了。要再任其这样下去,朝鲜的天都得让他捅出窟窿来。”
张謇坐回座位,半真半假地说:“人家已不再以老师相称,叫我如何管教?”
“这话怎么说?”张詧一怔。
张謇自嘲地笑了笑:“弟犹是一人,可在他那却称我为先生、季翁,直至前日竟称我为季直兄,真是愈变愈奇,我也不解其故。”
“岂有此理!”张詧愤然一拍桌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样的道理他能不明白?我看他是有意疏远于你。”
“他有意疏远的又岂是我一人。”
“你是说——筱帅?”
张謇点点头:“筱帅对他扶掖、信任、倚重直至寄予厚望……谁知此人却刚而无学,专而嗜名,攀缘李鸿章,令筱帅颇为难堪。”
“筱帅如今一病不起,袁世凯便更加肆无忌惮。”张詧沉吟片刻,“依我看,如此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人,还是尽早与他断交为好。”
张謇想了想说:“我看还是先好言相劝,若其不知改悔,再同他断交也不迟。”
“还有什么可劝的?”张謇的话音刚落,就见朱铭盘一掀门帘走了进来,大声说,“袁世凯妄自尊大,不顾礼义廉耻,与此人相识,实乃朱某毕生之耻。”
“曼君兄。”张謇一见朱铭盘这么大火气,忙站起身来,“莫非慰亭又招惹你了?”
朱铭盘也不答话,只是沉着脸,一把拽起张謇就往营帐外面走:“我们现在就去找他,断绝彼此的旧日交情。”
张詧一见两人匆匆往外走,也急忙在后面跟了上去。
招商局越南分局。
一名法军少校带着一队法国士兵,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
“你们……要干什么?”一名局员见一群陌生的军人骤然闯入,虽显得有些惊慌却还是本能地挡在法国军官面前。
“走开!”少校一把推开局员,冲着在场的人大声喊道:“所有人都待在原地,保持安静。”
局员们被眼前这群荷枪实弹的法国士兵惊得呆在了原地。
“上尉,带上你的人,搜查这里的每一个房间……不要放过任何一个角落。”少校冲着自己的部下下达指令。
“是的。少校先生!”一名佩戴上尉军衔,身材魁梧的法国军官,身体笔直地冲着上校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少校先生,你们没权这样做!”总办张沃生听到外面的骚乱,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从自己的办公室里走了出来。
少校望着张沃生,嘴角露出一丝轻蔑的笑意:“你是谁?”
“我是这里的总办。”
“总办先生。”少校朝张沃生走了几步,“我们怀疑招商局为中国政府提供军事情报,并且为中国军队运送粮食和弹药。”
张沃生郑重地说:“我们的生意是轮船航运,不是贩卖情报。”
“是吗?”少校上下打量了几眼张沃生,“任何罪犯在罪证没有公布之前都无一例外地会说——自己是一个好人。”
“招商局全都是合法生意,如果没有总督大人的搜查令,你们没有权利随便搜查。”张沃生义正词严地说,“我们还要营业——请你们出去。”
少校不以为然地看了一眼张沃生,随即对刚才那个法军上尉喊道:“上尉,你怎么还愣在那?快去执行我的命令!”
“是!”上尉答应一声,朝着自己身后的几个士兵一挥手,“你们跟我来。”
“你们不能进去!”张沃生大喊一声,挡在上尉面前。
少校的脸色骤然一变,从腰间飞快地掏出手枪,对准了张沃生,冷冷地说:“你要是再敢阻拦——我就枪毙你!”
张沃生倔强地伫立在原地,一动不动地望着少校,整间屋子里的空气也在瞬间变得压抑无比。
袁世凯见张謇、张詧、朱铭盘三个人鱼贯而入,先是愣了一下,随即若无其事地站起身,装模作样地朝三人笑道:“三位仁兄大驾光临,真是让世凯这小小的营务处蓬荜增辉啊,快请,快请……”
“袁司马这话不对。”朱铭盘不愠不火地揶揄道,“整个庆字营,没有比你这营务处更大的地方了。”
袁世凯听到朱铭盘对自己的称呼以及说话的语调不禁又是一愣,心中也蓦然升起一种不好的预感,他连忙换上一副煞有介事的面孔说:“世凯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还请曼君兄直言相告。”
“在下有一事不明,故想向司马请教。”朱铭盘坐在椅子上,从衣袖里掏出一封手札递给袁世凯,“这封手札可是出自司马之手?”
袁世凯皱着眉接过,看了一眼点头说:“正是。”
朱铭盘冷冷一笑:“营务处只是个差事,其官也不过从五品而已。于镇将可用札,于州县可用札,以上对下方可用札,而孝亭军门乃从二品武职,司马以手札付之,以下驭上,其意若何?”
袁世凯又是一愣,随即哈哈笑道:“曼君兄误会了。李中堂札委我为营务处主办,亲掌关防,而孝亭军门为会办,按北洋体制,我与孝亭以札往来,又怎能说是以下驭上?”
“真是笑话!”张詧在一旁冷笑道,“关防颁自北洋便用北洋体制,司马不见大清的州县检簿之印,无一不颁自礼部,难道你让这些县府州衙也与礼部一体吗?”
袁世凯的心里一震,他已经明显意识到朱铭盘和张詧是专门来找茬的,而张謇既然也和他们一道而来,看来也不会对自己存有善意。
刚想到这,他就听到朱铭盘又说:“司马荒谬之处,又何止唯此一事。内地职官,唯补实缺者方可出则张盖,营务处营官,从未见有用之者。乾隆、嘉庆年间我朝使节东抵朝鲜,国王出迎,乘以肩舆,曾被诏旨申饬,而司马出入居然乘舆张盖,制五色马旗,并将兵船遍插黄龙大旗,真不知司马欲自处何地?欲置筱帅于何地?欲置国家体制于何地?”
面对朱铭盘的一番质问,袁世凯不由瞠目结舌,无言以对。
“副营是筱帅从戎三十余载的坐营,放手让你接管之日,曾唏嘘嗟叹,遍谓宾僚:慰亭与吴家是三世交情,我所识拔,必不负我,必不改庆字营章程。”张詧也愤然道,“而司马接管后,便对海防教练经费吞吐其词,意谓筱帅曾借以冒领浮支。司马也不想想,筱帅何许人也?自你到营之日起,仆役口粮皆照差官发给,即便对你的贴补也动辄二三百、四五百不等,又如何会冒领那区区海防之款?”
“叔翁这话从何说起?”袁世凯自嘲地笑了笑,“真是越说让我越糊涂。”
“司马刚到朝鲜之时,对贩烟、宿娼之兵痞痛加严惩,当刑则刑,当杀则杀。朱某对此深表钦佩。”朱铭盘在一旁又接过话头,“而如今鸦片又重现军营,司马却视若无睹,官妓三名,聚宿三军府中,司马则躬与之,敢问司马:不知又何以面对昔日那些所杀、所刑之人?”
袁世凯的脸一阵红、一阵白地不停变幻着,目光闪烁游离,他想迅速找到诡辩之词,可朱铭盘、张詧所说却言之凿凿,根本不给他丝毫的喘息之机。
“袁司马。”张謇叹了一口气,“势力不可以慑人,权诈不可以处事。令叔祖端敏公、堂叔文诚公皆进士,尊公乃举人,正所谓荣当时而福后人。我劝你能像他们一样,好好读书,光明做人,万万不要重蹈三国时袁本初一家的四世三公之陋说。”
“季直,跟他多说无益。筱帅患病至今,他一次都没有探望过!如此不忠不孝之人,我朱铭盘今日便与他断绝昔日旧交!”朱铭盘说完之后,愤然一甩袖子,大步朝房门走去。
“曼君兄,你先别走,咱们有话好说……”袁世凯站起身,故意作出一副着急的模样在背后喊道。
张詧也站起身,对袁世凯说:“我等与司马相识,今已三年。以司马往日之为人,应该不能如此,以司马今日之行为,恐其不只如此。司马家世隆盛,年方二十几岁便当上了营官,且姓名又见知于天下闻名的李中堂,张詧不敢高攀,故于今日起,将与司马形同路人。告辞!”说完,紧随朱铭盘之后,也快步离开营房。
“叔翁留步,叔翁……”袁世凯满脸遗憾地冲着张詧的背影喊了几声,随之望向张謇顿足道,“老师,世凯虽非完人,却敢对天盟誓,所作所为绝无方才二公所言之意啊!”
“孰是孰非自有公论,这一点欺瞒不了旁人。”张謇站起身,语重心长地说,“袁司马,希望你能息以静心,一月不出营门,将我原来劝你读的《格言联璧》《近思录》诸书,字字细看,事事引鉴,千万不要以为天下人皆愚,天下人皆弱。需脚踏实地,痛改前非,不负令叔祖、令尊之名,及筱帅知遇之恩。”
袁世凯失声道:“老师,连你也信不过世凯?”
张謇一抱拳,郑重地说:“请司马不要再如此称謇,謇受之有愧!”说完之后,也独自朝营门口走去。
“老师,老师!”袁世凯紧赶了几步。
张謇停下脚步,背对着袁世凯,颇为沉痛地说:“慰亭,你应该晓得,为何今日我三人不照平日称谓而改称司马。若你果然能恢复三年前之面目,我等自当仍按三年前之交情待你。望你好自为之。”
袁世凯呆呆地盯着房门,过了半晌,他快步走到桌前,拿起放在上面的一只盖碗,狠狠地摔在地上。
就在法军少校和张沃生对峙之时,另一名法军少尉带着两名士兵从外面跑进来,在少校面前站定:“报告少校,我们在栈房发现了大量的军米。”
“是吗?总办先生,请你解释一下——”少校收起枪,傲然地望着张沃生,“你们的栈房里为什么会藏有军米?”
“请问少校先生,大米是违禁物品吗?”张沃生反问道。
“只要你们为中国军队服务,所有的物品就都是违禁物品。”
“我们是中国商人,为中国人服务是我们的本分。”
“从现在开始,让你那愚蠢的本分见鬼去吧。”少校冲着少尉一挥手,“把军米全部扣押,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准提运。”
“是!”少尉转身带着两名士兵跑了出去。
“中国军队随时会跟我们开仗。总办先生,现在你该知道问题有多严重了吧?”少校转过身,晃了一下手里的枪。
张沃生说:“可目前我们两国并没有开战,招商局承运军米是完全合法的行为。”
“荒谬!”少校不再理会张沃生,而是冲着那名先前正待执行搜查任务的法军上尉歪了歪头,“去执行你的任务,不要漏掉这里的每一个角落。”
“是!”上尉一边指示手下的士兵,一边朝里面的房间快步走去,“你们去那,你们几个跟我来……”
张沃生知道已经无法阻拦,便极为愤慨地说:“我对你们这种强盗的行径表示强烈愤慨!我一定会向贵国的总督阁下提出强烈抗议。”
“那是你的自由。”少校把枪重又插入腰间,“行使军人的特权也是我们的自由。”
顷刻间,房间里的卷柜、抽屉、存放杂物的木箱被士兵们一一打开,里面的文稿像雪片一样被撒得满屋都是,各种物品也被接二连三扔到地上,整个越南招商分局里面顿时一片狼藉。
上海金融风潮的影响,开始迅速向全国波及。
胡光墉在北京、上海、镇江、宁波、福州、湖南、湖北等地开设的阜康银号,几乎在同一时间全部关闭。
当杭州阜康亏倒之后,整个杭州城的市面顿时萧索无比。绸庄、皮货的交易也随即寥落,一切交易都需要现钱成交,以致各行各业无不紧张度日。
昔日北京城内的阜康此时也已大门紧闭。而在北京素有“九城之冠”的著名钱庄——恒兴、恒和、恒源、恒利,也因人心摇惑,横遭挤兑,终因周转不灵,不得不关张歇业。
一时之间,银价狂涨,人们害怕银票不如现银安全,于是持票去钱庄取银的储户络绎不绝,街道也几乎为之壅塞。各钱庄主人人自危,整个北京城的行市都笼罩在一片恐慌之中。京中那些在阜康银号存了巨款的高官们,此时更是急红了眼,纷纷上书要求清廷干预。
此时,翁同龢已兼任户部侍郎,阎敬铭也已接替董恂任户部尚书。慈禧对阜康倒账之事惊诧之余,责令户部全权纠察此事。
这一天,翁同龢、阎敬铭、文煜三人正在商议着如何对阜康进行清查和清偿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