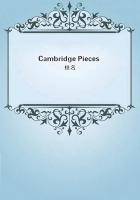五点五十分左右,车夫准时拉我姥爷到火车站,姥爷从黄包车上下来,坐在一个大碗茶摊子前喝茶。姥爷偷看一下表,只能偷偷摸摸看表,像穿福子这样衣服的人不可能戴着欧米茄手表的,五点五十五分。再一抬头,中野太郎带着几个队员过来换防,换完了,中野太郎捂着肚子向茅房跑去。
“老板,多少钱?”我姥爷掏钱。
“一碗大碗茶,一个大子儿您哪。”
我姥爷没有大子,拿出钞票给老板。这一下麻烦了,老板几天也挣不了这么多钱,还得找别的摊位老板换钱。我姥爷有点着急,眼睛看着车站里面。
“找您钱哪!”
我姥爷拿了钱向车站走去。走着走着,突然有点害怕,动作稍有变形,但他还是咬牙走了进去。候车室很乱,像现在乡镇一级长途汽车站,味道难闻,空气浑浊。厕所在一进候车室的右面,空间倒是不小,里面没什么人。厕所蹲坑都有弹簧门,不高,也就到人脖子,但蹲在里面的人从外面看不见。姥爷进去的时候,蹲坑的破门里面传来日本小曲 《 荒城之月 》,看样子这小子还有点思乡。环境不错,刚刚走了一个尿尿的,茅房里正好没人。姥爷掏出枪,拉开保险,按照自己想了多少遍的设计动作再不犹豫,打开门不由分说对着里面的脑袋就是一枪。
人像麻袋一样堆在地上,屁股还露着,姥爷感觉不大对劲,掰开那人的脸,糟糕,原来不是中野太郎,是仁丹胡子原田。顾不得那么许多了,按照自己设计的赶紧拔枪。姥爷从里面关上门,离仁丹胡子零距离,他也是王八盒子枪,拔了半天拔不出来你说着急不着急。这时候有人尿尿,姥爷不敢动,等人出去继续拔,原来王八盒子的枪套有机关,幸亏是搞机械的,很快打开了机关。刚要走,想起还有子弹,又摘了左右俩子弹盒子,一股脑儿放进褡裢里。这才开了破门,反身用个棍别上,把之前准备好的牌子从褡裢里取出来贴上:茅坑已堵!
出了候车室,姥爷尽量走得很从容,走了几步见四下老百姓都像平时一样悠然自得,更加放心了,也开始漫不经心走着,免得行色匆忙被人怀疑。
出了车站广场范围刚好过来一辆黄包车,姥爷拦住上去。
“您去哪儿?”车夫问。
“哎哟,我突然肚子疼。”姥爷捂着肚子好像马上就不行了。
“那我拉您去药房,要不去医院?”
“不用,你别动,我坐会儿就好了。”姥爷观察候车室方向。
“那这算嘛呢?”车夫不能白让姥爷上车。
“我算给你钱。”
车夫不说话了,干脆装了一袋旱烟抽着,表情就像现在你打车停下办事,照样走字,司机不吃亏一样踏实。
我姥爷捂着肚子,眼睛却看着火车站里面,趁车夫不注意又看看表,六点半了。
原来因为上厕所的时候仁丹胡子已经蹲在里面了,中野太郎一看自己的茅坑被人占着,又不喜欢去别的茅坑,跟猫似的死认一个地儿,干脆到月台里面的那个厕所,就这毛病救了自己的命。他回来找不到仁丹胡子,问别的日本兵,说如厕了,便来找。按理说他不抱希望,因为自己比仁丹胡子蹲得晚,还跑到月台厕所一个来回,碰碰运气吧。
“你这家伙,害得我到别处去上厕所,怎么还不出来……”
中野太郎一路骂着进来,突然看见刚才的茅坑门上贴着纸条,觉得不对劲,走近又发现有血迹流出来,小心谨慎从上面一探头,仁丹胡子死在里面。中野太郎掏出枪,开着枪跑出去。
广场上,我姥爷看见中野太郎开着枪跑出来,还吹着哨,日本兵听见枪声都往他这跑来集中。
“走吧,连歇会儿都不让。”我姥爷发着牢骚。
车夫拉着我姥爷快速离开乱哄哄的车站,但车站远处立刻围了很多人看,以至于车夫很费力气才把我姥爷拉出来。我姥爷最后一眼,看见一队日本兵抬着仁丹胡子出来,仁丹胡子的脸被军大衣盖着。
一辆卡车开来,中野太郎带几个人把仁丹胡子抬上去,围观的议论纷纷。熟悉天津人的都知道,天津人最喜欢看热闹,别说邻里之间吵架四周都围满了人,哪怕进行一场枪战,保证四下都有围观的,即使有人中了流弹,那也是一乐子。
“怎么了?”有人问。
“不知道。”先看见的绝对不会告诉后来的人,好像这秘密越少人知道就越属于自己占了便宜。
“好像大卸八块了?”
“不会!身上没血。”
“那就是开枪打死的。”
“不可能!我一直就在这,根本没听见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