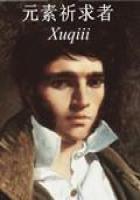俞舜臣心中豪气陡升,觉得这些人既藏于暗中,便都是些鼠辈。不管他们预伏着多么厉害的阴谋,自己也是“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不能怕了他们。当下再不犹豫,不论此人是故弄玄虚还是修炼的当真如此稀松平常,他都会一往无前。那人还是对俞舜臣毫无察觉,俞舜臣见他奔向了一个破旧祠堂,在那祠堂门前停下,却并未进去,而是站在门口踌躇不前。俞舜臣不敢与他相距过近,怕会被他发现,于是也便停了下来,观察那人举止。
只见他停了一会儿,突然开口说道:“星河耿耿在天,明月清辉匝地。暗夜私语,却不防隔墙有耳吗?”听见他的这两句话,祠堂中登时炸开了锅,许多人都大声叫了起来:“什么人在外面?”“是谁躲在那里?”“谁在偷听咱们说话?”“……”众人声中一个老迈的声音道:“我雀栖山二十八宿在此办事,朋友既出声示警,那是友非敌了,既如此,何不进来一见,你我也好攀谈攀谈。”这人说话雄浑有力,显然修为颇深,否则他那声音也不会凌于众人之上,俞舜臣心道:“他故意将偷听之人说成是‘示警’,显然老谋深算,不愿不明就里的与人为敌。”心中不禁称赞他的高明。听他自称是雀栖山二十八宿,思忖道:“这雀栖山二十八宿是什么来路,我如何竟没听见过?”他跟着的那人听见那老者的邀约之后便大大落落的走了进去,只听祠堂中一阵骚乱,俞舜臣想机不可失,趁他们注意力都在进去那人身上之时,自己何不趁机掩入祠堂,看看他们究竟说些什么。他快步向祠堂掩去,见祠堂的门窗残损,他怕躲在外面被人发现,于是又绕到祠堂之后,纵身一跃上了屋顶。好在屋顶的砖瓦也有破损,他不用用手掀开,倒省去一个麻烦,于是就着那破损之处,向祠堂里面窥望。
祠堂中间用枯木生着一个不大不小的火堆,但却异常刺眼,将那祠堂照耀得如同白昼。俞舜臣心想:“这火堆看着似有怪异,不知因为什么?”不及细思其中关窍,早看见火堆周围黑压压的站着二三十条汉子,人数太多,一时也数不过来。他们均身穿银丝雪线短衣,一副老于江湖的势派,他们手中拿刀举剑、扛枪挥棒,人人手中兵器各不相同。那二三十条大汉面向祠堂门口,一齐盯着那不速之客。他跟着来的那人一袭黑衣,脸上也是黑巾掩面,他进入祠堂之后便没再说话,眼光在众人脸上扫略来去,显得非常无理。那二三十条汉子中早有人按耐不住,高声喝问道:“你是谁?何以要搅扰我等的聚会?”
蒙面客向左走了两步,道:“这里似乎人太多了些,各位不嫌憋闷吗?”随即答那人的话道:“这祠堂也不是你们所有,你们来得,我便来不得吗?”人群中有人怒道:“这厮可不是找死吗!”他旁边一人拦下那人道:“十七弟,不得无理。”俞舜臣听出他的声音就是适才凌于众人声音之上的那个老者,见他瘦脸高鼻,长相与众人迥异,颏下一部白须隐在他那身雪白的衣服中几乎看不出来。他拦下自己的兄弟,对那人客气道:“阁下是友是敌,既然到此,因何不以真面目示人?”蒙面客哈哈笑道:“诸位伏于暗中,怎倒反说我藏于衣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