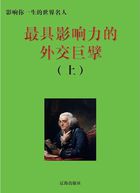就在李慕崎来到魏洲城的第二天午时,就有一队衙差,手持官榜,在城中各处张贴,这仿佛是一道福音,引来无数双目光,就连李慕崎也站在人群中,张望着官榜上面的字迹。人群中,布面夹着许多,不识字之人,满面的紧张与不安,左右四处张望,望着那些正瞧着官榜上面的字迹的人,想要寻到一丝别样的痕迹,从中推断,揣摩官榜上面的内容。
一位潦倒的书生模样之人,不忍瞧着那些面孔,分开身边的人群,站在官榜之前,高声的朗诵起来,声音中夹着些许的沙哑与无力,再细瞧他的面容,不觉令人有些担忧:苍白的面容之上,带着病态,额角边的皮肉已经塌陷,看不到一丝血色的双唇,正在吐着官榜上面的字迹,字字清晰,声声入耳。
就在他的声音之中,夹着数声冷冷的嘲笑之声,还有几句不满之声“哼,又在显摆自己的文化了,好像别人不知道他读过几年书似得。”又有一人插言道“仿佛我们看不懂,只有他一人明白似的。瞧他那一身穷酸样,你在瞧瞧他的面容,真不知他哪里来的勇气。他们身旁传来一阵附和之声。
他们的声音并不是很高,也没有故意压低,每一字,每一句,十分清晰的传到那个书生的耳中,生怕他听不到,甚至伸出手指,对着书生指指点点。书生听到这些言论,仿佛如没有一般,面上没有一丝变化,继续读着官榜。看着书生的面容,李慕崎赞赏的与他点头微笑。
书生细细的读了两遍,才慢慢的离开人群。瞧着那一道消瘦落寞的背影,李慕崎加紧步伐,三步并两步的迅速的追上书生,走在他的身边。书生瞧到身边衣着华丽的李慕崎,并没有放缓自己的步伐,亦没有抬起头去瞧李慕崎,只管慢慢的往前行进着。
“难道你没有听到他们的言论吗?”李慕崎眼中满是浓浓的兴趣,瞧着低着头慢慢行走的书生道“难道你不在意他们的评论与目光?”
书生未抬头,亦没有回答李慕崎的意图,依旧默默的走着自己的路,仔细的瞧着脚下的路、
“难道你是聋子吗?”李慕崎故意如此道。
书生终于抬起头,冷冷的看了李慕崎一眼,然后又将自己的头低下,冷冷道“我不是聋子,你倒是一个十足瞎子。”
“瞎子?”李慕崎面上没有一点怒容,望着书生道“我有眼,而且很亮,能够看到世上的一切事物,又怎么会是瞎子?而且,你方才应该也已瞧到我的双眼,怎会说我是瞎子。”
“你的眼睛确实很亮,亦没有瞎,”书生冷笑道“但也只能看到事物的表面,看不到事物的本质。如此与一个瞎子又有何区别?”
“哈哈哈···”李慕崎大笑道“我之瞎并非真瞎,而君之瞎才是真瞎。”
“哦?”书生猛然顿住脚步,抬起头望着李慕崎道“此言怎讲?”
“你说我看不到事物的本质,那么你应该可以看到,但依我瞧来,只怕未必。”李慕崎摇头叹息道“只怕是你自视太高罢了。人言‘自视太高看不清自己者,莫过穷酸书生。’想来此言定会不虚。”
书生仔细的瞧了瞧李慕崎。纵声一笑,又将自己的地下,快速的往前行进,想要逃离李慕崎的身边与他的视线。李慕崎却紧紧的跟在他的身边,仿佛不了解他的意图,依旧伴在他的身边,步伐几乎与书生的频率一般。
书生仿佛知道自己逃不掉,放缓自己的步伐,冷冷的道“既然你知道那一句熟语,为何还有追来?难道你也想要学穷酸书生的模样?”
“为何不可?”李慕崎冷嘲道“难道只许书生如此?”
书生沉默,没有回答,低着头,听着李慕崎的冷嘲热讽。他不知李慕崎的用意,但是心中明白,李慕崎如此缠着他必然有他的目的,不然瞧他的模样,又怎会如此。虽然曾经不知被多少个衣着华丽的人嘲讽,但是李慕崎与他们有着明显的不同,他知道底线,他有道德底线。
“你怎么不反驳?”李慕崎道“难道你不知道反驳,还是觉得我讲的是事实?”
“不论我反驳与不反驳,又能够影响你几分?”书生冷笑道“你已经对我作出了评判,我的反驳与不反驳,与你而言,只是最后的挣扎,我又何必如此白费力气。”
“不试一试又怎么会知道结果?”
“结果重要吗?”
“难道不重要吗?”
“不论你讲些什么,说些什么。该做的事情,我依然会做,不该做的事情,我依然不会去做。”书生冷冷的道“我总不会在你的眼光下生活,按照你的意图做事。若是我在意别人的眼光,总是在意别人的言论,只怕我只有死路一条。”
“难道你不在意对于与错?”
“对与错,应该留给后人去评论,世人口中的对与错,只是再拿自己做着对比,又怎么会得出真正的对错。”书生轻声一叹道“有几人能够站在真正的那个点,去评判对与错。”
“你果然不同,”李慕崎言语满是赞赏道“你的见解虽然独特,却满是深刻的道理。”仔细的瞧了瞧书生,轻声一叹,满是惋惜的道“这是你的优点,却也是你的缺点,有可能是你致命的缺点。”拱手一礼,道“可否一起饮一杯?”书生望着李慕崎,思索良久,终于点了点头,与李慕崎走进附近的一间十分简陋的茶馆。
景致只是陪衬,只是那一点睛之笔,岂会是最重要的环节。若是在意,只怕只是貌合神离的一对朋友,只是相互在敷衍。倘若彼此间的谈话也会十分的小心,只怕已经走到了那个小心的边缘,已经再难挽回。
铜锣声响,几乎是震耳欲聋,几乎每一个角落都在回荡这刺耳的金鸣之声,无处可逃。
李慕崎手中端着一只茶盅,茶盖还未除去,站在窗前,望着慢慢走来的一队人马:只见其中有四个着华丽官服的衙差,肩上抬着一只极其巨大的铜锣,三个手中紧握着巨大的锤子的衙差,高高扬起那个锤子,用尽全身的气力,狠狠的击在铜锣之上。三声合成一声巨大的金鸣,推开清风,瞬间盖满整个魏洲城。细细的瞧那几个距离铜锣最近之人,他们的身子也在轻轻的抖动,显然也受不了如此的巨震。与他们有数步之距,亦是一队衙差,手中高举着书着回避,肃静等字样的红底金漆的大字。一顶朱红的软轿夹在其中——八抬大轿。抬轿之人的面上满是红光,额上布着一层细汗,汗珠滚在一起,拉出一条细线,顺着脸颊的棱角,缓缓流下,流在已经有些粗肿的颈项之中。一队形容憔悴的士兵跟在其后,面上的疲惫与慵懒之色,令人不忍细看。也不敢再看,若是守疆的士兵,亦是如此,心中怎安?
旌旗几乎全部歪在一边,就连手中的长矛,亦是无力的斜在一边,矛尖之上,有着深深的锈痕,若不是阳光还算明媚,几乎见不到矛尖的光芒。幸好此时众人的目光全部集中在那一顶华丽的软轿之上,不曾望向那些士兵。幸好,李慕崎知道这些士兵的出处,不至于失去心中的希望,却难免失望,担忧。
细瞧着那顶朱红软轿,心中没有担忧,十分的开心。不免十分敬佩李李书衡的用人之道,若是来一个十分精明之人,李慕崎还不知如何作接下来的安排,见到这个钦差的举动,李慕崎瞬间安心,瞬间充满信心,甚至已经推测出这个钦差的所有举动与安排。
朝廷之中竟然还伏着如此人物,是幸还是不幸?李慕崎不禁问着自己:如此草包,不知是怎样爬到今日的官位?倘若朝廷如此人者众多,只怕是天下数万百姓之苦,是百姓之大不幸,如此之人,怎能留在朝中?
如此人物,爬到今日职位,必有其一技——溜须拍马,阿谀献媚。这本是他的升官之道,此刻却成了他的末日——只怕这是他最后的一段官运历程,他已经走到了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