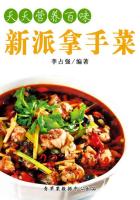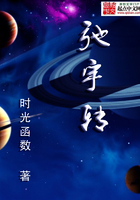韩诗韶望着渐行渐远的大旗,直至在风中飞舞的大旗隐没在那一片密林之中。过了许久,她才不舍的将双目缓缓的收回,望着残留在手中的余温,嘴角缓缓的勾起一抹笑容。那笑容无论怎样去看,总是会发现其中夹着深深的苦涩,就连吹拂在面上的春风,也难以将它融化。
望着已经消失不见的旌旗,那一个熟悉的身影也已消失在那片密林之中。不知何时,眼角处滴出一滴晶莹剔透的泪珠,浅浅的挂于眼角。微风轻轻的一吹,沿着美丽的棱角,缓缓的落在那一抹白颈之上,心中渐渐的泛起一丝不安,仿佛已经听懂了荡在心头之上的那一抹不安述说的言语。恍惚间感到,这一次的离别,就是永远的别离,不会再有相见之时。只怕若相见,已陌路,一个在这头,一个在那头,只能凝望,却不能触摸;若想触碰,却只能够抚摸到曾经的欢乐,此时的痛苦。
不知何时,眼中打转的泪水终于落下,一滴,一滴,重重的滴落在支撑着韩诗韶身体的那一张红木桌子之上,荡起的泪花,拍打着她手臂,亦在刺痛着她的心——仿佛缓缓的在她的心上流动,狠狠的落下道道细微的伤痕。
哭着哭着,终于累了,倦了。缓缓的趴伏在桌案之上,合上了那一双泪眼···
风悄悄的划过,逗弄着悬在屋檐之上的那一只风铃。“铃铃铃”,清脆的响声,响在这一处宁静之地,将熟睡的倦鸟唤醒。茫然的张开眼睛,抬头望着挂在天空之上的那一轮明月,对着那一只风铃叽叽喳喳叫个不停,似在怪怨那只风铃——扰它清梦,又似在埋怨天上明月为何如此明耀,令它难以再入眠。
那一轮明月确实太过耀眼,令人厌恶,尤其是一个寂寞之人,一个此时正在伤心相思之人。那一轮明月,将那一道寂寞的背影拉的太长,太长,也太纤细。仿佛是放大的寂寞,又仿佛是拉长的痛苦;又仿佛像是映在心底的伤痕···
响在夜风之中的铃声,终于将韩诗韶唤醒,张开红润的眼睛,抬头望着那一只不住摇晃的风铃,伸出手,想要将它捏在手心,想要触碰它的棱角,努力许久,终究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点。许是如此的动作,亦令韩诗韶悠悠醒转,望着自己努力抓了许久,不曾碰到的那一只风铃,嘴角勾出一抹无奈的且又幸福的笑容。那一抹笑容,仿佛就如窗外的春风一般,温暖,令人陶醉,却又夹着一丝冰凉。
望着窗外的那一轮明月呆呆的出神许久,终于被眼角冰凉的泪水唤醒。伸手轻轻的将冰冷的泪珠试下,一声低叹自嘴角划出。又深深的凝望一眼天上的那一轮明月,才缓缓起身,似乎费了全身的气力才能够站起。带着浓浓的疲倦,将烛台之上的红烛点燃。跳动的火焰瞬间映照在韩诗韶那一张满是苍白的面容之上。若不是这一片火光,几乎见不到一丝红**光。
就在这一片微弱的灯火之上,韩诗韶的目光终于落在了烛火之旁的一封书信之上——那是一封已经开封的书信。曝露在空气之中的那几行墨色的字迹映在韩诗韶的眼中。望着那几行字迹,韩诗韶猛然一怔。待细细的那几行字迹读完,心中又是一惊。思索许久,终究还是将封书信用力的执起。缓缓的取出,细细的读着心中内容。面上浮起的那一层惊色渐渐的退去,转而浮起一层喜色,那一层喜色愈来愈浓,终于将她的脸颊全部覆盖,就连她的眼中,此时也出现了笑容——慢慢的幸福。
明月无声的落在一片火炬之处,跳动的火光将那一片大帐映的仿如白昼,每一张面容亦清晰可见,就连面容之上的那些细纹的神情亦能够清楚的看到。
此时,大营之中十分的安静,跳动的火焰爆裂之声亦能够清晰的听到;巡夜兵士整齐的步伐一声声传于耳中,令人莫名的浮起一阵振奋之意。胸中的血液也会随着整齐的脚步重重的跳动。那时心中自会出现兴奋,还有一股激情。
李慕崎轻轻的跳挑着炉上的火焰,火焰在他的挑动之下,更加的耀眼。炉上有一只壶,壶中的水已沸,蒸蒸水气不住的自壶中跃出,萦绕在李慕崎的身旁,几乎已经他遮盖在那一层水雾之中。朦胧间,只能够清楚的望到那跳动的火焰。
李慕崎不远之处摆着两只茶碗,碗中此时静静的躺着香茗,却不见李慕崎将壶中的水摇入碗中,而是将那一壶沸水全部倒入帐外,重新支起一壶清水,将炉上的火焰挑的只有微微的一簇火焰之后,才将那一只盛着清水的壶放于炉上,将眼帘缓缓合在一起,嘴角挂着一抹笑容,缓缓的倒在椅背之上···
一声惊呼自帐外传来,却不曾将闭目的李慕崎惊醒,只是令他转了一个身。若不是韩忠邦将他唤醒,只怕此时他依旧安睡。
望着眼中带着一丝倦意,嘴角之上挂着一抹笑容;又见到他的身边摆放着那两只茶碗,还有此时几乎将要煮开的那一壶清水。韩忠邦的面色一边,目中射出冰冷的目光,冷冷道“元帅好兴致,居然又如此雅兴···”
听着韩忠邦鼻息中的那一声冷哼,李慕崎缓缓自椅背之上爬起,用手揉了揉眼睛,又深深的舒展一下身体,望着韩忠邦道“若是焦急有用,你我又何必如此奔波?”见到壶中之水已开,遂将壶中沸水倒入茶碗之中。将一只茶碗缓缓移到韩忠邦面前,笑道“何不将心中之事放下,静心将这一碗茶水饮下···”
“将军自饮便是,末将可没有这个心情。末将此时只愿生出一双翅膀,飞到敌军之中,饮敌人的鲜血。”韩忠邦冷冷的望了一眼李慕崎道。
李慕崎笑了笑道“即使将军此时果真背生双翼,只怕到了那一座城池,也只能够望着它落入敌军手中,无能为力。”
韩忠邦面色一惊,望着李慕崎道“元帅怎知那一座城池此时危机?”
李慕崎笑了笑道“那一座城池并不危机,而是已经落入敌人手中。若非此时已经落入敌人手中,又怎会派一细探入我军中,将这一封告急书信交于将军之手?而且定会在将军面前形容如何的危机,以及城中将士如何的奋力抵抗?”
“将军又怎知此信是假?”韩忠邦望着李慕崎道,“又怎知那一座城池已经失陷,落于敌军之手?”盯着李慕崎的眼睛缓缓道“将军并非亲见,怎会知其中有诈?”
李慕崎大笑道“若是将军得到城中的令牌,会不会见机拿下那一座城池?”
“令牌?”韩忠邦面色一变,惊声道“难道齐莫于丢失的令牌已经落到敌人手中?”
“若非如此,这一个细探怎会如此的匆忙赶到我军中,而且惶急的求救,却又不能够准确的形容城中之景。”
“难道方才将军已经听到他的言语?将军又怎知他所言是虚?”
李慕崎笑了笑,并没有回答韩忠邦之问,而是执起桌上的清茶,不管此时韩忠邦面上的惶急之色,将那一碗茶缓缓的饮下。
韩忠邦如热锅上的蚂蚁,见到李慕崎如此,。心中惶急,却又无可奈何,虽然心中亦在怀疑方才那人之言,却又不敢深信李慕崎的言语。如今挣扎吗,却又是一种令他难以忍受的折磨。就在韩忠邦不堪忍受,即将爆发之际。
只见大帐猛然被人用力的掀起,两个人影出现大帐之外。这两人韩忠邦都熟识:一人是李安桐,而那个十分狼狈之人正是方才送信之人。见到此人,韩忠邦面色瞬变,自坐上惊坐而起,手指着那人,满面惊色,却发不出一句言语。
细看那人,又怎会是韩忠邦熟识的中原之人,他的面容虽然像极了中原人,但是他的身上其他之处,并没有一丝一毫的中原人的痕迹。韩忠邦之所以会如此的震惊并不是因为此时站在他面前的这一位细探,而是李慕崎。他不曾与这人见一面,但是他却已经知道他是敌方的细作,亦知敌人计谋。如此又怎能令韩忠邦不惊?
望着韩忠邦此时面上的惊色,又见到他眼底深处的钦佩之意,李慕崎缓缓道“并不是因为我有未见先知之明,而是因为那城亦陷落之事我已在日落之时知道了。”
“将军怎会知道此事?此时应该十分的机密,绝不会有一丝消息外漏。”
李慕崎望着李安桐道“此事于比人人来说绝对会是一个秘密,但是与他而言却不是。”
“他?”韩忠邦顺着李慕崎的目光,望着李安桐道“他又怎会知道?他也不曾离开过大营一步。难道?”
“我并不会任何的奇术,”李安桐望着韩忠邦投来的好奇的令他有些不舒服的目光道,“只不过,若论细作一事,我只不过比他们高明一些。”
并不是李安桐打探消息的手法高明,而是他接收消息的手段高明,而且他的目光很是独到,仅仅只看了一眼,便察觉到那人是敌军的细作。
而边城失陷一事,却要感激丐帮之人,若非他们,只怕李安桐也很难知道这个消息;而李慕崎定然中敌军之计。后果将不堪想象。
胜负的关键,并不是智谋,亦不是人数,而是料敌之际。知道敌人的动向,知道敌人的意图,才会有胜利的希望。
“此时边城已失,该当如何?又该用何计破敌?”望着李慕崎,韩忠邦缓缓而道。
“夜已深,何不将此茶饮下,待明日再说。”这便是李慕崎的回答,令韩忠邦疑惑,不解的回答,却又是韩忠邦不得不做的回答。他以为李慕崎心中并无良策,需要深思才会如此言语。只得将那碗茶饮下,缓缓离开李慕崎的大帐,并未瞧到李慕崎嘴角的那一抹诡异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