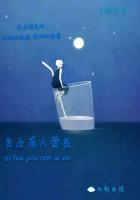第四章:北京之旅
舅爷爷的堂兄姓汪,家境也是非常的贫困,他有一对儿女,儿子因为在外打工喝酒后聚众斗殴打死了人,被判了刑,至今关在监狱里面。女儿更是嫁出去的人泼出去的水,自从嫁到城市里之后就很少回家来探望,偶尔回来慰问一下,看到家里面灰溜溜的东西就一直嚷嚷父亲把他们都给扔掉,可却也不拿出一分钱来补贴家里面用。由于汪伯靠家里的几片薄田来获取收入,偶尔也卖几只羊,可根本无济于事。他的妻子看到儿女一个个长大成了非人的模样,老伴也不思进取,满足于种田的现状,就赌气的离开了家。
汪伯失掉了儿女,又丢掉了老伴,感到异常的苦恼和孤独。为了躲避同村人成吨的口水,他每次等夜色降临,关好家门、把羊喂饱之后,就骑一个高梁的自行车去娘家索要老伴,几次未果,但她的娘家人依然执着,就开出了一个条件:让汪伯去城市里面打工,等银行卡赚够了五万元就跟他回家。
五万元,对城里人不算什么,但对农村人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汪伯年纪也不小了,可又有什么办法呢,城里人夫妻不合一拍桌子离婚就完事儿了,但到了到了农村,媳妇儿们都流行跑,那不顺眼就往娘家跑。汪伯养的子女们是没有指望了,只能依靠老伴来托付终身。
打工对汪伯来说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对痕雪来说,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父亲不成好,天天赌博、吸毒品,母亲因为他饱受村里人嘲笑的目光,所以母亲也和痕雪说了,她现在活就是因为有痕雪这个儿子。为了不让母亲后半辈再受父亲的气,痕雪毅然踏上了打工的路。
痕雪坐在车靠近窗户的位置,他看着形形色色的人从窗外一闪而过,看到了上学的少年、看到了吃草的羊群、看到了黄灿灿玉米挺拔的身姿。
“如果不是因为父亲的吊儿郎当,自己也大概和别的小伙伴们一起上学的吧?”,痕雪看着窗外的风景陷入了沉思。在一个车上坐的人大部分都是去外面搞副业的人,大包小包简直要把车顶给透和窟窿。
“你家孩子这么小要去哪啊?”
“不好意思,这不是我的孩子,他跟我一起去打工的。”汪伯看着众人诧异的眼神羞红了脸。
“也好,让小孩子去外面早点闯荡一下也好,多点社会历练和社会经验,也免得成了书呆子。”
车上的人为了不让气氛搞得特别尴尬才这样说的,没想到汪伯却当起真来,来自豪自己这么一个伟大的决定。
“来!来!同志,抽一口吧”,汪伯说着把自己手里的旱烟给了同车的人。
“不用!不用!不客气!”,车上的人都同时摇头。
痕雪还是看着窗外,一言不发,他想着家里的田地一定比他看到的肥、家乡的山也一定比看到的山要高、尤其是家里的人要比看到的要好些,这路边的人一个个穿的这么暴露,也不知道是要勾引谁,嘴唇染着口红、头发直溜溜的披下来,晚上就像一个鬼在行走一般。他们不像梦可看上去那样真实、那样单纯、那样的可爱,给人一种存在感,一种可望可即的幸福。
痕雪坐在车上,车行走在柏油马路上,他感觉到偶尔是车停了几下,痕雪就从沉思中回过神来,问汪伯是不是车坏了?汪伯就告诉他车是在过红绿灯。
痕雪到时希望此时的车是坏了,再也走不了了,最好是修不好的那种。那样自己就可以回到家中,重新回到母亲的身旁,再尝一尝母亲做的饭菜,那样的话即使是明天走自己也心满意足了,可汪伯的话使他的希望破灭了,不是车坏了,而是这该死的红绿灯。
“汪伯?你知道我们这是要去那里吗?”
“我也不知道,听他们说好像是往火车站的方向开的。”
“为什么要去火车站?我们不是去北京吗?直接让车把我们拉到北京到行了哇!”
“傻瓜,北京那么远,还不把车的四个轱辘给跑丢了呀!”
尽管汪伯给痕雪解释的再多,痕雪也是不明白,明明做火车也是坐、做汽车也是做、为什么还要倒车,不能直接开往北京,这在痕雪懵懂的年纪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同样也是不可理解的。
痕雪继续看着窗外的风景,渐渐的,树木消失了、田地消失了,他看到了很多的人聚在一起,还有很多的车在不厌其烦的打着车号,叫卖身,拉客声,都混成一团,当人潮代替了松柏,当人声代替了鸟鸣,这一切都让痕雪感到崩溃,那种滋味说不清、道不明,他瞬间感到自己晕头转向。
车停了,车上的人都下车了,他们大包背着小包,汪伯也背着一个大大的,红颜色的包,痕雪曾经问他背包干什么,他说是日常睡觉用的东西。
“汪伯,我们这是到了北京吗?”
“傻孩子,没到呢,距离北京还有几十公里呢,要想到北京我们还的做这铁轱辘跑一个通宵呢”
“我不要!我不要!我嫌累呢,我要睡觉!”,痕雪又耍起了孩子脾气。
“听话,伯伯给你去买一个卷饼吃,你不要乱跑,我们晚上听话的坐火车,好吗?”
痕雪一听自己可以有吃的了,就立即停止了哭喊,等待着伯伯把他说的那神奇的东西拿来。
一会儿,痕雪看到汪伯跨过了高高的栏杆,他那身躯显得一团肥胖,来到痕雪的面前时大气还在喘,手里拿着一个纸包着的东西,给痕雪送来。
痕雪拿过东西以后,看到爷爷所说的卷饼不过是一张饼里面含着一根火腿、还有几片生菜,饼上面所染着的油让痕雪吃了感到油腻,不时的怀念起了母亲做的薄饼,如果他此时不在去北京的路上,自己也许今晚就在吃着母亲做的香甜可口的饭菜!
“走吧,痕雪,我们该上车了”,汪伯的话让痕雪一下子从回忆中拉过神来,汪伯牵着痕雪的手登上了这铁轱辘。
当一进入车厢的时候,痕雪就有一种油然而生的呕吐感,脚气味、泡面味混杂在空气中,而这里面乘客的形态更是有多种,他们有的在睡觉、有的拿着手机看着什么东西,说起手机,痕雪是陌生的,在村里他从来没有看到过人们手机拿着这个铁东西,村子里的人家只有少数安装着固定电话。
痕雪在车里面坐着,他不知道一晚上自己睡了几次、又醒过来几次,只看得外面是一样的,黑乎乎的一片,和轱辘划过铁道的声音,旁边的汪伯还在聚精会神的看着行李,生怕有小偷来光顾他的全部财产。
车在走着,一刻也不停的走着,把痕雪带上一个未知的城市和一个模糊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