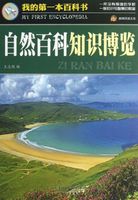“看来一般的比如符咒之类的东西对它们已经没有任何反应了!”她抽了口凉气说着。
“怎么讲?”
“我想知道你进去的时候身上带着我给你的那张符咒吗?”
“不带着我怎么敢进去?但是进去之后还是感觉害怕。”
“这就对了!这类东西对它们已经没效了。你进去后,我敢肯定它们就还在里面,符咒怎么会失灵呢?看样子它们也不像是很恶的那一类……”
“那怎么办?”
“我得去请我爸爸!”
“这不在阴阳先生的职业范围。”我有些不解的说着,阴阳先生的专利本来就是不驱鬼降魔。
她瞪了我一眼,说着:“谁说的,有的阴阳先生也兼职捉鬼哩。”
我笑了出来,这不是瞎扯淡吗?阴阳先生还带捉鬼的?难不成我这个外行还真不懂?
“问题是,你不是不想让你爸知道你在哪吗?难道要接受娃娃亲了?”我笑着问道。
她瞪了一眼,说:“那倒不是,只是万一这种厉鬼果真对符咒没有表现出任何反应的话,那就说明这不是一般的厉鬼!说明它并没有投胎做人的打算,这就是个大麻烦了!不过给你说了你也不懂!问题是万一它残害其他人怎么办?”
“我懂,你的意思是说,这种厉鬼想必是在人间还有仇恨,所以它要留在人间报仇是吗?”
“确切的说,这种仇不小!尤其是那个小鬼,它留在人间更可怕,它肯定是一来到人间就死了,然后带着与生俱来的仇恨!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听她这么说,好像还有几分道理。我以前倒是听老人说起,再凶恶的厉鬼,只要是大师都可以让它去投胎做人,因为大师可以找到它们的仇恨根源,然后将其化解,但要是这种小鬼,那就麻烦了,它对世间的仇恨在它来到这个世界时就形成了,这正好与“人之初,性本善”相悖,是天注定的,要么让它自生自灭,要么将其打入十八层地狱!这貌似有点滑稽了!但确实有人这么说过……当然我也不知道说这话的老人是不是“内行”,尽管如此,也总觉得他们的话有那么一丝道理。
半晌,我说:“万一在我进去后,它们就没在里面呢?这个该怎么讲?”
她说:“这不可能,那房间就那么大点,它能跑哪去?”
“可问题是我并没有看见它们的踪影……”
“你不是说天花板上有血字吗?”她有些不耐烦。
我说:“是的,是两个字:离开!”
“这就对了,它们一定是在里面,而你的符咒却没有作用,不然就不能解释它们从里面安然无恙地走出来……”
目前令我纳闷的并不是这一点,而是为什么那个女鬼在进去的时候蹑手蹑脚,还有些害怕的样子!这是我无法理解的。随后我表明了这个问题,然而,她也表示这不好说。
整个后半夜,我都不曾睡着过,脑子里浮现出了越来越多的杂乱的东西:假设这一切都不是真实的,那该怎么解释?是阴谋吗?问题是就算把它当成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那也找不出实施阴谋所针对的合理对象。
见过鬼的人就只有我和一一,不可争议的是,我绝不是“合理对象”——我了解自己,我并没有任何值得别人注意并引起策划阴谋的那种利害关系。相反,我倒觉得一一肯定是此次阴谋(如果阴谋的确存在)的最终受害者,当然,关于她的一切我并不是很了解。
那么,问题又来了,倘若这一切都是真实存在的,那该怎么讲?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难不成真见鬼了?
次日,醒来时只感觉头特别疼,好像里面的东西都被谁掏空了一般。
来到客厅,一一早已坐在沙发上了,看着那身行头,估计是要走了。
她见我便说:“我以为你死了,这么久才出来。”
我倒了杯水捧在手中取暖,说:“可不是吗?这和死了一样呢!这几天发生的事基本没让我睡好。我可真担心我这身体吃不消,我感觉我应该搬走才好!”
“很快就没事了,今天我回去请我爸来,一切问题都会解决了!”她边说着边整理行李:“好了,我该走了!”
“大概多久回来?”
“一两天吧,拜拜!”
最后,我目送她下楼去,她去到街上时,还向我挥了挥手。
我回到客厅,坐在沙发上,仿佛还听见行李箱的轮子辘辘的声音,渐行渐远。现在,感觉客厅空荡荡的,仿佛一瞬间少了很多东西一样。
突然,电话响了,那头响起了酒友的笑声:“喂?言川啊!你在哪呢?发地址给我,我马上过来?”
我发了地址给他。
瞬间,内心也有了很大程度上的愉悦感——至少有个酒友要来还钱!这一天我等了多久了,尤其是在手头拮据的时候,能有人主动还钱,岂不美哉!南无阿弥陀佛!
我静静地等着酒友的到来。想想这久日子也是受够了,工作没找到不说,还近乎是坐吃山空,尤其是这几天的这些经历,更是让人身心疲惫,等他来了我可得好好和他拉拉家常!
很快,门外响起了有力不乏沉闷的敲门声。
“请进!正等着你呢!”出乎我意料,进来的竟然是房东。
这个胖男人进来后,倒是不客气的坐在茶几旁,看着一桌的酒菜笑着:“呵呵!我就说这小伙子行!我就知道你正等着我呢!看看都是些什么菜,嗯不错,这个卤味香猪脚,正好可以当下酒菜!”
说罢,他便把我的好酒从茶几上拿起,倒了两杯,给了我一杯……这可真是个蹭饭吃的家伙!
“嗯,胖老板(别人都这么叫,那我也得这么叫),亲临寒舍,有何贵干啊?”
他把嘴塞得大大的,说着:“你是不知道啊……我那房间要是租不出去,这个冬天可要饿饭哩……”
“你儿子不来接你去吗?”
“这个啊,可不好说,再说我不想让他们操心了,在这也挺好的,只是生活不太富裕……不过我都是快要进土的人了,这也不在乎什么。”
他说出这话我倒是很惊讶,这胖男人年龄可不怎么大啊,进土(将死之人)?怎么可能?他好像看出了我的想法,随后说着:“脑肿瘤,加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嗯!这猪脚味儿不错!”
也到是,这么胖的人,不得“三高”才怪!
酒过三巡后,这位蹭吃蹭喝的胖男人便谈起了令我惊讶的事,原来,他那间房子,在我之前的一位房客在去年惨死里面,随后的事情都不怎么太平。
他说:“那是个爱干净的人,对了,我给你说过那间房子的上一位顾客是在上个月搬出去的,其实也不无道理这么说。因为上个月才请了一个法师做法,但没想到后来你入驻后还是发生了怪事,这可不又请了个法师吗?”
“那她是怎么死的呢?”
“怎么死的?谁知道啊?她是个孕妇,看样子是怀孕三个月左右,在她死的前一天,我还看见个男人来找过她,结果第二天她就死了,死得很惨!”
“有多惨?”我把头凑过去(这时也有了些酒意)。
他压低声音说:“她的尸体是在楼下发现的,也就是说她有可能被从二楼扔了下去,但是后来警察说,找不到任何他杀的证据,唯一能证明是他杀的证据是……”
“是什么?”
他泯了口酒,继续说着:“被斩首了,头不见了……”
我瞬间感到胸脯一阵发凉,这的确太残忍了,很难想象凶手的歹毒……这倒是和我昨晚看见的手里提着自己的头的那个女鬼描述得不谋而合!
“那后来头被找到了吗?”我问道。
“一直没找到,嗝!不过要是找到的话,这个案子早就被警察破了。但也得这么说,嗝!即使找到头,也不一定能破,你看现在共产党都养了些什么狗杂种,只吃饭不干活的低级执法者!”
他这么说倒是令我惊讶,原来这个男人可算得上是个极端主义者呢。
他泯了口酒,纠正道:“但也只是部分执法者,嗝!那个女人多惨!为什么就查不出凶手来呢?真是饭桶!不!是装馊食的桶!”
听他这么说,好像是在假设他要是那些执法者的话就能破案似的。
我说:“那万一不是人杀的怎么讲?”
“怎么?小伙子难不成还相信是妖魔鬼怪杀的咯?”
“这世上的确有鬼神,这是我看见过的!”
“不不不!绝不是!嗝!绝不是鬼作怪。”
“你怎么就这么肯定?”
“这个嘛,是出自个人感觉……”
“那倒未必吧!”
他顿了顿了,说:“也可以这么认为,但我不是什么执法者或是什么有权有势的人,所以我说的话谁信?我曾去派出所提供线索,但那帮家伙就是不信,还说我老糊涂了,这叫什么事嘛,荒唐!”
“线索?什么样的线索?”
“我以前是做屠夫的,那是在我年轻的时候,我知道猪的头颅怎么卸下来,当然,人和猪也没什么区别,你应该懂我的意思?”
“怎么讲?”
“我只是想说,某些电焊工以前也是当屠夫的,这是他说的,我估计他正后悔说这话呢!”
这时,我突然恍然大悟,原来是那个楼上的电焊工,难不成看起来如此随和的人竟是杀人凶手?
不过我继续问道:“那你怎么就这么肯定是那个电焊工呢?”
他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小声点!我也不确定是他,只是怀疑而已,怀疑,你懂吗?这小伙!我在这里居住十多年了,这老城区每到过年还是有一定的人家户要宰猪的,当然这就是我的工作了。后来来了那个电焊工,他是前年来的,有一次我们去围观别人家宰猪时,他和我聊起了卸猪头的手法,我一听就知道是个经验丰富的屠夫,他说他后来改做电焊了。”
“那他有妻儿吗?应该有吧?”
他干了最后一口酒,大声说道:“妻儿?怎么可能?他是个单身汉!在这居住两年了,从没听说过什么妻儿,当然也没看见过!”
我回忆起了昨晚看见的那位电焊工居住的房间,那窗户上女人喂小孩吃饭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