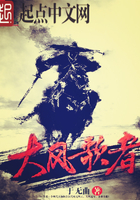安逸的生活,总是让生灵在懒散和随波逐流中不忍去破坏,而丧失了进取心。
巴巴享受着大王的待遇,意志消沉地混着日子。他也讨厌争斗,他也不想看见血流成河的景象,最关键在于,现时的他正欲想翩翩,正沉醉在各种幸福之中。他的下一代呈倍数增长,其中虽掺杂有其他霸王龙的后代,但他懒得去计较。他的部队刚刚经历过一场绝无仅有的霸王龙和翼龙间的战争,伤亡惨烈,急需新鲜血液和新生力量的补充。他似乎知道这一点。他童心未泯地和那些小辈厮混在一起,看着它们学爬行走路,学咀嚼进食,学嘶吼鸣叫,学排便撒尿,等等。他仿佛在它们成长的经历中找寻着自己该有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几只年迈的霸王龙可不乐意了。哪见过这种大王?也不管管族群事物,也不管管自己的属下,也不管管自己的三宫六院,也不对后代溯本正源,还整日和小龙一起玩耍,嘻嘻哈哈,唉!它们几个唉声叹气后,试图在族群中另立王以拥戴。它们环视一圈下来,不光体量上无龙能和巴巴为敌,且从眼中的精光中也无龙有巴巴那样的王者之气。它们只得作罢,又一起唉声叹气地以为族群总有一天会被别的族群消灭,而悲观至极;甚至,这种情况让那几只年迈的霸王龙的衰老速度都变快了。
族群的雌龙们,想法简单得多,一心只想完成自己的使命——生儿育女。它们在发情期发情,在生育期生育,在喂养期护犊子。因为巴巴从不“滥杀无辜”,所以它们都能看着自己的孩子破壳、阑珊学步、长大成龙。它们对这种变化有些无所适从,但它们从内心中希望是这样。过了发情期,带孩子的霸王龙雌龙是最可怕的动物,它们会对那些藐视和欺负自己孩子的动物赶尽杀绝,它们有这种能力。
巴巴的族群一团混乱。其中的雄龙,开始不断向外扩展猎食范围。它们经过和翼龙的大战后,仿佛突然被点醒了似的,竟然学着开始群体围猎,甚至开始学着使用“小聪明”伎俩了,比如:咬断树杈,扇打飞禽;尾巴击打砂岩,用沙石攻击猎物,等等。
所有这些只是为了吃饱喝足,它们那颗愚笨的大脑依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或者是变化太慢,让我没有耐心等待。我决定四处游历一番。
其他真冥天子都太高深莫测了,只有诺杰处的原始百慕大还能令我好奇,我寻迹而去。
﹌﹌﹌﹌﹌﹌﹌﹌﹌﹌﹌﹌﹌﹌
乙腊一世也在此处,跟着诺杰三世在海水中寻觅着什么。
“诺杰三世,乙腊一世,你们在找什么吗?”我看见他俩匍匐着,就问。
“怪了,肚脐眼就像消失了,好久都没出现。本来我还想显摆一番,让乙腊也享受享受泡泡浴,哪知怎么恭维它它都不出来了。”诺杰有些沮丧地说。
“喔,竟有这种事?”我说。
“嗯。”诺杰简单回答,又开始自己的寻觅工作。
乙腊和我彼此点头示意,相互间也没说起上次分手后的事情。他的注意力又被百慕大的神奇吸引住了,他没有心思理睬我。我知道他已经善于循金色线而行,而且我也发现他很合群,他可能受不了独自漫游茫茫宇翰的寂寞,因此知道他迟早会回到地球的。
看着他俩又开始仔细寻找蛛丝马迹,我也开始四周感知着黑漆漆海水掩盖着的海沟。
海沟整体“S”型走势逐渐形成;海沟上端变宽,底部收窄,还下沉了不少,形成一道深深的凹槽,像漏管,仿佛想要吞下一切。各种藻类生存于浅水区,其间优游着小体型成群结队的原始鱼类,像穿行在彩带中的小精灵;太阳光也只能穿透到它们这一区间,再往下就是黑幽幽一片了,就像宇空。在这片海底宇空中,数量上更少的中大体型鱼类,各自凭借自身的感触系统,警惕、缓慢地游荡着,玩着“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泥巴”、“大鱼避天敌”的种种把戏。再往下,那深深的海槽中则不再适宜地球孢子培育的生灵了,连单细胞孢子都没有,那里几乎不含氧,却有大量的氖气、氡气、氙气、硫化物、硝酸物等等充斥其中,只有数量极少极少的外来怪胎,艰难地在此处勉强求生,想要发展壮大则根本没有这样的条件和机会,荒蛮一如无物;但各种地球生灵的遗骸却堆积如山,被腐蚀被消匿着,让人无法查知海槽的真正深度。
在如此死寂之地,我的意识之思仿佛也被颠覆了,竟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这是地球在减肥呢!想秀一秀自己的腹肌呢!
我一怔之后,突然想看看此时地球的真实全貌。这种想法来得突兀又强烈,令我没和另两个真冥天子打招呼,直接瞬升而起,极速上窜,准备远远地看看这个大孢子。“噗嗤”一声,我和一物相撞相交相融,这一物就是地球孢子的儿子——月亮了。也正因为这次的相融,我才真正意识到父子间的那根无形的纽带,其中有血脉、亲情、包容、难舍、延续等等,也有矛盾、嫉恨、不解、讥骂、甚至打闹等等。我从没仔细查验过这根无形的纽带,这次自然不能再错失机会了。
我下意识瞪大了眼,什么也看不见。我这才想起:自己乃虚无之物,而那根纽带也乃无形之物。我试着闭目冥想,终于,一根捻绞的绳索出现在我的意识之海中。每一种情感和概念——血脉、亲情、包容、难舍、延续等等,矛盾、嫉恨、不解、讥骂、打闹等等——都是一根人类的DNA似的双螺旋线,盘旋却不相交地绞成一根有形的绳。无数根这种绳,又加捻、并条、合股,终于形成了那根粗粗的、完整但不完美的纽带。各种情感和概念都绞并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
我飘浮于中间,先看看父亲,又看看儿子。两个硕大的生灵,彼此敌视敌对着,毫无缓和的迹象,就那样生生地分离着;分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实际却装作一副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的样子。为人时,人世间一出出父子间的丑剧闹剧上演于我的意识之海中:
就像三皇(燧suì人、伏羲xī、神农氏)和五帝(炎、黄、颛zhuān顼xū、喾kù、尧yáo、舜shun),南朝刘义隆和刘邵,隋时杨坚和杨广,唐初李渊和李世民,清朝的康熙和雍正;其他文明古国亦如此;动物世界亦如此;国与国间亦如此;甚至连意识形态也难逃其祸,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与独裁……
多如牛毛,太多了,太多了!搞得我晕头转向难分对错,一声长叹后,我跌落在月亮上,没激起一丝一缕的粉尘,进一步证明了我的虚无。
哪家没有一本难念的经,清官尚且难断家务事呢!更何况我这么一个无实无用之物。不想这些了,反正这一世我是能经过那些朝朝代代的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与其听人传说,不如自己去经历后再判断。只是时间长了些,动辄数万年、数十万年,乃至百万年,我得遵循地球时间一天天地挨过,挨过每一个春夏秋冬,挨过每一个孤冷暗夜。你们便有福了,我寥寥几笔便是时光如梭、瞬间万年,你们便能轻轻松松知晓那些曾经的传闻轶事的真伪、历史本真的原貌了。当然有个前提,那就是不能得罪冥冥之中的那个谁了,得罪了则我将灰飞烟灭无影无踪,真冥天子之命既无,何来探究史实之旅,你们便也将无法随我一起弄懂虚空中发生过的和即将发生的事了。(哈哈哈,别信了,真冥天子姓甚名谁,何德何能,竟能有此本事!)
我悬浮于月球体表,遥望着地球,扒开它的外衣,它不再圆润、凹凸有致,一个真实丑陋的地球出现在我的意识之海。即使它自认血脉正宗,从外形上看实际和别的孢体没有多大区别,孤单单悬浮的傻大个一个,都歪七扭八没有正型,癞疙包坑坑洼洼,丑陋,荒漠,凄凉,因形成期的各种纷争,表皮上还沟沟壑壑伤痕累累,像衰老的皱纹,更被太阳孢子折磨得缺了一支胳膊(月亮)而残疾着;它无奈地被鞭打着旋转,一刻也不敢停顿,就像一只拉磨的瞎骡子;它既得对外打拼,还得对内哺育那些并不尊重它的细菌,同时还得任劳任怨,稍有牢骚则会给自身带来病痒;它明明是只公兽,却不得不扮演母亲的角色,还得装作心甘情愿的样子;它明明有一颗温度高达6000摄氏度、直径4000公里的炙热的心(内核和外核层,中心温度6000摄氏度),却偏偏要套上一件2900公里厚的圆领衫(地幔层),还披上一件17公里的灰旧、冰冷的外衣(地壳层),作出一副冷冰冰的表象。它实在可怜得紧!或许正因此,冥冥之中的谁才给它披了一件轻薄透明的“皇帝的新衣”(大气层),阴差阳错给它送来水这种物质,遮掩它的坑坑洼洼皱纹累累,又让它的细菌们动弹起来,好让它增添些许灵动,却没想到带给它的只是更多的嫉妒和非礼,无形中给它增加了太多的负担。它实在太可怜了!更可怜之处在于:它至今都还没明白“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道理,沾沾自喜于自己和别的孢子的不同。呜呼,哀哉!
我不忍心继续观摩这个裸露的、皱纹满满的老父亲了。我放大自己的意识之感,包裹住它的儿子,又去感知着这个离家别父的浪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