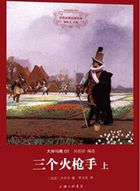第三章建筑工地
他们从那趟公交车上下来之后又走了很远的一段路,才终于在一个很宽阔的十字路口望到了他们此行的终点。
站在那个由铁路和公路交叉形成的十字路口上,几座耸立的还并不是太高的塔吊告诉他们,他们到了。
他们所在的这一建筑工地虽然也属于是县城的管辖,但离县城已经很远了。工地的外围是一大片空旷的土地,但土地上并没有种庄稼,除了一小片野草的绿色外,到处都是一片荒芜。
映入他们眼帘的这片工地很大,大到他们只是其中一栋楼里面一个单元的施工人员。
由于郭雷在谈合同时来过几次,所以他对这里很熟。
他们依然扛着他们那庞大而又沉重的行李,跟着郭雷的脚步朝属于他们的工作地点走去。
工地的外围是一堵用蓝色铁瓦围城的墻,墻并不高,冷冰冰的,给人一种监狱般的森严。墻的外面是一条坑坑洼洼的泥土路,偶尔有车驶过,荡起的尘土漫天飞扬。顺着这条土路和围墙走是两扇蓝色的大铁门,铁门上用红色油漆喷着四个醒目的大字,“长阳四建”。门的两侧又用白色油漆喷出了一副很算不上是对联的对联。
“精益求精坚决保证施工质量
真抓实干务必确保工人安全”
在大门外还站着一个矮胖并且有些秃顶的中年男人,那个人穿着一身不怎么得体的西装。一手叉着腰,一手夹着一根已经快抽完了的烟。正注视着这群向他走来的民工。
而郭雷看到这名矮胖的中年男人后,马上扬起嘴角,小跑着就跑向了那人的跟前。伸出一只手热情的对那人说,“李经理,不好意思了,晚来了一天。”
原来这就是郭雷口中的那位李经理,大腹便便,一脸横肉,确实像一个领导的样子。
只见那李经理不紧不慢的扔下手中的烟头,轻轻的给郭雷握了下手后,有些不悦的说,“我就是在这儿等你们哩,你们要是再不来,额都准备换人了。”
他把我说成额,大体上可以判断出他应该是陕西人。
郭雷只得再一次道歉并解释说,“真对不起!对不起!火车确实是晚点了。”
郭雷在说话的同时,还毫不心疼的把他那行李卷儿扔到了地上,只为能够腾出手来给那李经理敬上一颗烟。
那李经理结过了烟后,态度果然有些转变。他不再追究他们来晚的事了,改口说,“我先带你们到住的地方去。”
在这位李经理的带领下,这群民工们终于踏进了工地的大门。
一进入工地的大门,首先映入他们眼帘的就是那个巨大的地基,一个又长又宽的土坑就像是一块陨石砸到地面形成的窟窿。坑的四周用黄黑相间的钢管围着。坑里面秘密麻麻铺满了钢筋,就像是一个长满杂草的丛林,丛林里面散布着一些带着安全帽上的工人,这是工地上的钢筋工。
地基的北边是一条供人行走的小路,路的再北边也是用钢管围着,里面是是两个用钢管搭起来的棚子,根据棚子上的字显示,这里一个木工加工区,一个是钢筋工加工区。
顺着那条小路一直往里走,绕到他们工地的西北角,有一扇小门,出了小门便是一座用红砖水泥砌起来的小院,院子的也用红色油漆写着八个很显眼的大字,“安全生产,质量第一”
进入院子里,围墙东边是一排十间宽上下两层的蓝顶白墙彩钢活动房。靠着围墙的西边是一个长达数米,高达一米的水泥台子,台子上面是水槽,水槽的上面是一根布满了水龙头的铁管,铁管的另一端连着一个很大的塑料水罐。水罐的另一旁是厕所。这就是他们的工棚,是他们接下来一年内遮风挡雨,吃饭作息的地方。
所谓彩钢活动房,这种房子的主要的材质就是,薄铁皮包裹着泡沫。而这种材质的厚度一般不会超过十厘米,这也就注定了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冬天会很冷,夏天会很热。
李经理带着他们这一群人在一楼的其中一间门前停下后,他解下腰上的钥匙打开那扇门后,又对他们说,“先拨给你们两间房子先住着,你们一间做饭,一间住人。等以后你们再有人来了再给你们弄一间。”
郭雷笑着连连点头,但那李经理却突然又沉下脸说,“你们在这儿做饭归做饭,但是做饭不能用电。屋里面的电源除了照明和充电,啥也不可以用。谁要违章发现了是要罚钱的。”
工棚内不可以用大功率的电器,这是每一个建筑工地基本都在遵守的一条规定。表面上是怕形成电线短路,引起火灾。但实质上暴漏出的问题却是,大部分工地上的领导和采购,采购一些劣质的电线电缆给工棚内输电。而省下来的钱却都进了他们自己的腰包,所以这些领导们才会坚决捍卫这一规定。
这样的情况在温暖的季节里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可是一旦到了严寒的冬季,工人住在这简陋的工棚里,没有暖气,不能用空调,也不可以用电来取暖,面对严寒他们只能硬生生的忍着。
李经理把房间的钥匙拆下来交给郭雷后就走了。
郭雷看着那李经理的背影冲他喊道,“晚上有空请你喝酒啊!”
但是那李经理只是向后摆了摆手,连停也没停。
看着那李经理走远后,郭雷手下的这些民工迫不及待的就涌进了他们的房间里,由于有一间是厨房,除了郭雷大伯单独进了一个房间外,剩下的人都挤进了另外一个屋子里。
屋子里面除了四张上下铺的床之外,什么也没有。四张床分别靠四面墙放着,显得屋子里的空间非常的狭小。
这时郭雷又特意交代了他们一句,“都自觉点,让岁数大的住下铺,年轻的住上铺。”
其实郭雷的这种担心有些多余,由于这些民工都长期的在一起同甘苦,他们之间最起码的互帮互爱的精神还是有的。当郭雷说出那句话时,杨宇和杨树彬他们几个年轻的工人都早已把他们的行李扔到上铺了。
至此他们那庞大而又沉重的行李才算彻底离开了他们的肩膀,紧接着他们又开始把行李的里的东西一件一件的往外掏。他们的行李之所以那么大,里面的东西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除了被褥和一些衣服之外,他们又像变戏法似的往里面掏出了,锤子,手锯,尺子,扳手,碗筷,电动工具等一大堆的用品与工具。
上述所说的这些东西这都是这些工人都有的,而唯一不同的是,那几个年轻的民工还从他们的行李里掏出了一副刷牙的牙具,而那几个年老的工人则只有一条毛巾和一块香皂。
当他们这些人把这些东西都摆放好后,郭雷掏出手机看了看时间,见离午饭时间已近,便又对他们说,“你都先在这儿休息一会儿,我出去买点菜,中午咱自己做饭吃。”
杨宇听说后也想跟着去,便请求他姐夫,“我也跟你一块儿吧?我正好也买东西。”
郭雷不但没有同意,反而斥责他说,“你跟啥跟!想买啥我给你捎回来。”
郭雷之所以生气,显然是他这位小舅子没有理解他的用心。郭雷之所把这么一位不能吃苦,工作又不认真的妻弟带到工地,主要是想他自己不在时,还可以让他起到一个监工的作用。
但是,这些外地来的民工出于对新鲜世界的好奇,他们哪里肯老实的呆在屋子里。郭雷刚一走,他们都就又跑出来了。
他们所在的这个工地由于只是刚刚开工,大部分的工人都还没有来,所以这个时候工棚的院子里显得很冷清。
他们站在院子里出于无聊,就有几个人扒别的屋子里的窗户往里看,但是他们刚一凑近,就听到有人故意向他们咳了一声。
突入而来的一声把扒窗看的那几个人都吓了一跳,他们忙顺着声音回头看时,已经有一位满头银发并系着一条脏围裙的老头儿站在他们的跟前了。
老头儿见人们都把目光盯到了他的身上后,他又有些不好意思的笑了笑。
随后他操着一口极重的河南口音问他们说,“你都是新来的?”
这老头儿也许是还有些感冒,说话时不仅夹带着很重的鼻音,还往外喷着唾沫星。微笑时漏出的那几颗仅剩的牙齿也已经黄的有些发黑了。让人看了很不自在,所以也没有人愿意理他。
只有何世贵对他说道,“俺都是新来的木工,你又是干啥的?”
老头儿又说,“我给钢筋工做饭哩。那你们到这儿一天能赚多少钱呢?”
老头儿虽然吐字不清,但何世贵他们还是听懂了。这一个问题一下子让何世贵也变得沉默了。
工资同样也是工地上的民工们最不愿意提及的一个话题,由于他们长期内拿着这个社会最底层的工资,一提到工资他们就会有一种莫名的自卑感。尽管他们的工资在来之前工头儿就和他们讲好了的,大工日薪200,小工日薪150。也算不上是太低,但他们为了保护他们那份敏感的自尊,他们在遇到这个话题时,一般都是能回避就回避的。
但是那老头儿却一直在盯着他等待着他的回答,何世贵迫于尴尬最终才含糊的说了句,“也没多少,干的多也就赚的多。”
由于他们挣的都是日薪,没有双休日,更没有假期,上一天的班就领一天的工资,所以工作的天数多赚的工资也就越多。
但由于没有听到实际的数字,那老头儿又试探着问了一句,“那这栋楼25层下来,怎么着也能挣个十来万吧?”
何世贵却马上笑起来否认说,“不行不行,一年能挣个几万块钱就很满足了。”
出于对相同工种的敏感,这时郭雷的大伯也上前问那老头儿说,“老板一个月给你开多少钱?”
这时那老头儿使劲的往地上吐了一口痰,又拧了把鼻涕,然后伸出了一根还沾着鼻涕的手指说,“一千!”
一千,这个数字和郭雷开给他大伯的工资是一致的,也和绝大多数建筑工地上做饭师傅的工资是相差无几的。由于建筑工地上的饭菜既不讲究营养,也不讲究味道。馒头不用蒸,面条不用擀,用不了太多的技巧,所以工资向来都是很低。也正是因为工资低,所以在工地上做饭的大多都成了一些年近古稀,不怎么讲究卫生的老人。
相同的工资也让郭雷大伯的心理也平衡了,所以他笑起来又回复那老头,“不少不少,咱这做饭哩不能和干活儿的人比。”
那老头儿也连连点头表示赞同。
当那老头儿还正准备说些什么的时候,杨宇突然问他,“这地方哪有超市?”
老头抬起手来往北边的方向一指,告诉他说,“北边七号楼工人住的那块儿有个大的生活区,里面啥都有卖的。”
得知了这一消息后,这些初来乍到的民工便再也在这小院儿里待不住了。
他们很快就告辞了那做饭的老头儿,又顺着来时的那条小路,走过那片巨大的地基,再一次来到了工地的大门口。
这一次他们竟然意外的发现在大门口左侧还有一排彩钢做的房子。来时由于走的匆忙,他们谁也没有注意到。
这里虽然也是彩钢瓦的房子,但远比他们住的地方要高档的多。走进一些仔细一看,里面不仅有办公室,还有洗澡间,会议室,传达室,以及专门用来做饭的厨房,并且每一间房都配有一个空调。房子前面的空地上竖着一杆正在迎风飘扬的红旗,红旗下面停着几辆高档的轿车。原来这是领导们住的地方。民工习惯称呼这个地方为项目部。
任明看了几眼后,不禁感慨,“领导的待遇就是不一样。”
站在他身后的杨树彬以为他那是羡慕,笑起来调侃他说,“你是不是也想进这里边儿了?那你去问问里面的大老板还有没嫁出去的闺女了,你要给人当个倒插门不就进去了吗?”
一旁的杨宇听后也忍不住笑起调侃说,“有闺女也不行,他家里已经有一个了。”
任明听着他这两位工友对他的调侃,他不仅没有笑,反而有些痛心。同样是工作上一个工地上的人,领导们就配有专门的空调和厨房,而他们民工则只能睡着光床。而对于这明显的不公,他的这些工友们不但不意外,反而都已经不当回事了。习惯了卑微的他们,都已经忘记了呐喊,忘记了申辩。
正当杨宇和杨树彬他们两个正笑的欢时,突然一阵汽笛声划破长空传进他们的耳朵。紧接着一列长长的列车从他们工地的大门外快速的驶过。他们来时看到的那条火车道恰好经过他们工地的门口。
火车经过时,杨树彬惊讶的说了一句,“咦!这里还一条火车道哩?”
杨宇听后笑着对他说,“这不正好,等你回去的时候就正好就可以在这儿坐车了。”
杨树彬楞了一下,很快又反应过来骂了他一句,“滚蛋吧!这里又没有车站。”
杨宇脸上虽并在意,但仍趁杨树彬不注意在他后脑勺上拍了一下。杨树彬哪里又肯吃这个亏,瞬间又给还了对方一掌。等杨宇再想打回去时杨树彬已经跑远了。于是他们两个就像两个孩子一样在工地的大门口嬉闹了起来。
建筑工地上像这样的年轻人还有很多,二十六七岁,稚气未脱,正值青春的花朵绽放的最美丽的时刻,但迫于生存的无奈,注定了要让这最美丽的花朵开在这满是尘埃的建筑工地上。
他们这几个人一路有说有闹的走到七号楼的那片生活区后,果然发现了这里除了工人住的工棚之外,在工棚的外围还有一大片租借在这里的商店。
除了几家风味不同的饭馆之外,还有两家超市,还有一家五金劳保店和一家手机充值维修店,在这片商店的最末端竟然还有一家简易的澡堂。
商店的中间是一条临时修起来的水泥马路,路的两旁还有两个卖煎饼果子摊子,其中一个摊子的隔壁有一个老妇推着一辆破旧的三轮车,车上稀稀疏疏的摆放着几条烟和一些零食。
现在虽然还并没有多少顾客,但不难看的出等工人们都下了班之后,这里一定很繁华。
在很多人的意识里工地只是一个脏与累的代名词,所以很多人都并不太喜欢建筑工地。但是一座工地的存在却在无意之中养活了无数个生活在这个社会最底层的人。除了那些直接在工地上领工资的建筑民工之外,在工地的外围还有着数不尽的人在为民工与工地服务,他们的收入其实也都是来源于工地。
房子盖的太多,工程搞的太快是不是对的,我不清楚。但是我们却不敢想象,在现今这个社会状态之下,工地一旦不复存在,那些靠着工地生存的最底层的人,他们的生活将是多么的黯淡。
他们悠闲的徘徊在一家小超市的门口,从超市的外面就可以看到里面瓜果蔬菜,烟酒零食,一应俱全。但是他们却没有人一个人进去。放在超市门口几样果品让他们看的都有些饿了,而饭馆就在他们的跟前,却同样没有一个人有想要进去的打算。
这是因为这些民工常年来养成的节俭的习惯,让他们轻易的不敢花去自己的一分钱。生活中用到的一些东西他们都是从家里带来的,吃饭吃在工地上,能省他们就会尽量的去省。而在他们还没有开始赚钱的情况下,他们更舍不得花自己的钱了。
最终他们徘徊了一会儿后走进了那家五金店里,一些劳保用品是他们不买不行的。
那家五金店很小,不大的两间屋子里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五金劳保和建筑材料。
开店的是一对三十来岁的年轻夫妻,老板娘长的还颇有几分姿色,何亮在盯着那老板娘看时还被她给发现了。在两个人目光交织的那一刻,都瞬间尴尬的不得了。
那五金店的老板看到这么多人进来喜得眉笑颜开,忙拿起柜台上的香烟给他们每人都递上了一颗。
又热情的对他们说,“你们要点什么?这里啥都有。”
但领头的何世贵扫了一眼店里的货物后,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先看看”
对于他们这种冷漠的态度,那五金店老板也并没有介意。
他反而是注意到了另外一件事,由于何世贵在说那句话时用的是方言,正像是他老家的声音,这让他很是意外。
于是那五金店老板也换成了相同的口音又问他们说,“你们都哪儿的呀?听着像老乡。”
在这遥远而又荒凉的工地上听到熟悉的家乡话,让何世贵他们也同样感到一阵意外。
当他们都对彼此说出自己的籍贯后,他们果然是来自一个地方的人,而且住的还特别的近。
老乡之间的那种亲切感也让他们很快都打开了话匣子。
何世贵说,“你们在这儿干这个买卖行啊,工地上人那么多,每人每天买双手套就够你们赚了。”
五金店老板却谦虚的回道,“不行,指着卖这点小东西根本挣不了几个钱。在这儿也就主要卖点建筑材料。”
一座工地从预算的角度来说,材料的费用就可占到整个预算的百分之五十。除了钢筋水泥都是被一些大公司所承揽外,同样用量很大的如铁丝,铁钉等一些建材都是来源于一些小店。
这对年轻的夫妻所从事的就是这种生意。
所以那五金店老板在提到建筑材料时,让这些民工都感到无比的羡慕,纷纷夸耀他们生意做的大。
但这时这家五金店的老板娘却叹了口气说,“唉!也不好干。现在工地上都是赊账,帐还特别不好要。到最后如果要过来了还能赚点儿,要是要不过来,就得倾家荡产。”
听到这老板娘的感叹后,杨宇想也没想张嘴就说,“他不给就找人要啊,实在不行就上法院告他。”
杨宇这种不过大脑的回答让那开店的夫妇都笑了。
那五金店老板便又说道,“我们的钱和你们的工资还不一样,你们那是农民工的工资,他们不干欠,到了最后他们没钱借钱也得给你们。我们这打官司就算赢了也不行,以后还想继续合作哩,关系得搞好。”
五金店老板的一番话说的他们都沉默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拖欠农民工工资已经升格成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所以现在民工索要工资都并不是太难。但是工地上要账难的问题还依然存在,只不过被拖欠的对象从农民工的身上转移到了别的和工地打交道的人身上。而这所谓的别的人其实大部分也都是农民,也是社会最底层的人。
由于有些冷场,领头的何世贵故意转移了话题说,“你这儿有没有手套,我们都要。”
何世贵说完又用眼神征求了一下他工友们的意见,并没有人反对。
但是那五金店的老板听了这个请求后却有些不可思议。
他问他们说,“手套儿还得你们自己买?老板不管吗?”
何世贵并没有急于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先看了一眼站在他身后的杨宇。随后才有些无奈的说,“老板给的工资不少了,手套这一块两块的自己买也没啥。”
他这么说只是在照顾杨宇的面子,并不是他的工资就真的很高。
手套这种最基本的劳保用品一般都是由工地的工头给提供的,只是他们的工队例外。他们的心里当然也不满。但是碍于工头的小舅子在场,他们也并不敢把心里的这种不满发泄出来。
但是那五金店的老板却并不清楚杨宇和郭雷的关系,他听后有些气愤的说,“你们老板真抠啊,工人的劳保钱都省。”
何世贵傻笑了两声,并没有再说什么。只是那杨宇的脸上明显漏出了不悦。
出于老乡的情谊,那几幅手套五金店老板并没有收他们太多的钱。这让何世贵他们也感到非常的满意。临走时,那五金店的老板又特意塞给了何世贵一张名片,告诉他有事打电话。
他们从五金店出来时,时间已经过了晌午了,但是他们依然没有接到郭雷通知他们回去吃饭的消息,虽然饭馆就在他们的跟前,但他们强忍着肚子的鸣叫,就是没舍得进去。
就在他们徘徊在那条小路上不知该何去何从时,突然一道闪电从空中划过,随后便是几声闷雷,很快就下起了雨。这让他们不得不回工棚去了。
雨来得很急,他们一路小跑,从生活区跑回他们的工地门口时,小雨已经变成了大雨。
但他们刚一跑进工地的大门,一个让他们惊讶的发现放缓了他们的脚步。他们发现那些在地基里工作的钢筋工,现在都披上了雨衣还在争分夺秒的工作着。
于是他们人便把目光纷纷都转移到了他们那些命苦的同行身上,每个人的目光里都流露出了一种唇亡齿寒般的悲凉。现在他们眼里看的他们,就是不久以后的自己。
他们仔细的注视着那群冒雨工作的钢筋工,他们绑钢筋的手法依然那么娴熟,他们的表情依然那么从容,他们好像也并没有把下雨太当一回事。
在别的行业里冒雨作业,也许你会觉得多么了不起,但是对于建筑工人来说,这已经是家常便饭了,没有什么好稀奇的。
何亮看着他们,有些担心的说了一句,“对接钢筋还有电哩,他们也不怕被电着?”
但他的父亲却喊他,“管你啥事哩,赶紧走吧,一会儿淋感冒了再。”
他们这一群人回到工棚的寝室里后,郭雷依然没有回来。已经饿得不行的何世贵拿起他那用来吃饭的大茶缸子,又冒雨跑到水池子边满满了的接了一碗凉水。
他端起来一饮而尽,暂时解决了饥饿引起的难受。
他的工友们看到后,纷纷效仿。恰在这时一个人突然闯进了他们的屋子。
进来的那个人正是郭雷。
他一进门就匆忙的命令他的工人。“都赶紧出来,帮忙卸卸车。”
寝室的门外停着一辆红色的载客三轮,这是郭雷为了拉东西特意租来的。只见车里面放着一袋大米,一袋土豆,一壶油和一袋馒头,还有一罐煤气和一口大锅。除此之外,郭雷的手里还拎着一个很大的白色塑料带,里面看起来也像是吃的。
但是车里的这些东西让除了工头之外的每一个人都感到很失望,这一车的食物就是给他们准备的。但这同时也意味着接下来他们很长一段时间都只能吃白菜和土豆了。品种的单一让他们每个人都高兴不起来。
工人们七手八脚的把车里的东西搬进厨房后,郭雷看到了他们脸上的不满,但是他以为这是他的工人在责怪他回来晚了。
于是他马上笑起对大伙说,“都一定饿坏了吧,出去事太多给耽误了。中午不用做饭了,我从食堂买了点现成的。”
说完他就从自己手里那个白色塑料带内掏出来九个小的袋子,工人们走近一看才知道原来九份炒饼。
买回来的炒饼都已经冰凉了,但看来民工们那种狼吐虎咽的样子,好像那冰凉的食物依然是芳香四溢。
郭雷看他们几口下去就吃了将近一半,怕他们不够,特意又对他们说,“谁不够了,那屋还有馒头。”
何世贵却接过他的话茬命令他,“那给掂过来吧。”
郭雷于是放下了手中的筷子,亲自跑到隔壁又把那袋馒头送到了他们的面前。并且过来时他还又顺手从厨房里拿来了一头蒜。
他攥着蒜头对他的工人炫耀说,“这儿还有蒜,从咱老家带过来的,最适合赔炒饼了。”
就这样工人们的午餐又多加了一个馒头和一瓣蒜。冷却的炒饼加上冷却的馒头,外面自来水管里的生水再加一头生蒜,就成了他们一道丰盛的午餐。
他们吃的很满足,吃完后把那盛食品的袋子往门口一扔,都打着饱嗝就躺回床上休息了。
何世贵躺在铺上,百无聊赖。于是他掏出了他那部又厚又旧的手机,胡乱摁了一会儿后,就往自己的家里打了个电话。
他一共也没说几句话,给家里简单报了个平安后就把电话给挂了。
但他这个电话却勾起了所有人对家的思念,已经出门两天了,他们也都还没有给家里报个平安。
他们给自己家里通话的内容各不相同,但是通话的时间却都非常短。原因就是话费太贵了。
由于他们来时都是从老家带过来的卡,到了外地再电话长途加上漫游,一分钟至少要消耗一块多。即使随便说上几句,也够他们平时买上一包烟的钱了,所以他们都舍不得。
但是这个电话他们又不得不打,他们的家人始终在担心这他们,他们也都同样在牵挂着那个虽不富裕但幸福的家。他们为什么不辞劳苦甘愿到这几百里外的工地上滴血流汗?他们为的还是他们背后的那个家。家是他们最甘心的负担,也是他们最情愿的牵绊。
但他们队伍里也不是所有人都是那样幸福。在刚才大伙都在打电话时却有两个人例外,一个是郭雷,一个是任明。
郭雷身为工长正忙着研究明天施工时的图纸,所有没有时间打。但任明却不知道该把电话打向哪里。
任明在听到他的工友们亲切喊出一声娘或者他们妻子名字的那一刻,他痛苦极了。
他也有妻子,但他的妻子却已经不想再听他说话了。他如果贸然打过去,他得不到不但不是安慰与关心,反而有可能是更深的痛。
他和他的妻子在一年前也是相遇于这样一个浪漫的雨季。
他和她相亲时,他开着一辆借来的车。但媒婆为了增加他们两个人的成功率,就谎称那部借来的车就是他的。
于是那辆崭新,漂亮的汽车外形把她给吸引了。他也被她那迷人的外表所吸引。
但是这种夹杂着谎言的相遇注定只是一场美丽的误会。
再加上两个人的性格不同,结婚后他们的距离是越来越远。
再后来,他所在的那家工厂也因经营不善倒闭了。但只有高中学历的他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识字的文盲,为了生存,他迫不得已加入了建筑工人的队伍。可是这让她更加接受不了了。
今年过完年的时候,她和他正式分居,现在的他们只剩下一个夫妻之名了。
但他却很看重他们之间的这份感情,他并不甘心就这样失去他。他很像再去挽留一下。
出于这样的想法,他双手颤抖着还是拨出她的电话。
电话拨通后,他紧张的说,“喂,是我,我,我到这儿了。”
但电话那头却冷冷的传来了一句,“到就到吧,管我什么事。你有事吗?”
“我,我没事,就是想给你说一声。”
“那没事就挂了吧,以后没事别在打电话了。”
他虽然早已想到会是这样一种结果,但当这种结果真正要到来的时候,他给自己所筑起来的那道心理防线,终于还是崩塌了。
他盯着手机屏幕上他妻子的那张照片,心如刀绞。但是他强忍着没有让眼泪流下来,因为他的身边还有很多人在看着。为了不在工友们面前出丑,他走到了窗前。
窗外的雨依然还是淅淅沥沥。雨所包含的成分,除了水就是思念,而他现在感到却只有痛苦和无奈。
一些披着雨衣的工人有说有笑的陆续从窗外走过,这应该是那些钢筋工人下班了。
如果说建筑工地带给人的只有艰辛和卑微,那又为什么他们的脸上却洋溢着幸福和欢乐?也许建筑工地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有问题的只是人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