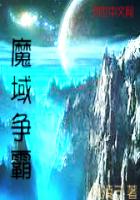初夏,凉州城城郊。
整整下了三天三夜的暴雨,终于歇住。在辽阔的天际边,橙红色的朝阳几经挣扎,从厚
重的云层里脱跳出来,给大地投下第一道耀眼的光芒。
这里是凉州的农业区,农田一片连着一片,广阔无顷,城中富庶人家的田产几乎都购置于此。农田边上是一块地势开阔的平地,零零星星散落着土黄砖墙黑瓦结构的低矮平房,间或有鸡鸣狗呔声传来,其中一片苍翠的竹林中,一角琉璃瓦飞檐堪堪探出头来,尤为引人注目。
梁婉清静静地躺在榻上,身上压着厚重的被褥,鼻尖额头处已渗出细密的汗珠。
她感到身上的被褥有些沉重,压得她有些喘不过气。
或许不是被褥的问题,而是自己的这具身子的问题。用刀子割了左手手腕的动脉,失血过多,在上躺了三天,意识才清醒过来,才感到几近虚脱的身子里力气在慢慢地汇聚回来。
说实在的,她实在很佩服原主的勇气。
但,绝不赞同。
浓密的睫毛动了动,她睁开眼睛,目光再次掠过四周的摆设。
这是一间很宽敞的卧房,南墙六道楹窗,皆挂上了湖蓝色的软纱,窗子半开着,阳光洒了进来,一地金光灿灿。柔柔的风吹了进来,软纱帘子随风逸动。榻附近摆着一张梅花小几,再过去就是紫檀木梳妆台,台上搁着一面铜镜,铜镜很是清楚,能倒映出人影来。用紫檀花嵌螺钿四季围屏隔开的另一侧,正中墙上挂了幅踏春图,下面是花梨木圆案,上面摆着一套景德镇官窑彩绘茶具。靠门处的墙角支起了一个藤木花架,青瓷花盆上养的是素心兰。
梁婉清记得自己第一次醒过来的时候,看到周围这古香古色的一切,惊得半晌动弹不得。
她记得自己是飞机失事,不想却穿越了。
她用了整整三天,在半昏迷半清醒之中,才接受自己都不敢相信的现实。
透过内室的湘妃竹帘,她听到有脚步走动的声音,然后是一个苍老带着威严的训斥的声音:“……何妈妈你说,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三姑娘好好的人儿,怎么就出了这么大的乱子呢?你是府里的老人,又是三姑娘的乳娘,这三姑娘可是你奶大的,你当视如己出,怎会疏忽至此?”
一听到这个声音,梁婉清马上条件反射地与脑海中的残存的记忆对上号:老太太身边的贺妈妈。
外屋里,何妈妈跪在地上,浑身抖若筛糠,眼睛哭得红肿,垂着头接受着贺妈妈的训斥,一句话都不敢说。她整个人精神几乎涣散,若不是勉强撑住的话,只怕早如一坨泥般瘫倒在地上了。
跪在旁边的小渔咬着唇,有些不忍心地抬了抬头。贺妈妈的语气未免重了些,如果说府里头谁对三小姐最好,只怕是除了作为乳母的何妈妈之外,再无他人。当看到自己视作亲生女儿般疼爱的三姑娘的惨状时,何妈妈当时整个人都崩溃了,拿着头就要朝墙上撞去。要不是小渔死命拉着的话,只怕是此时何妈妈已经去了。如果贺妈妈当时在场的话,定不会说这样的话。
看到小渔抬起头来,贺妈妈毫不客气地接着训斥:“小渔你也是,你是三姑娘身边的一等丫环,三姑娘心里面想什么,你该有个考量才是,凡事多为姑娘想想,平日里多往好的地方劝着点,怎么一点也不懂事呢?”
小渔紧咬着嘴唇,委屈涌到脸上。她素来知道自家姑娘是个莽撞性子,怎知道竟会冲动如斯!何况出事那天晚上并不是她当值,睡在外间睡得像头死猪的是春晓。第一个发现自家姑娘出事的人还是她。是她半夜出恭,不放心春晓照顾不周,推门进来看看,这才发现姑娘出了事。
看到小渔眼中的委屈,还有涌起的泪花,贺妈妈愣了一下,马上想到怎么一回事,不确定地问道:“难道那天晚上不是你当值……是春晓?”
小渔含着泪点点头。
春晓……
梁婉清记得,这春晓原本不是她屋子的,而是薛姨娘屋里的。听何妈妈说,八年前,薛姨娘屋里的丫环勾心斗角得厉害,年幼的春晓无辜当了炮灰,薛姨娘追究下来,饿了她三天的饭。就在快饿死的时候,此事被主持中馈的自己的娘亲苏氏知晓,看不过眼,让丫环给她端了一碗米汤,就是这碗米汤,救了她的命。
别看春晓小小年纪,心里面可是有算计的。她在薛姨娘屋里不过是个三等丫头,算计不过那些被薛姨娘极为看重的一二等丫头,于是便跟了梁婉清,做了管钗饰的一等丫头。过了几年荣耀的日子。八年前,苏氏殒,梁婉清在府里的日子虽不如前,但好歹是个正经嫡女,这待遇也不会差到哪里去。何况府里还有老太太身边的贺妈妈看着。去年夏天的时候,梁婉清因了一件事情被罚到城郊农庄思过,春晓也受了牵连,与何妈妈、小渔等人跟着梁婉清一起来到这里的农庄。远离了梁府,这待遇眼看着跌了下去,一直跌到了谷底。
此时,春晓的心眼又转开了。一年来,梁婉清带到农庄来的九子方漆奁,里面的首饰接二连三失踪,而春晓手头却日渐宽绰起来。听城里梁府暗地里传过来的消息,春晓近段时间以来与薛姨娘屋里的一等大丫头柳杏走得很近,经常往柳杏手里塞东西。
当年的的一碗米汤价值几何?势利的春晓早就忘了当年的一饭之恩,一心一意只想如何调回梁府,不在这里受苦。
贺妈妈环视了一下四周,果然不见春晓的身影。自家姑娘出了事,做丫头的却不知跑到哪里快活去了,这哪有一个丫头的样子?!但是目前,薛姨娘的风头较以前更盛……
权衡利弊,贺妈妈只得把快溢到胸口的怒火往下压了压,继续数落道:“这屋里屋外有你们两个,不管怎么说也得对那丫头防着点,怎么就疏忽至此呢?尤其是三天前那个头等重要的日子…….”她有些恨铁不成钢地看着跪在地上的两个人,“我不是早就托人捎话过来,一定要防着不能出事吗?怎么偏偏就出事了呢?这不是跟那边叫板吗?”
梁婉清记起来了。三天前,梁府大喜的日子,薛姨娘经过多方努力,依托镇守边关、位高权重的大将军胞兄薛泽的帮忙,终于替自己的儿子,梁府大公子梁玉明谋得一个七品县令的位置。而薛姨娘因了这事,换得老太太开了金口,抬为继室,身份转了正。两件喜事一直办,听说宴请了整个凉州城内的大小官吏、达官贵人等一大群有头有脸的人物及家眷,摆了整整十六桌,场面空间的盛大。
而这个原主呢,也不知道哪条神经搭错线,不想着薛氏荣升之后成了自己的母亲,以后自己的事情必受其管束。理应识实务,尽快送礼道贺巴结才是,以期以后的路走得顺畅些。反倒背其道而行之,于夜深人静之时,大咧咧地来了个割脉自杀。这不是明摆着就是抹薛氏的颜面吗?
外间传来“咚”的一声,似乎有什么栽到了地上,紧接着传来小渔的惊叫声:“何妈妈……”一阵捶背顺气的忙乱声之后,外面这才传出何妈妈气若游丝的声音:“贺妈妈,事态真的有这么严重吗?”
“三姑娘不管怎么说,这名份上依然是梁府的三小姐,与那边对着干,你说说严不严重?”贺妈妈冷哼一声,声音陡然转厉,“当天夜里,当消息传到了府里,薛氏当时就跑到老太太的屋里头闹了起来,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说自己不当这个继室了,这个府里上上下下就没把她当正室看待,朝脸上贴了金也没用。还说自己生来就是个姨娘的命,就连个正经嫡女也看她不顺眼,容不得她好。老爷当场就掀了桌子,说反了反了。老太太急火攻心,半天才顺过气来,当时就说了,断了三姑娘之后的月银,让她自生自灭去……”
何妈妈脸色刷地白了,嘴唇哆嗦着,好半天才吐出几个字来:“老太太……真的说了要断了我们的月银?”
自从到了城郊后,这月银明里是说按着以前的例份给,其实是变着法子苛扣。按小姐一个月三两银子,她与小渔一两半银子的例份计算的话,每个月她们应得六两银子。但实际上到她们手头的,最多的时候是一两银子,多数时候是一两银子都没有。但是好歹有这份月银在,即便是七扣八扣,剩下些渣沫,在农庄这个地方,买些米粮维持生活,还是转得开的。如果真的断了这份来源的话,让她们这一屋子一老二小的,喝西北风去?
何妈妈本来要比何妈妈还要年轻一些,因着这些年的操劳,忧心日重,竟过早白了鬓发,脸上也有了深深的褶皱,乍一看的话,竟比大她一轮的贺妈妈还要老上几分。
贺妈妈深深看了何妈妈一眼,终究还是不忍心。她唤小渔将何妈妈搀扶起来,见四下无人,迅速从袖袋中取出二两一锭的银子共五锭,塞到何妈妈手里,压低声音道:“这些银子你且收好,省着点用。老太太那边我会瞅准机会给三姑娘求求情。毕竟是梁府的骨血,老太太又是个吃斋念佛的,断不会放任三姑娘就这么没了。”
说到这,贺妈妈深深叹息一声:“即便过了这么些年,老太太这心里头,还是装着苏氏与二公子的。就凭着这一点,我也好劝着点。等到哪一天,三姑娘越闹越不像话,把老太太心里面这点念想给消磨殆尽了,反生了恶意,只怕是我再劝上千句万句,也无济于事……”
何妈妈一听,心里面一激灵。贺妈妈的话说到这份上,算是半劝导半告诫。她跪了下去,恭恭敬敬地磕了个头:“贺妈妈把这份担心放到肚子里便是,我即便是拼着这条老命,也要维护三姑娘的周正,绝不会再出这样的事情。”
贺妈妈受了她的礼,算是应了她的承诺。待何妈妈磕完了头,一把把她拉起来道:“我们都是老姐妹了,也用不着这些虚礼,我的话你记下便是。对了,三姑娘的药快熬好了吧,那个把三姑娘救过来的神医呢,带我去引见引见,得好好谢一番才是……”
说着,脚步声渐远,想必三人俱已出去了。
梁婉清有些疲惫地闭上眼睛,这么聚精会神地听了这么久,真心觉得累,看来这个身子真是太孱弱了,居然连认真听别人说话都吃不消。
眼睛虽然闭着,脑子里却急速地转开了。原主自杀时间是三天前的晚里,消息也是夜里送到梁府里去的。而接下来的三天里,下了特大暴雨。三天后,大雨歇住,老太太才让贺妈妈过来看望。这老太太对于她这个亲孙女,到底是亲还是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