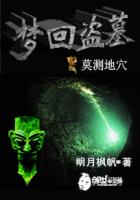不怪木安安着急,这事不仅仅关乎赔偿金,还关乎她木家百年金字招牌。
她去报道的第一天就无意听说病患已经连续赶走了五个医生,她早在导师面前夸口,自己绝不会成为第六个。
凌晨三点,G市锦华别墅区内,一丛矮木林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突然有三个人笨手笨脚地爬出来,领头的就是木安安。她压低声音吩咐两个师弟:“反正就按照我说的行动,我上去扒他裤子,你们在楼下给我守着。”
小师弟胆子大,拍胸脯说没问题,大师弟性格稳妥,挺迟疑。
“师姐,咱们这样做真的好吗?”
木安安戴上夜视镜,说:“没事,那家伙刚从庆功宴上回来,而且是被抬着回来的!再说,我也不干坏事,就看看究竟是内痔还是外痔才能对症下药嘛!”
戴着夜视镜的她看清了屋内的一切,她弓身从窗户跃下,摸进主卧,青年裹着被子卷,躺在豪华宽敞床中央。木安安果然闻到一股刺鼻的酒气,她窃喜地推开门。
旁汀穿着丝绸黑睡衣,没了平素不近人情的假面,浓长的眼睫毛像蝴蝶颤动的翅膀,在月光下随呼吸轻微起伏,但显然他睡得并不安稳,眉紧蹙着,让人不由得心生怜爱。
月光透过窗棂,哪怕夜空里最亮的星,也比不过此时惊鸿一瞥下艳色。
木安安暗骂自己见色忘事,她小心翼翼地扒开羽绒被,又绕道顺手的另一边,手指揪起裤头,眼看就要得手之际,青年猛地抽搐了几下,居然毫无预兆地睁开了眼睛--
木安安一下乱了阵脚,没来得及收回自己的手,下一秒手腕剧痛,竟是被人精准无误地抓住了。
第二天,包括小助理在内,许多工作人员围上来关心:“木老师,您被家暴啦?”
木安安肿着一边脸强颜欢笑,她是以营养师的身份陪同来片场,公司觉得痔疮医生这身份有碍观瞻,容易破坏旁影帝纯洁无暇的光环。她撑着下巴,懒洋洋地看着旁汀跟几个老戏骨酣畅淋漓地飙戏。大热天的演民国片,旁汀穿着一身三件套欧版西装把身体线条勾勒得极惹眼漂亮。
旁汀业内口碑极好,有天分又勤奋的人,做什么都不会失败。
旁汀下意识看向一侧,他今天难得耳根子清净。木安安没追着他絮叨,反而有种缺了点儿什么的感觉。
木安安一个人无精打采地坐在林荫下,娇小的身子软软地陷在椅子里,倒有些可怜兮兮的样子。旁汀开工前隐约听说了几句,休息时过去一看,眼里当即蓄起怒意。
下手的人太狠了,木安安半张脸青肿,鼓得跟猪头似的。旁汀升起一股无名火,但木安安垂着头一言不发,就是不肯透露是谁下的手。
“都被打成这样了还包庇他?能下这种手的人,无论什么理由都不值得原谅!”
木安安看旁汀恨铁不成钢的神色,脸颊又开始作痛了,心里涌起百般滋味。
昨晚一个拳头挥在她脸上的罪魁祸首,可不就是您老人家!
但显然旁汀是不记得的,他根本不知道那个深陷在梦魇里苦苦挣扎,因逃脱不得而十指攥着被角的人就是自己。昨晚她试着唤醒他,但无济于事,青年勒得她手腕几乎骨裂,他嘴里喃喃念着什么,她听得真切,旁汀说的是--
“别打我,求您了……”
他反复呢喃着这句,口气像孩童般充满了稚嫩的无助。在夜深人静的豪宅里,呜咽声与酒气将空气割得支离破碎,他遇到过什么?他在童年是遇到了什么事,是有人对他做了什么事吗?所以他才不愿意去医院,抗拒所以医生?
木安安正琢磨着这事,忽然被旁汀拉去保姆车里。他动作迅速,拿热毛巾贴到她脸上。她疼得闭上了眼睛,含混不清地着问:“你手里拿着什么?”
“问武指几个兄弟要的,独家秘方,你等我把药酒热一下。”
他口气恶劣得像对待一块不成器的朽木,但动作却是与之背道而驰的轻柔。
“看看自己,都丑成什么样了,顶着这样的脸还好意思做我的医生,不休息好别回来。”
“不行,我的病患在这儿呢。”木安安忧伤地,意有所指地看向他,“如果我的病患能乖乖吃药,早点儿给我看看,我才能了无牵挂地走啊……”
她疼得五官都皱在一起,还顾着这件事。旁汀怒意淡了一点儿,矜持着挽起衬衣袖,把助理叫过来,让人把木安安送回去。
“看看是别想了,吃药的话……我会稍微考虑下。”
毛巾捂着她的半边脸,热度仿佛会传染,也跟着热进了心里。助理说得对,旁先生的确是个面冷心热的笨蛋。
所以,她是真的想帮帮这个笨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