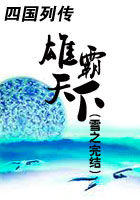一哲刚到镇子里,就感受到周围人们怪异的目光,一个平时关系不错的朋友看见一哲,上前打招呼同他寒暄了几句,便婉转的让他快点回家看,一哲听后不由得心里一沉,意识到家里出事了。
镇子到家很近,一哲快马加鞭一口气赶回家,远远的就看见自己家的大门前竖起一根白桦杆子,杆子上挂着一串黄纸在风中摇摆,那是乌拉人家中有丧事的标志。
在大门前的空地上搭着一座棚子,棚子前烟气缭绕,在夕阳中一片呈现一种不祥的氤氲。好多人围在棚子周围谈论这什么,一哲只觉得脑袋“嗡”的一声,他几乎是从马上摔下来的,随后跌跌撞撞跑到家门口。
围观人群看见一哲回来,主动为他让出一条路来,一哲跑到灵棚一看,里面赫然摆放着一口红漆棺材,那是赫青山很早以前为自己和老伴准备好的,当时一共准备了两口,这是其中一口。
灵棚里全是赫家族人,老根缓也在场,看见一哲进来根缓站起身,一双悲伤的眼睛看着一哲不知道该说什么。
一哲大脑中一片空白,他上前一把抓住根缓的双臂,“额其克,这是咋了?”一哲不知道棺材里躺着的是谁。
根缓似乎一夜之间衰老的许多,他挣脱一哲,用手背抹了抹眼睛:“不知道咧,今早他们发现的时候,你阿玛就已经...!“根缓没忍心将那个“死”字说出来,“他们说是狗日的狼人下的毒手!”根缓同一哲一家情同亲人,赫青山的意外死亡对根缓的打击很大。
一哲在瞬间奔溃,他一下子扑倒在阿玛的棺材前面,恸哭了起来:“为什么啊?怎么会这样啊!”一哲用力的在地上磕着响头,“阿玛,我回来晚了!阿玛啊!我对不起你啊!”撕心裂肺的哭声让周围人为之动容。
根缓一看吓坏了,赶紧上前拉住一哲,“臭蛋子,不能这么作遭践自己!”说着他使劲拉着一哲,阻止他那样不要命的磕头,其他族人也过来一同劝慰着。
“不要太难过了,人早晚都有这么一天儿!”
“就算你这样糟践自个儿,你阿玛也活不过来了!”
他们哪里知道,一哲除了伤心之外,还有一种深深的自责,一哲想起领巴图鲁奖章那件事儿,自己对赫家名誉带来的毁灭性打,还有后来阿玛去镇子上被冼秃爪子羞辱的事他也知道。
他一直觉得特别对不起阿玛,阿玛含辛茹苦的养育了自己,到头来自己不但没有报答阿玛的养育之恩,反而让阿玛因为自己受到这样的侮辱,还有大阿哥,他就是死在黑水人手下,可自己偏偏却执意要娶黑水女人做老婆。
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此刻一哲悔恨交加,嚎啕大哭,周围人只能不停的安慰,哭了一会后,根缓似乎想起了什么,他吞吞吐吐的对一哲说:“崖蛋子,你进屋去看看...你额娘吧!”
一哲已经有点麻木了,根缓说完便拉着一哲的手,陪他一起往院子里走,边走边安慰一哲:“你额娘没事,就是受了点伤!”
一哲额娘被发现的时候还剩下一口气,大伙将老太太抬进屋,随后有人去镇子上喊来了那个会看病的白萨满,结果白萨满看了老太太的情况后无奈的摇了摇头,“老太太内里受了严重的伤害,恐怕挺不过今天!”
随后白萨满给老太太灌了点自制的药水,快到中午的时候,老太太居然醒了过来。
她同族人说了大概的经过,但并没有提羿箭被抢走的事,后来有人从那个空墓穴里发现了冼法连的尸体,鉴于老太太的状况大家无法追问,但所有人心头都有若干谜团等待解开。
那些狼人为什么要袭击这对离群索居的老人?冼法连在镇子上已经失踪多人,为何如今尸体却出现在赫青山大儿子的空墓穴里?是谁杀死的冼秃爪子?墓中一片狼藉,到处是被翻动的痕迹,甚至连地面也被掘出了两个坑,那些狼人想在找什么?
一哲进屋看到额娘脸色苍白的躺在床上,他终究没能忍住,眼泪再度夺眶而出,他跪在炕沿边,两手握着老太太的一只手不停的轻声呼唤着,“额娘,我回来了!额娘!”
老太太还算清醒,听见呼唤睁开眼看着一哲,眼中流露出十分惊喜的神情,随后她缓缓的转过脸,注视着一哲,然后艰难的举起手,用指尖轻轻的触碰了一下一哲的脸,似乎想为一哲擦眼泪。
一哲几乎将嘴唇咬破才强忍着没哭出声:“额娘,你一定会好起来的!”但刚说完这句话后,眼泪却又不争气的又流了下来,一哲只好低下头,不让额娘看见。
“不要怪你...阿玛...你阿玛...一直都...都很...疼你的!”老太太虚弱的说,“前...段时间...你受伤,他...好几...次上山...给你套跳猫...“老太太断断续续的说,”他想给你...补身子!”
屋里还有另外两名族人妇女,听老太太这么说鼻子一酸哭了起来,一哲听后心中更是羞愧难当,“你别说了额娘,我不怪阿玛,是我对不起阿玛!”
老太太说完闭上眼睛停顿了一会,随后她让一哲打开放在炕梢的那个柜子,在柜子底部有一个精致的小盒子,老人从身上拿出钥匙递给一哲,让他将盒子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绸布包,老人颤巍巍的展开绸布,里面有一块写满字迹的白布和半块玉佩,随后老人用微弱的声音告诉一哲:“这个...是你的...亲...额娘给你...留下的,那个...白绸子上...写着你...的姓名...还其他...一些事!
一哲紧紧的将那半块玉佩攥在手里,然后哭着对额娘说:“你就是我亲额娘,我亲额娘就是你!”虽然一哲已经知道这件事了,但此刻在这种场景下老太太如实相告,还是让他十分动情。他有些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泪水在脸上恣意流淌。
老太太听后强挤出一个笑容,握着一哲的手稍稍用了用力,似乎怕一哲就此离开她不见,屋里这娘俩就这样牵着手,流着泪相互陪伴着,时光也仿佛凝固。
老太太休息了一会儿,艰难地抬头看了看屋里,屋里只剩下两位族人的妇女,“他敖科,麻烦您俩先出去一下,我们...娘俩要说几句话!”老太太说话比刚刚显得力气足了些。
两位女人听后连忙答应着走了出去,等屋里就剩下一哲同额娘两人后,老太太脸色突然变得严肃起来,“哲子,你不要怪你阿玛!”老太太说。一哲连忙点头答应着。
“不管...出了什么事,你也不能...怪他!”老太太继续说,气氛变得紧张压抑,一哲感觉有更糟糕的事情即将发生。
“昨天晚上,那些狼人...从咱家...抢走了...“老太太内心经历着激烈的挣扎,情绪变得不稳定起来,脸上的肌肉不停的抽搐着,一哲轻抚着额娘的手心,”额娘别着急,慢慢说!”他赶紧安慰老太太。
老太太呈现出一副痛苦又悔恨的表情,“那些狼人...将羿箭抢走了!...当年...就是咱们...赫家人...救...救的三足乌!”说完,老太太如释重负般重新闭上眼睛,再也不说话了,两行浑浊的老泪悄悄从眼角了下来。
这下可把一哲惊呆了,当年救起三足乌的竟然就是阿玛的先人,而且,那支全天下都在寻找的羿箭,竟然一直藏在自己家中,这怎么可能呢?他有些难以置信。
但很快往日的种种可疑之处便不请自来,在脑海中轮番浮现,并在此刻都有了一个合理的解释,离群索居的家、独一无二的墓园、大阿哥的空墓、以及自己曾因为偷进墓园挨打。
可要命的是,眼下羿箭已经被狼人抢走了!
一哲明白这意味着什么,狼兽族若是得到了羿箭,那么北疆的保护神就再也无法对它们构成威胁,即便如今三足乌已经复明。当年三足乌被射落的时候不就是同样正常的吗?
天下人都知道,羿箭是三足乌的克星,这绝对是关乎到整个北疆存亡的大事,关乎到每一名北疆人的安危!他感觉事态严重,这个的消息必须马上告诉大族长,否则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一哲不动声色的安慰额娘一番,并告诉她,自己找到了空青,而且就在中午的时候,三足乌已经复明。
老太太听后十分激动,握着一哲的手又用了用力,眼里露出自豪的神情,然后目不转睛的盯着一哲看,“你是赫家的骄傲!”老太太有种看不够的感觉。
其实一哲本打算告诉额娘,大族长已经亲口同意他娶塔娜,但看着额娘苍老的脸庞,他始终没有说出口。虽然大族长已经正式允许,但对于普通乌拉人来说,要他们真正从内心接受一个曾经敌对部落的女人,恐怕还要等些时日。
老太太平稳的睡了一宿,并没像那个白萨满说的那样发生意外,大伙都说这是因为一哲回来的缘故,但不管怎么说,见额娘平安,让一哲心中重新燃起了希望。
天刚刚亮,他就起来,然后出门喊起根缓,让根缓套上牛车,自己将额娘抱上车,“我没办法就这样眼睁睁看着额娘等死,我要去圣鸦堡找大族长,让苏勒大人救额娘!”
众人这时也已经知道一哲找到空青的事,高兴之余自然赞同这个决定,毕竟圣鸦堡的萨满国师,不是镇子里的普通萨满可以相同并论的。
两个时辰后,牛车径在圣鸦堡门前,引起周围人好奇的围观。侍卫进去通报后,很快便放一哲等人进去。
从昨天一哲走后,苏勒大人一直就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中,连晚上的梦也全是开心的事,让他笑醒好几回。
在自己的主导下,三足乌复了明,而自己并无需担心大族长的位置,这简直完美的不能再完美了,真是做梦都梦不到的好事,怎么当初就没想起那小子是中土人这茬呢,否则也不至于白白烧毁了望江楼。
但比起大族长的位置,那个酒楼显然变得无足轻重,大不了以后可以重建,正在高兴的时候,侍卫近来报告,说赫一哲求见,并说一哲用牛车拉着一个人来,苏勒以为一哲来领那些金贝来了,不由觉得好笑。
结果一哲一见到他,一下子跪倒在他面前,声泪俱下的哀求苏勒救额娘的命,这让苏勒有些意外。但一哲刚刚为北疆立了功,自然不好拒绝,苏勒便派人找来萨满国师,为老太太看病。
麻鞑看过老太太的伤后,轻轻摇了摇头,但随即又皱着眉说可以试试。苏勒将老太太安排在塔克图堡左边的城堡里,原来那是三族长的府邸,“你放心,北疆会尽全力去救助你的额娘!你们暂时就住在这,等你额娘的病好了再回去!”苏勒向一哲保证到。
根缓自告奋勇留下照顾老太太,等一切全都安排妥当后,一哲见四周无人,他走到苏勒面前,压低声音对苏勒说:“大族长,羿箭被狼人抢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