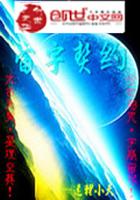“醒喇?你昨天去哪了?我睡的时候还不见你回来。”
苍若泣躺在床上,睁开眼,看到一张既陌生又熟悉的脸,愣了愣,还没意识到眼前的人是谁。他又闭上眼迷糊了半刻,才突然从床上弹坐起来看着桑穆,一副惊愕的样子。
“干嘛?跟呆B似的。”桑穆窝坐在被子里,脚上垫着电脑,瞟了他一眼。
“回来了?我真的回来了?”苍若泣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掀开被子看到自己正穿着睡裤的脚,又摸了摸自己的脑袋。
桑穆用奇怪的眼神看了他很久,托了托眼镜,“怎么,昨天被人拐走了?还是又作了什么乱七八糟的梦?”
苍若泣飞快地跑到厕所里照了照镜子,发现在那里长了三年的头发居然变回了原来的长度,样子也回到了二十四岁时的模样。“我失踪了多久?”他从墙后探出头来向桑穆问到。
“没事吧你?不就是昨天早上起来才出去的吗?”桑穆头也没抬,看着屏幕不停地敲打着键盘。
苍若泣像失了魂似的一下又摊回床上,两眼望着天花板直直地发楞,“难道只是作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而已?”他想着,“但是桑穆又说我昨天出去了,印象出我没出去啊…”他翻了翻身子,手不自觉地移到了被子边上,忽然像是摸到了一个什么东西。
“这是…”苍若泣将那个东西抓了起来,举到面前,是一个水蓝色的绸缎香囊,“我的天啊…”在那个世界生活了三年的一幕一幕瞬间无比清晰地在他脑海中闪过,那些朴素而精致的木屋,那些善良而勇敢的人们,那些简单而坦率的笑脸,以及那些真切而伤感的泪水。
“不是梦!那不是梦!”苍若泣大声叫了起来,他冲到桑穆床前指着那个水色香囊,脸红气促地说道:“你看你看!这是一个日本姑娘给我的,我回到了日本古代,在那里和很多武士一起打仗,对,对,是德川家康和武田信玄打仗的那个年代,我穿越时空了!”
桑穆极其无奈地听他发疯似的一口气讲完那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冷冷地笑了一声,边摇头边不屑地感慨:“唉,这年头神经病还真多,穿越时空?拍电影啊你。”
“你不信?是真的!我没有骗你,我…”苍若泣焦急地找遍了自己的全身,想找出几道在那个时候受伤留下的疤痕证明给桑穆看,却发现那些伤疤居然莫名其妙地全都消失了。“唉!”苍若泣重重地跺了一脚,闷闷不乐地坐回床上,一声不吭。
桑穆打了几行字,又转过眼看了他一下,“下午我和秋玥清她们想去医院看看老忽他们,你去吗?”
“老忽?”苍若泣想了半天才想起的确有这么一个同学,在另一个世界渡过了那么漫长的时间几乎让他忘记了这边认识不到几个月的同学,离开了这原来的世界太久太久,他开始有点怀念这个美丽的小镇,于是便想着借这个机会出去走走。“额…好吧,去看看。”
罗尔河上凉风依旧,明媚的阳光洒在鳞波浅荡的河面上,泛出一片澈净的安宁,绿意悠然的矮树林沿着河岸肆意伸延,几条小木船慵懒地飘着,林荫水影,美若宣彩。
碧蓝的天空里卷着几抹淡淡的浮云,它们随意地躺卧着,任那清爽的微风吹拂它们湿润细嫩的肌肤,让风将它们的这份清凉带与大地上的勤劳工作的人们,它们偶尔舒展翅翼,那绝美的翼弧华丽地勾勒出世界上最自然纯洁的曲线,随而轻羽四散,薄薄地染满了晴空。
风斜斜地吹着,撩起了苍若泣额前的几丝碎发,柔柔地摆荡。
“桑穆,星期天去教堂吗?好久没去了。”他笑着望向青山绿翠上的那座历练沧桑,却依然屹立的圣纳泽尔教堂,满心洋溢着喜悦的期盼和莫名的兴奋。
走在前面的桑穆背对着他不断地摇头,像是满怀伤感的老人般细语呢喃,“唉,傻的傻,痴的痴,现在连这个也开始觉得自己能穿越时空了,看来这房子绝对有问题,一定得搬了,马上搬,明天就搬!”
苍若泣见他一味地自言自语,不搭理自己,便想走上前去拍他,但刚走出两步,眼前的画面忽然闪烁了一下。
原本满目斑斓的世界像是瞬间洗去了色彩一般,霎时只剩下灰白的一片,时间的流逝有如放着慢镜一样,马路上飞驰的汽车,空中疾掠雀鸟的动作都突然缓慢得几近停止,现实中的一秒在此刻都仿佛被拉成数十秒那么漫长。
但当他将目光再次移到桑穆身上时,那惊愕的程度比他知道自己回到古代那时还甚。
在一片灰白无色的背景下,桑穆身上却是鲜明的一泼橙橘色,犹如带着生命般微微跃动着,细看之下还能看到那团橙橘又像是滴进几点淡彩的清水那么透明,那么的洁净,让苍若泣忍不住要伸出手去触碰一下。
但在他刚刚伸出手的时候,却发现自己的手居然也一同变成了桑穆的那种状态,不同的是,他看到自己的身体是暗红混浊的一片,像是有无数道愤怒的热岩在流动,而那些烫红的岩流上又缠绕着一丝丝如海洋般蔚蓝清澈的水线,两股极其矛盾的颜色各自向着相反的方向川流不息,这种连作梦也从未想过的情景居然在这个毫无预兆的时候突然出现。
眼前又是一闪,所有的事物又回复了原状,桑穆身上那橙橘色的光芒也消失不见了,刚才的一切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桑…”这变故实在是太突然太诡异了,苍若泣的脑子一下像被炸空了一样,两眼发直,呆在原地不能动弹。
“又怎么了?”桑穆叹了口气,无奈地转过身来,看到他像木头似的,便是一脸的不满,“干嘛?又穿越了?”
苍若泣听到声音,浑身打了个冷颤,意识才渐渐恢复过来,像是噩梦初醒般满脸冒汗,粗喘连连,他直直地望着桑穆,半天才说得出话来,“刚…刚才,我不知道…是不是看到幻象了,整个…世界没了颜色,然后…”
“车来了!快!”桑穆见到不远处的车站刚好有公交停下,便顾不上听他讲什么,马上跑了过去,苍若泣也只好跟在后面追着。
不算宽敞的车厢内稀稀落落地坐着两三个人,桑穆走到最后面靠窗的位置坐下,马上从背包里拿出耳机,自顾自地听起了音乐。
苍若泣本想让他摘下耳机听自己讲,但想了想,又觉得不太确定刚才看到的究竟是什么,是贫血的眩晕?还是一时的错觉?他不知道,只好挨在了座位的靠背上,将这一连串的怪事试着联系起来,看能不能想出些什么。
公车沿着狭窄的山路上爬回转,路上的车辆很少,两旁也是一片冷清,偶尔经过路边的咖啡馆才能见到三五成群聚着聊天的人,他们没有工作,靠着社会的救济过生活,无论是周一到周日都是那么地悠闲,这样的社会也不知是好是坏,以少数人的劳动便能养活整个社会,不工作的人也能得到温饱,这样的情况估计只有在发达国家才会出现。
车内的气氛非常安静,年迈的老妇人一脸慈祥地望着桑穆,松弛的脸皮却是红润光泽,米色的棉衣十分好看,桑穆见妇人看着自己,便对老妇人回以微笑。
他望向窗外,耳机里播着愉快的轻音,云飘万里,让他不禁又想起了他故乡的女友。
恬静的时光缓慢而悠长,却是流年似水,静静的来去无痕,就像映着斑驳树影的车轮,一圈一圈地,不觉,已至远方。
“咯咯。”白漆的木门被轻轻地敲了几下,清脆的响声充分证明着门板良好的质量。
“进来。”艾莉萝·洛翰摘下黑框眼镜,揉了揉疲惫的双目。
年轻的金发女护士捧着一叠文件走了进来,随手关上了门,“洛翰医生,这是圣歌勒精神病院传来的病人移交批准,以及其他病人今天的例行病况检查表,请您过目。”
“放下吧。”艾莉萝摊靠在椅背上,似乎十分困倦。
待金发女护士走出了门外,她才慢慢坐直起来,翻看着桌上的一份份报告表。
“移交将于四月七日下午二时进行,请做好病人的移交准备,以配合我方医务人员。”她拿起那几份移交批准表粗略地读了几行,“四月七日…”她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急忙翻了翻桌上的日历,“噢!天啊,不就是今天吗?批准才刚到,人马上就要来,有没有搞错?”艾莉萝气急败坏地将批准表往桌上一摔,撩起白袍便冲出了办公室。
“伽特妮娜!”艾莉萝在走廊上不断叫唤着,直到一名实习生模样的女护士从值班台后匆忙站了起来。
“又在看小说?”艾莉萝看着她手放背后,一脸紧张的样子,略带不满地问道。
伽特妮娜赶紧摇着头,一边将手中的书偷偷丢进了抽屉,一边挤出无辜的笑容分散着对方的注意。
“有什么好笑的,跟我来。”
“是,洛翰女士。”
还没走到病房,在走廊上就能清晰地听到从那里传出一阵她听不懂的说话声,艾莉萝皱了皱眉头,快步走了过去。
“咳咳!”她用两声假咳,代替了敲门声,站在了门边。
桑穆他们几个见到来了个医生模样的人,便马上不再说话,让到了一边。
“来探病的吗?”艾莉萝拿起老忽床前的病况记录卡写着,看也没看地对他们问了句。
“探病的吗?”见对方没有回应,她用眼角瞟了下,又重复了一遍。
“是。”卢逸安最早反应过来,点了点头。
“本来这么多人同时探病是不行的,不过反正等下就要转走了,也不管你们了。”艾莉萝将病况登记表往床尾一插就走到另一边。
“她说什么?”蔡镇铭把眼睛睁得老大,凑到人群里就问。
“说什么要转走。”苍若泣边说边看着众人的表情,发现自己似乎没说错。
“转去哪?”
“我怎么知道。”
卢逸安踌躇了一下,然后便踮着脚轻轻走近那个女医生,朝她欠了欠身,装出一副彬彬有礼的样子,“夫人,打扰您一下,请问您可以告诉我他们要转去哪里吗?”他不禁为自己流畅的语调而暗暗得意了一下,认为对方必定会为之震惊。
艾莉萝面不改容,用笔飞快地在登记表上画了几划,“L’hopitalpsychiatrique.”她说得漫不经心却又行云流水,顿时将卢逸安搁在了原地,转身走开。
“怎么了?”蔡镇铭又凑了过来。
卢逸安像是被泼了一身冰冷的凉水般,尴尬地挠着头,笑了笑,“我只听到医院,后面那个听不懂。”
“管他呢!转就转呗!”桑穆忽然喊了一声,表现得十分潇洒,扬了扬手就向忽孛冗的方向走了过去。
艾莉萝将房内六张病床的登记表都填了一遍后,走到门边拿起了墙上的电话就开始不停地说话,旁边的实习女护士却甜甜地对着他们笑。
“哇,你看,这女的好可爱啊!”蔡镇铭扯着卢逸安的袖子,猥亵地对伽特妮娜挥着手,不停上下打量着护士的身材。
桑穆走到老忽床前,伸出手指就使劲地戳着他的脸。
“你别欺负老忽嘛。”秋玥清似乎想用她娇柔的语调阻止桑穆,但明显是徒劳无功。
“你看,老忽多好玩!傻傻的躺着不会反抗,跟呆B似的!”桑穆直接将整个手掌压在忽孛冗脸上,来回地搓。
“别这样嘛。”秋玥清也忍不住走了过去,口里说着制止的话,嘴却笑得比谁都要灿烂。
“好吧,就这样。”艾莉萝挂上了电话,转过身来看到这群胡闹的中国人,原来阴沉的脸色更是罩上了几道乌云。她黑着脸叉手站在那,就像盛怒之下将要爆发的训导主任。
过了一会,四五个看上去壮得像头牛,臂膀肌肉隆隆突起,胸部涨得像是塞了两块砖头的大汉走了进来,看样子似乎是专职负责医院搬运工作的人员,他们和艾莉萝嘟囔几句后,直接走到了此时呆得像块木头似的卫蔚的床前将她整个抬到担架上,继而抬出了病房。
“现在就转移到别的医院吗?”蔡镇铭看着钟芷莉也被抬了出去,不自觉地哆嗦了一句。
很快,几个壮汉又折返回来,走到臧舜床前就要解开绑在他身上的束带。
“小心哦,这个可不好对付。”门角处不知何时忽然多出了一个人,那代表医生身份的长袍白得发亮,浅紫色的衬衣烫得不带半点皱痕,颈上系着金花墨绿底的领带,笔挺的西裤,擦得油光烁烁的皮鞋,衣着极其考究。他双手插在外袍口袋里,倚着门框,那又薄又利的嘴唇拉出几分讥扬。
“马提尔,你来干什么!”艾莉萝马上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柳眉怒竖。
那个男医生没有理她,只是满脸嘲意地看着臧舜,似乎在静静等待着什么事情的发生。
果然,当壮汉们解开了臧舜身上最后一根束带,打算将他移到担架上时,原本一直处于沉睡状态的臧舜忽然醒了过来,一甩手轻易地推开了体重将近两百斤的壮汉,扭身跃起,站在床上左踹右跳,其中一个壮汉想上前将其制服,却不料被臧舜伸手一爪抓到脸部,顿时被划出了几道血痕。
病房内一下子乱了起来,那些壮汉此刻就像是动物园里的饲养师要制服失控的野猴一样将臧舜团团围住却又不知从何下手,而卢逸安他们几个走过去想帮忙又插不上手,秋玥清和那实习女护士则吓得躲在了墙角,浑身发抖,只有站在门边得马提尔在暗暗地笑着,仿佛对这场闹剧感到十分满意。
苍若泣慌乱之中无意看了他一眼,却刚好看到他的眼,就在这四目相投的瞬间,刚才在桥上的情形又再次发生了,苍若泣只觉得眼前的景象忽然又闪烁了一下,然后整个病房瞬时变得灰白,和之前的感觉一摸一样。
他四下顾盼,惊奇地发现房间内所有人的身上全都有着那微微跃动的彩光,除了之前看到桑穆那橙橘色之外,其余大部分人都是近似土黄一样的颜色,只有臧舜、老忽和小简三个身上的光谈得近乎灰白,而那个靠在门边的男医生身上的光则明显和其他人有很大的区别,那颜色很浓很暗,深得像是褐色。
苍若泣正想走近去看清楚这些奇怪彩光的时候,周围的环境马上又变回了原来的样子,而且这次异状的持续时间明显要比桥上那次短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