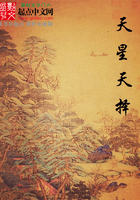第十八回
安内乱移军击河北
窥边备涉险探高阙
公元前208年,秦二世二年夏六月,项梁把十三岁的熊心扶上了王座。大概因为位出有源,人们复又把这个楚王推导为“怀王”,算个标签,一种用死者唤醒未来的期待。
楚的都城设在东海郡的盱台,地址在今江苏盱眙东北的官滩。项梁则移驻彭城,形成实质在北,旗帜在南的畸态。
楚国回归“正统”,陈婴接替项梁担任了上柱国,赐封五个县,平时就跟随在怀王左右。项梁自封武信君,黥布封为当阳君。当阳属南郡,地处今湖北荆门西南。
因为项缠的缘故,韩公子张良很快便进入了项梁的视野。出于帮弟弟报恩的心情,项梁提示道:“子房有心迹尽管表明!”张良流着泪说:“如今楚、赵、魏、燕、齐都已恢复,唯有韩国……”
六国借尸还魂,唯韩国还在墓中沉睡。可恰恰唯有韩,尚存一名货真价实的复仇者和代言人。项梁显然有意,便搓着手掌说:“是呀,韩国该如何办呢?”
张良虽然无力,但心理却是有准备的。见项梁主动发问,便说:“韩国的各位公子中,横阳君韩成最为贤能!”
已经存在五路诸侯,少一个韩不为少,再多一个韩也不为多。只等张良开口,项梁便表示支持。当下委派张良去寻找韩成。其实哪用得着“找”呢。
项梁派人到怀王那里打了个招呼,便立韩成为韩王。张良担任了韩国司徒,就此惜别刘季专心辅佐韩王,带着一千多人向颖川郡、南阳郡出发,去实质性恢复韩国。秦朝本相对平静的一隅,大小也要被搅起点波澜,这对项梁来说,没什么不好。
乘秦军疏忽,韩成、张良一举夺得了好几座县城,但在军事地理位置上也算得敏感的颍川,这种胜利只是暂时的。果然,一旦惊动了章邯所部,那些城邑便立刻被夺了回去。韩成君臣只好带着丁点儿军队,退到山地打起了游击。
战事进入一个相对平静的阶段,秦军动静不大,但肯定没闲着。张楚被剿灭,秦庭上下弹冠相庆。李斯和章邯内外主导,开始布局全面进剿。
内乱必致荒边。戍守阴山长城的主将王离奉命从北部军团抽调十五万主力,在上郡集结,东渡黄河,取道太原郡,出井陉口进攻赵国。大部队前脚开拔,留守原地的军卒便有所动摇,被迁来垦荒的人口也开始逃亡返乡。
对于秦庭来讲,这是一种信心加决心的表现。根据设计,河水南北双管齐下,全局将一举匡定。及至蛰居漠北的匈奴全面反应,王离大军也能迅速复位。总之,一切不足为虑。
南路章邯率军沿河水东进。首当其冲的魏王咎心知无力对敌,赶忙派相国周市去向齐、楚两家求救。诸侯唇亡齿寒,齐王田儋权衡局势,决定亲自率将军田巴、田荣去助魏拒秦。项梁也不甘落后,立即率军进驻胡陵,派侄子将军项它为先头,溯济水而上,紧急驰援。项它是项燕第三子项乐之子,与项籍、项庄为叔伯兄弟。
齐、楚两军离临济城十余里扎营。入夜,秦军发动了袭击。齐、楚两军猝不及防,大败亏输。田儋、周市死在乱军之中。项它悍勇,单骑逃脱,天亮收集败军,狼狈退去。
魏王咎却有份善良的心,想想自己死了也罢,却何故连累临济一城百姓。于是向章邯递交了降书,自己则引火点着了宫殿,****而亡。他的弟弟魏豹噙着泪水逃奔到了楚国,项梁拨予几千人,由他去与秦军周旋。
田儋的堂弟田荣带领残部回撤到东阿。秦将赵贲、杨熊随后追击,包围了田荣。当时的东阿在今山东东阿与阳谷之间,现地名阿城。齐国反对派势力得到田儋的死讯,便乘机拥立已故战国齐王田建的弟弟田假为齐王,田角、田间兄弟二人分别担任相国、将军。
北路秦军进展也很顺利,王离已经从恒山郡南下攻克信都。赵王歇、相国张耳、将军陈余被迫退守邯郸,也派使来向齐国求救。田假派将军田间前往救援。
项梁再度派司马龙且前往解东阿之围;原起于薛县的将军陈武也率领手下两千五百将士,作为友军前往助战。
龙且是一员悍将,陈武亦可谓善战,二将出其不意地发动强攻,赵贲、杨熊败退,放弃了对东阿城的攻打。
田荣得救,立即率军东返,驱逐了屁股还没有坐热的齐王田假、相国田角。田假逃亡到楚国寻求庇护;田角则逃往赵国,找田间去了。田荣扶立田儋的儿子田市接替了王位。田市任命田荣为相国,田横为将军。
项梁乘胜率军西进,与秦军战于濮阳城东。项梁这回也集中力量先发制人,诸将猛攻。秦军大败,章邯终于从速战的梦境中惊醒,迫不得已沉下心来专心琢磨项梁。他退据濮阳城内,下令环城掘沟引水,紧固城防。楚军猛攻,刘季所部樊哙率先攻上城头。秦军在城上发起反攻,两下展开了激烈争夺。最终,章邯还是不得不放弃了濮阳城。
仓促后退的秦军并没有远离濮阳。章邯开始调整方略从长计议,在防御上下功夫,终于遏阻了楚军的锋芒,双方进入僵持状态。
项梁亲率黥布、蒲槐等继续逼攻章邯,却派刘季、项籍向南迂回。此举攻防结合,在开辟南郡南、砀郡境内第二战场的同时,也遮挡了秦军从济水、睢水流域进袭楚国腹地的必经之路。
宫廷内卫首领郎中令赵高依仗二世的恩宠,专权跋扈,挟私杀害了许多官员。为了遮掩自己的滔天罪行,唯一的办法就是堵上皇帝的耳朵,蒙上皇帝的眼睛。本来,想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但这件事却可以由皇上自己去做。于是,他劝二世说:“今陛下即位不久,正当青春华年,何必在朝廷上与三公九卿论长道短,还必须被迫作出那些自己不乐意的决断,真太累啦!”
二世本能地逮住了话头,问:“青春华年?你说的是啥意思,啥乱七八糟的,我听不明白……”他真的听不明白,但倒是勾起了一丝心愿。
赵高从皇上弱智的反映中,看到果然能钻个大空子,偏把话题落在了别处,回答:“如果陛下的判断发生误差,作出个不合适的决定,那就把缺陷暴露给了众臣,很没面子,也要被那些人笑话,从此无法显示圣明……”
二世急了,问:“那可咋办呢?”
赵高推心置腹地说:“天子之所以称‘朕’,是因为天生高高在上。所以,本就应当让群臣只能聆听他的声音,却见不到他尊贵的容颜。”
二世面露喜色,击掌说:“哎呀,我明白啦,你咋不早说呢!”
说那秦二世笨拙不错,但过于笨拙的道理,在于另有用心。赵高清楚地记得,二世曾经问过:“人生居世,就像六骥过隙,青春易老。我既然已经君临天下,只想享受耳目所能企及的一切喜好,穷尽心里追求的所有快乐;由此却也能让宗庙安定、万姓各得其乐,达到天下长久、自己也终享天寿的目的,这能做到吗?”赵高当时回答:“这是贤明君主所能实现的,但却是昏乱人主所禁止的。”他知道皇上说的都是屁话,也便在回答中留下了明显的歧义,反正二世只会朝一边想。
冒顿消极着,长时间远离单于庭,甚至不去关照那一万“特种部队”,也不去左部处理事务。这一天,且蛰来告诉他,秦朝王离率领大部队撤离了北假,打内战去了。这是否意味着一种机会呢?二人计议未定。冒顿忽然生出一个冒险的念头,想亲自到阴山去看看,还要带莶扶一起去。且蛰有点担忧:“唉,这个胆大妄为的家伙,说风就来雨了!”但他还是同意了,并且决定亲自陪同前往。责任是一方面,其实他也想亲眼看看那个他曾经驻扎过的地方。
且蛰让曳当带了少量人马,与侥直那、屈烈支一起随同护卫。为了确保安全,他又调遣右大当户蓬奚率一千游骑随时接应。“要离得不远不近,眼睛睁大些,睡觉时竖起耳朵!”他叮嘱。
要绝对保证太子安全,也要避免与戍守的秦军发生无谓的冲突,这很是作难。好在有些时日了,匈、秦双方无战事,一线的敌意也不那么强烈了,方便的地方还擅自开关做起了买卖。且蛰哪里知道,此前冒顿已经擅自潜到雁门的集市上耍过一圈了。
大山的尾脊之间还算宽拓,但一路行走,仍难免盘岭绕沟,萦回迂曲。在姑且水末的湖边稍作停留,这里可以眺望浚稽山西、东两座山峰。然后看山不走路,走路不看山,迤逦到达蒲奴水尾,那里是冒顿出为人质时走过一段的位置。擦过夫羊句山狭北,一行人马逐渐进入荒漠地带,十分行程已过其六。
下一段直线距离还有六百余里,可见冒顿、且蛰这“玩”的兴致。一路不紧不慢到达沙砾地带,总是影影绰绰的阳山于不知不觉中清晰起来,高大起来。所谓“看山跑死马”,行程尚有近百里,但毕竟快要到了,一行人不由得活跃起来。
东西走向的阴山山脉全长1200公里,海拔一般在1500米到2000米,西端的阳山、也就是现代所称的狼山相对高出,海拔2364米。这是一座古老的断层山,由于环境形势北高南底,所以北坡山势平缓,而南侧断层则高峻陡峭,俯瞰河套平原相对高差达到1000米。山间形成许多垭口,现在叫作吴公坝、昆都仑沟的峡谷,都是山系南部重要的通行孔道。
莶扶在全家被驱逐到大幕以南后,每天在自家的毡房前,抬头就能看到绵延的阴山北。她甚至还大着胆子和家人一起,在已经不那么敌视的秦朝守军面前,自由地通过长城隘口,沿石门水去九原附近交换物品以补充和调节贫乏的食品和家用。但此时此刻看到阳山,她的心情完全不同了。她激动,直是朝寸步不离的冒顿,朝偶尔看她的且蛰,朝始终守卫在一旁的侥直那、屈烈支、曳当,朝因为有了她而精神亢奋的卫士们报以微笑。持续得久了,面部的肌肉有时有些僵硬,但她发自内心。此时即使让她去死,也会面带欣慰。
晚霞漫天,把阳山层迭的山峰映照得通红。阴山形势如一只跃动的豹子,阳山恰如豹子高高耸起的尾嵴。现在这支重量级的冒险者队伍就暂歇在“尾嵴”下边,从容地扎好毡帐宿营了。明天赶早出发,他们要在太阳升起的时刻,登上一座足以远眺的山峰。
躺在毡帐里,拥抱着温情的莶扶,冒顿竟然设想起父亲带着小胭脂夷莪巡游余吾水的情节。夷莪能享受到的,他要让莶扶都享受到;夷莪享受不到的,他也要让莶扶享受到,这就是他带莶扶来冒险,来寻求刺激的直接动因。当然,本质的目的不这么简单。
半夜起程,冒顿、且蛰一行人化装成牧民,骑马循着山里的道路,绕过几座山腰,跨过几道山谷,登上山头仰眺,逶迤雄居山脊的长城映入眼帘。太阳正从东边升起,把长城曲折而豪迈的身影投射到了起伏的山峦上。
雄心、好奇和刺激,使冒险心理随着太阳升温。由屈烈支小心翼翼地试探着开道,小队人马沿陡坡上的小路来到城下,辨认了一下,这里就是高阙的关楼。已经五年多了,且蛰的骑士们就是迫于蒙恬大军的威力,从关下的峡谷中,最后一批退出狼山的。
眼前仍旧是那座早年就存在的军事工程,看上去确实经过了修整加固,墙垣完好。然而,城垛边却没有发现戍守的军队。在越发的好奇心的驱动下,他们下了马,顺次向城上谨慎地攀去。
屈烈支探头看过一遭,的确没有人,便跃身登城,卫士们随后鱼贯而上,向四边守望。冒顿一手拽上莶扶来,在城上拉着手看过一圈,然后说一声:“自己玩去吧,要当心点!”
南侧的城下是高高耸起的峭壁,形势险峻远远超过城北。且蛰寻思,如果把两边的形势掉个个儿,即使善于攻城拔坚的中原人,又将奈何这道卓越的防御工事呢!他笑了,可惜匈奴骑士不但不擅长攻城,而且也极不善于防守。
左、右两位屠耆王左右站立,匈奴的第二、第三号人物边看长城翻山越岭气势恢弘,边在头脑中搜寻和调动全部的历史知识和传说,想晋赵燕秦分合吞并,匈奴往来,战和交替,光阴瞬息,物是人非,不由得感慨无限,也助长了气吞山河的英雄之志。
长城垂下的屏障,把整个河套平原狭长的水草地彻底圈护在怀抱里。遥望似乎能看见河水,那是一条水流浊黄的宽阔的大河,河面旋流相接,水下暗流跌荡。河水那边就是河南地。冒顿和且蛰也都曾去过河南地,据说,他们的祖先曾经在那里游牧过。
河水率意地抛着大弯,向北,向东,向南,再向东北,大气磅礴奔流到离这里很远很远的大海去。入海的那一段就在匈奴左部的南面,也不一定离东胡的草原更近,却与匈奴如今的游牧地隔着重重叠叠的山川大漠。冒顿真想看看河水从哪里流进了大海,是怎样流进大海的,大海又是啥样子。可眼下,命运在旋涡中挣扎过后,正逆流而上,还不知终究会把自己带到什么地方去呢。也许在经历艰苦磨砺之后,他将成为大匈奴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单于,也许……他有一个巨大的梦想。
河水宽阔地从山地流出,从富饶的长满庄稼的平原上流过,朦朦胧胧听说过,在那里它也流经传说中的匈奴远祖夏族的发祥地。遗憾的是,匈奴人从来也没有能深入到那里。
高阙朝北与姑衍山隔大幕直对呼应,西南与月氏北山越流沙遥遥相望。且蛰在注视着,好像能看到什么。他能看到什么呢?
冒顿一路十分注意且蛰。他看且蛰的举止,回味他的作为,与他长谈,这才惊叹于这位兄长洞察形势,善思练达,胆识俱备,行为有度,心下便日益尊重。现在,他们并肩俯视,指点山河,心里成长着许多默契。
脚边是一溜蹬道,也还齐整,只是在石缝里露出许多草茎来,透露着防御的疏怠。蹬道下边,连接着一座规模宏大的军城,从上面俯看,一目了然。城内营舍井然,但却旗帜寥寥,也许时候尚早,还未见有几个士兵的踪影。
周围忽然警觉起来,屈烈支在悄声招呼卫士们,侥直那和曳当已经守候在两侧。原来,一队步兵沿着随山势而错落的城墙远远巡逻过来了。秦军竟然只巡逻,而不驻哨,包括高阙这座不可不防的要塞!难道夜晚这里真的无人值守?
必须赶快撤离了。冒顿走到一堆柴草面前,踢飞了一截树柴。一般来讲,如果发现敌骑,了望哨是要用它们来引火的。夜晚燃火光,白天熏狼烟,这虽然只是一种传递敌情的方式,但对于匈奴人来说,也能形成直接的心理威慑。这一点,冒顿心里清楚。
迅速返回城墙边,上马遁入山中。回望高阙,冒顿暗暗感慨。他意识到,如果秦朝无法控制函谷关以东向河水以北、江水以南大肆蔓延着的混乱局面,大匈奴返回北假也就指日可待了。然而,还得耐心往后看。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要牵动单于庭和整个族群,没有充分的准备不足以发起。难以处置的还有月氏和东胡,各方面互相牵扯,得拿出足够的智慧来应对。说到底,自己内部也不是轻易摆得平的,父亲不时唠叨返回北假之类,只算是过过心瘾,跟闹着玩似的。还不到时候,冒顿不愿意想得太多,更不愿意想得太具体,他希望自己的身心能更加放松些。他向莶扶摇摇鞭稍,示意向自己再靠近些。
巡逻近来的秦军朝关楼上放声吆喝,城关激荡,弄得冒顿一行格外紧张起来。完全出乎意料的是,关楼上竟然有人应声了。原来,那上面有人戍守,想来是一夜劳累,凌晨当不住困乏,就躲到碉楼的某个角落里睡熟了。
冒顿、且蛰等心中吃惊,也感到这个凌晨是如此地荒唐,又如此地侥幸。正这时,队里的一匹战马发出嘶鸣,回声响彻山峦。这一下,卫士们慌乱起来,纷纷张开弓弩,以备敌骑来寻。
关上的士兵拥到了墙垛口,一齐朝这边张望。张望了许久,大概再没有发现动静,竟然也就没动静了。
冒顿越发觉得,虽然对方的懈怠引起了自己一行的误读,但大伙儿能登城眺望玩耍,无意中与值守的士兵咫尺共处,那绝不是一种偶然。
秦廷政治已经悬于一线,胡亥依然浑噩着,反正父皇已经说过了,“这皇帝位是要传至二世、三世,以至永远的!”至于那些盗贼,本来有章邯就够了,偏偏还要搭上个王离,岂不多此一举。看李斯那副熊样,愁什么愁!朕正值华年,需要享尽天地间的欢乐,可朝中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太麻烦,文臣武将又絮絮叨叨没完没了,真够烦人!说不听,可总有风声吹进耳朵。幸亏朕心里有老主意,早就不操心那些屁事啦。青春有限,光阴一刻值千金,还总觉得不够用。听说世上有一种“无为”的说法,也许赵卿的主意就是从那里来的,贤明的君主就是要少给臣下找麻烦!
在赵高的耐心诱导下,二世不再上朝。他深陷宫闱,不经召见,大臣们谁也到不了身边,凡事只能对赵高说说。赵高侍奉左右,更是断绝了朝廷上下内外的联系,大小事情从此都由他说了算。
对二世的这种状况,李斯心里着急,不免到处发表些看法。赵高听说李斯颇有微言,便找上门来,换了一付嘴脸,说:“哎呀,听说那个关东盗贼多呀,都闹起来啦!您说这皇上他,总把心思放在盖那个阿房宫上头,这不是,又要追加征发夫役,又要到处搜罗那些狗马之类的没有用的玩意儿,我真想劝劝他,可是不行呐,地位卑贱呐,实在不敢开口!不过从本职上讲,那可是丞相您分内的事情,你却为何不去劝谏呢?”
李斯也怪,竟然信了这一番鬼话,说:“我早就想劝谏,可如今皇上深居宫中久不上朝,我想要说的那些话,靠传达是不行的。想见皇上吧,实在找不到机会。”
赵高说:“是真的吗?那咱俩配合配合,皇上一得空,我立即就给君侯打招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