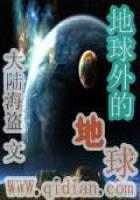刚刚进门的严中举并没有像严情想象中那样扑向满地的黄金,而是一脸严肃的说道:“情儿,你过来,我要告诉你一件事。”
对严情而言,那是记忆中从未见过的父亲。
小心翼翼地打开了被尘封十一年之久的柜子,严中举的脸上百感交集。在严情目瞪口呆的视线中,那三件本不属于这里的东西再次被亮了出来。
“这、这是……”
“就在你出生那天……”严中举没有看儿子惊异的脸,一双小眯眼目不转睛的盯着已经开始泛黄的画有冀墨麟的画像。将他从落榜结识杜识仙到林中巧遇冀墨麟,受其所托去绘世宫送东西之事,直至与前几天来村中避难的画师口中所听来的话,全都毫无保留的说了出来。
“是你爹我没用,胆小怕事。但是现在,画术浩劫已经逼近了!”严中举的语气比灰蒙蒙的天还要死气沉沉,那是实在没有办法下才做出的决定。否则的话,他宁愿严情傻乎乎的过一辈子,也不要他冒着威胁去完成父亲未完成的事。“前些天来的画师说了,他们刚刚在我们村子一千里的地方进行了战斗,结果落败而逃,才到了我们这里避难。那些打败他们的邪画师估计也快到我们这里了。”
“……”
“本来,我可以将冀墨麟之事告诉他们,但是,眼下这动乱之年,人心隔肚皮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好是坏。况且,画师本就是亦正亦邪。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画出那样的画,但是从你开始画圆的时候,我就感觉这是天意!儿子,你一定要将这三件东西送到绘世宫啊!”
“……”
没有一句回答,就好像没有听见这件事一般。严情沉默着望向窗外,虽说中秋节已过,可南方的天还是像个孩子,动不动就哭。只是,这积攒下的乌云,逼的人喘不过气来。一天之内经历这样多的事,严情心里早已乱的不成体统,宋员外的话与父亲的话,让他无从面对。
见他不语,严中举心里也不好受,毕竟儿子才十一岁。“情儿,要是不愿意去,就算了吧。爹知道,这有些为难你了……”
“父亲。”严情突然开口打断他的话,接口道:“不是因为这件事。”说着,严情便将宋员外刚才对他说的话全都说了出来,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或许,面对难题时,父母,永远是最好的答案。
“哼,无事不登三宝殿,我就知道,那姓宋的没安好心,自身都快要难保了,他还准备怎么陷害我们?”严中举不满的冷笑一声,目光转向严情继续道:“你只要记着,如果你不去,说不定天下就真的没救了,而到那时候,我和你娘还有你,恐怕只能在阴曹相会了。”
心莫名的漏跳半拍,因为这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话,严情心里更加难受了。
“爹…”
“情儿,照你说的,爹就更不能走了,否则,那姓宋的来了,你娘一人如何应对?”
“可是…”
“没有‘可是’,你只要快快将这些东西送去,再赶回来,天下浩劫一解,我们以后便可无忧无虑的生活了。”
就这样,在严中举的劝说下,严情被强行送出了严家村。要说这严中举也是,他担心亲自去送东西,绘世宫的画师们因时隔太久,迁怒之下要了自己性命。而让那严情去就不一样了,毕竟是小孩子,那帮画师再丧尽天良也不会怎么为难一个孩子。且说严情莫名其妙作出的画也是让人叹为观止,说不定那绘世宫中的人一高兴,还会收下他。再者说了,宋员外没有得到想要的东西,一定不会善罢甘休,严中举已年过不惑,膝下就此一子,他也不希望严情有什么闪失。
背着比自己背还要宽的画板,严情再一次的回头望向已生活了十一年的村子。心里泛起的不只是害怕,更多的是不舍。
回过头,面前的两条一望无际的小路便成为了他第一件头疼的事。“该选哪一条呢?”严情自言自语着,不禁又想起了临行前和父亲的那段对话。
“父亲,绘世宫在哪里?”
“不知道。”
“哦。”脑中思索一圈后,严情才反应过来“不知道?”
“嗯。”
“那我怎么去啊?”
“鼻子底下一张嘴,问别人啊!”
“……”
要说,这严中举也的确不知道绘世宫的地址,之前冀墨麟也没有告诉他,而那些画师们更是说不清现今绘世宫在哪里,有的说绘世宫被毁了,有的说他们迁址了,总之众说纷纭。无可奈何之下,严中举只能让儿子碰碰运气。
而这一去,是福是祸,谁都不知道。
严情向上托了托画板,三步一回头的离开了严家村,怀着憧憬,带着思念越走越远。他不会想到,这是最后一次见到家乡了。
未走几步,两个身影便出现在了眼前。
“就是他,就是他!”好熟悉的声音,严情抬起头才发现,那声音的主人便是早晨离开的宋员外。只不过此时的宋员外哪里还有早晨的威严,一身的绫罗绸缎被撕破,脸上都是伤疤,甚至两只手臂都不翼而飞了,顺着长袍流出的鲜血已是拖了一路,整个人像丧家之犬一般。
“哦,果然是个孩子。”未等严情吃惊,身旁另一人便开口笑道:“呵呵,是你画的这画吗?”说着,手中一扬,那不知是被宋员外还是谁的鲜血所染红的《银江雪狐图》便出现在了严情面前。
画中原本通体雪白的狐狸,让鲜血一浸,周身散发着妖气,而对严情来说,一股浓郁的杀气,在那人的笑眼中涌出。
“嗯…”严情望向那人时,又是一惊。来者不过二十多岁,一袭白衣,一把折扇,相貌异常英俊。若是在城中,定会让人误认为是哪家的公子哥。但是在这荒郊野外,此人又是身背画板,脸上虽挂着三分笑意,但是一双眼中满是冰冷。让人不敢直视,仅仅看了一眼,严情便害怕的低下头,小声答应着。
而那少年身后的宋员外听见严情的话,也不顾身上的疼痛,小心翼翼的问道:“人也找到了,现在可以放我走了吧?”那声音却像是祈求一般,这和早晨严情所见识过的趾高气昂大不相同,宋员外竟像是十分畏惧那少年。
且说早晨离开严家的宋员外担心夜长梦多,于是带着随从,又准备赶回乡,同那地方官吏商议,若严情不交出狐泪石,便如何将其父母关押,来威逼他就范。
谁知刚出严家村不远,便遇到了那白衣少年。本来,宋员外一行三人快马加鞭将要从那少年身旁路过,哪知白衣少年自从遇到他们一双冷目便没有离开宋员外手中的画卷。在将要擦身而过的一瞬间,那少年伸出手,避过骏马的冲撞,竟从宋员外的手中将那画卷抢了过来。
虽说宋员外的主要目的不是严情画的那幅画,但是毕竟那画画的很精妙,且是从自己手中被抢的,放任不管的话,有失颜面。于是停鞭勒马,怒视那白衣少年,还未质问,那白衣男子便反问自己“画从何来?”
不问不要紧,这一问宋员外更是勃然大怒,喝令随行两名壮汉去教训那少年。
要知道,跟在宋员外身边的人,也不会是等闲之辈,那两名壮汉摩拳擦掌冲向少年,大有将其生撕活剥之意。
而那白衣少年头也不抬,叹气道:“不自量力。”说着,从背上的画板中取出一张纸,随意那么一挥笔,两名刚刚还生龙活虎的壮汉惨叫跌倒。当着宋员外的面被拦腰截为两段,双双暴亡。
“画是哪儿来的?”白衣少年毫不在意,直视着宋员外,那双冷眼像野兽一样。
宋员外还当他也是为了狐泪石而来,便咬紧牙关说,不知道。
冷目一收,宋员外惨叫着跪倒在地,甚至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的他,从此便失去了两只手臂。看着掉到地上还在收缩的自己的双臂,宋员外顿时冷汗淋漓,他明白,眼前之人不达目的,是不会罢休的。
于是便将如何从严家得到这画的过程全都说了出来,只是,毕竟老奸巨猾,那宋员外单单撇下了“狐泪石”之事没有说出来。
听及至此,白衣少年便让宋员外带路去严中举家找那作画的严情,宋员外哪敢不依,只是,刚才所乘骏马已受惊远去,两人只得徒步前行。于是,强忍痛楚,宋员外拖着鲜血又一次前往严家村。
恰逢那严情刚刚出村,一念之差下选了通往宋氏乡的路,便正与两人相遇。
“呵呵,我什么时候说过,找到这孩子就放你走啊?”白衣少年说着,右手一挥,在画纸上留下一道痕迹。那宋员外听闻正欲求饶,嘴巴大张却发不出声音,一低头整个脑袋便掉了下来,鲜血喷了一地。
虽说死的是宋员外,虽说很讨厌他,但毕竟是人命关天。且说严情长这么大,第一次亲眼见到杀人,心里的恐惧可想而知,想喊却喊不出声音,特别是刚刚掉下的脑袋由于神经还未死亡,宋员外的双眼不甘的一张一合。此情此景之下,严情再也忍不住了,脑袋一歪,像他老子严中举一样,昏了过去。
白衣少年扫了眼倒在自己面前一死一活的两个人,也不说话,又随手从自己的画板中抽出一张画纸喝道:“人神出画!”说也奇怪,他话音刚落,八个身高体壮的汉子变戏法一般的从那小小的纸张中钻了出来。
“秋公子。”八个壮汉站成一排,恭敬地齐声叫道。
被他们称为“秋公子”的白衣少年也不多说,指向倒地昏迷的严情冲他们说道:“这个孩子可以用来‘供墨’,把他带走吧。”
在那八人走后,秋公子继续向前走去,目光却没有离开远处的严家村,冷笑道:“又是一个村落,很好,不如让它也消失吧。”
而与之相反的路上,昏迷中的严情眼前又一次出现了自己的故乡——严家村。只是他不知道,为什么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村子,在梦中渐渐模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