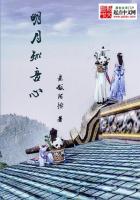刑平二人见这女子出了城后便越走越偏僻,也不知走了多远,眼见天渐亮,这女子脚步也渐放慢下来,伸手又点了两人几处穴道,这两人径直昏睡过去,醒来时已不知过了多久,只是见天色又已转黑,便被这女子拎了赶路,又走了一夜至天见明时,终走至一座山脚下,两人被这女子直往地上一扔,不由“哎呦”一声叫出来,才知道身上穴道竟已解开。
扁儿总算是够机灵,心想自己从未见过此人,估摸着这人还不知道眼下抓的便是刑家独苗少主。他心里知道现在万不可露了身份以免惹来祸事,眼珠一转,便摸着自己屁股,喊声“痛死我了”,又用脚去碰碰刑平的腿,道:“狗四儿,你痛不痛?”
刑平会意,便也抚着屁股,挤出一张苦脸,闷声道:“可痛死我啦,扁三,咱俩昨夜是触了哪门子霉头,什么钱财也没捞着,我叫你出门前拜灶王爷来着,你非不听,看吧,灶王爷不保佑咱有饭吃,便就遇上.....”说到这抬眼看了看这女子,只见她正背对着自己往山上瞧去,那风姿绰约非同常人,本想说她是霉神,一瞧之下竟脱口说成了“就遇上了这位白衣仙子。”
扁儿才听到“扁三”二字,便已忍不住捂了嘴强忍住笑意,心想少爷你真是扯谎不打草稿的人,这通篇的顺溜可真难得,心里偷笑,嘴上却哀号道:“那咱也没拜衰神来着,怎便就这般衰样?”
刑平还未还嘴,那女子突转过身来,一双美目把这二人上上下下仔细打量了一回,嘶哑的声音随之说道:“你们两个是偷儿?”
二人忙点头,那女子冷笑道:“你二人是多大的胆子,敢摸上柯府行馆?难道竟是武艺超群的贼人,行馆上下便无人能察觉你二人在行窃?”
二人不想立时就被这女子戳穿谎言,都脸不由一红,刑平忙道:“仙子真是神仙,这样就看出来了,是咱哥俩错了,不该在仙子跟前扯谎的。”
看那女子目光炯炯直盯着自己,刑平哀求道:“仙子饶命,我俩是牛头山人氏,我叫游乐,小名叫狗四,他是我的邻居,小名便叫扁三,大名叫扁担,因我俩家中实在揭不开锅,前些年便相约卖身到了柯府里讨口饭吃。昨夜因撞见那止溪塘中有异光,以为是甚了不得的宝贝,起了贼心,才偷着摸到那里去的,还求仙子发发慈悲,放我俩一条生路,我等再不去做那下三滥的事了......”边说着边就趴下了大拜几拜,这番谎话直把扁儿也糊弄得一愣一愣的,幸而反应灵敏,忙道是也是也,也趴倒了跟着一起跪拜。
那女子抬脚踢了踢刑平,哼道:“你便是要我绞了你的手筋才肯说实话不成?你身上这件短袄也值不少银子,何以屈就做个下人?”
刑平这才猛地想起,昨夜匆忙出来,本以为去去就回,万没想到会被劫持至荒郊野外,自也没想到要换个行头出门,眼下自己所穿全是名贵布匹所缝制的金丝袄衣袄裤,明眼人一瞧便知这是富贵之物,只怕这谎话再也编不下去了,不由急出一头汗。
反是扁儿这会急中生智,回身扑往刑平,伸手便去扯他衣裤,嘴里气呼呼地道:“好你个狗四,我说前几日刑公子赏我的一身好衣裳怎地便找不着了,原来被你偷穿了在身上,快还回来。”立时二人便扭打在一起。
那女子叱一声“胡闹什么”,一脚扫过,两枚石子飞唆而过,“啪啪”两声,二人分别被击中膝盖,登时跌分开来。
扁儿屁股还未着地,已被这女子揪住了胸前衣襟,吓得他浑身都哆嗦起来,以为刚才那句谎话漏洞百出,气恼了她要立时痛下杀手,却听她扯着那难听的嗓音道:“你说刑公子?是南财刑府家的公子?”
扁儿不由得向刑平望去,见他不住摇头递眼色,便哆嗦着对那女子道:“不,不,是,是......”一时还想不起哪个也姓刑的富家公子,只急得闭紧了双眼大声咳嗽掩饰,却听那女子自言自语道:“是了,这做爹的在,做儿子的怎会不在,我怎没想到,这二十年了,我竟狠得下心没去看过他一眼......”
扁儿听得那女子声音竟渐转悲凄之意,便偷睁一丝眼看,只见她目视远方,似已沉浸在回忆中,揪住自己衣裳的手上的劲道也渐松开来,便忙挣脱她的手,见她亦无察觉,心想这女的突然发起呆来,真是好机会,得快些开溜才是。这般想着边慢慢矮下身来,偷偷f地跟刑平打手势想叫他悄悄往后逃,谁知刑平只苦了脸,用手指指自己的膝盖又指指扁儿的,又是摇头又是摆手就是不起身。
急得扁儿直想跺脚,这一抬右脚才惊觉这整个腿竟像僵住了一般无法迈出半步,整个人一个不稳已经又跌倒在地,心里暗自叫苦,这四周仅只荒山野岭,即便这女子不杀或是她径直离去,等入夜野兽来咬上几口只怕也是没命,还没个全尸,想到那些肢体不全的惨象不禁又打个冷颤。
刑平也是想到了此节,眼中也不由露出一丝恐惧,心想这女子究竟与我家是敌是友尚说不准,不如由着她带走,慢慢套出话来再另寻时机逃走,总也好过在这里死得不明不白。主意已定,便开口求道:“仙子,昨夜失火后你这番把我俩带出来,只怕柯府这一会正清点人数,自然认定便是我俩惹祸潜逃,以后是再也回不去了。仙子这般好身手,我俩愿意追随仙子,赴汤蹈火定在所不辞。”刑平总算是在江湖游荡了好些时日,虽不曾遇上危急,但江湖上的规矩竟也学到了一二,当下便有样学样起来。
那女子一愣,回身望向他,道:“你俩要追随我?凭你二人这般一点根基全无的身手,我带着有什么好处?”
刑平忙道:“仙子这般超尘脱俗,怎能没有下人服侍,那些挑水砍柴洗衣做饭打扫的粗重活,我俩全都会,保管做得又快又好。”
那女子听刑平一口一个仙子,又赞她好,心里也挺受用,道:“我不缺人洗衣做饭,在山野间行走也无需挑水打扫,倒急缺几个劳力干些烦活,你俩若能挨苦,便就跟着。”
刑平和扁儿连忙点头如捣蒜,满口应承,女子便解开二人腿上穴道,头也不回往山上去,只说了句:“跟上来。”
苦了刑平和扁儿,又不会轻功,又不敢落下,一开始还能跟着跑起来,再往后累喘了便互扶着跟上,最后实在走不动了,双手双脚爬上来,脚掌和手指都磨出了许多血泡,总算那女子停住了脚步,说声到了,这两人才齐齐瘫倒在地,只觉得全身都酸软虚脱了。
那女子甩给刑平一只水袋,又指向脚旁一处山径说道:“这里下去可见着一股清泉,以后每日清晨阳光照下之前,你俩须用那泉水浇灌这些血果,若有一日不勤误了浇水,我便把你二人从此处直扔下山去。”
见刑平抱着水袋只顾着点头喘气也说不出话来,那女子冷笑道:“这山巅上有不少白色石头,我劝你二人趁日未落先给自己搭间小石屋栖身,此山夜黑后毒虫猛兽无数,若还想留得性命,入夜即刻进屋躲避。”说完也不再理他二人,一闪而去。
女子走后一会,二人才总算歇过魂来,强爬起来四下张望一番,只见身处的这片山凹树木青葱,花繁枝茂,竟清幽宜人,靠近崖边有一平台,栽种数十株奇异的矮果,形若灯盏,艳红似血,娇脆欲滴,竟是从未见过之物,刑平不由大奇,趴在边上仔细观赏,良久才自语道:“这可吃否?”
扁儿却看到日已过山头,不由急道:“我的爷,你看看这时辰,刚才那人说天一黑这儿就有猛兽,咱们赶紧去找找她说的那些石头,快弄来搭个屋子夜间好藏身。”
刑平经他一提才记起这事,连忙站起来和他一起寻找,只是几日未食,肚中饥火难耐,两人又去寻了几个野果充充饥,略缓些饿意了,又往上走了约一里地才寻着,这山巅的景色又和那山凹大有不同,此处寸草不生,更无树木遮荫,只高高堆起了许许多多白色的石头,足有十来人那般高,乍一看倒像是一个巨大的坟头。
扁儿虽是侍仆,平时也只需服侍刑平一人,单做些端茶倒水,穿衣梳头之类的细活,何时干过搬运重活,更不用说刑平这富贵少爷,加之爬了一天山身子早已发软,只搬出寥寥数块便已累趴下,两人身上衣衫湿得如才过水浆洗一般,手上脚上火辣辣痛,脸朝下摊长了四肢,只有喘的气,连说句话的力气也没有了,就这般倒在石堆隙缝间,谁也不肯再动弹半分。
不一会夕阳余晖缓缓落下,四下凉风吹起,这两人竟不知何时已睡着了。
扁儿正梦着躺在柔软的丝被上支着二郎腿啃着大鸡腿,怎知这鸡腿越啃越冷,不由地使劲巴砸嘴巴,谁知这鸡腿竟自己躲了起来,扁儿一急伸手去追,却碰着个凉嗖嗖滑溜溜的物件,不由得睁了睡眼,迷糊中只看到四周一片黑暗,伸手不见五指,以为天已黑,正在想继续睡去,却突然感到手触着的物件竟然缓缓移动起来,这一惊便直接抬起身来,揉了揉困眼,定睛一看,差点没把魂儿给吓飞了。
只见眼见游走的那一圈乌黑之物,竟是一段水桶般粗的蛇身,这蛇身遍体漆黑,虽无斑纹,却似披了一副尖刀做的甲胄,走过之地,便刮得石块铿铿作响。
扁儿恰好人陷在石堆缝隙中,见这蛇身只绕着身周这些石头,尚未危及他,便尽力往石缝里更缩了缩,心神稍定才猛地记起自家少主,又急忙探出身四下张望,只见这蛇身正绕着这巨大的白石坟头缓缓滑动,竟看不到蛇头蛇身在何处,只是借着朦胧月色,依稀看到脚下不远处的石堆缝里也趴着一人,只是动也不动,也不知道死活,心里又急又怕,忍不住轻声呼道:“少爷,少爷......”见四下无人应,趴着的那人也无动静,扁儿一急之下,脚下用劲一蹬,竟滚了块石头下去,一声闷响砸在一段蛇身上。
扁儿还来不及惊呼不好,便只觉得头上一股巨寒,惊恐之下抬头一看,只见一张血盆大口正从上方直直往自己扑来,心里的恐惧到了极点,人不知是吓傻了还是被这异寒冻傻了,竟一动也不敢动。
眼见扁儿立时便要成了这蛇口的猎物,一声悠扬的笛声从远处传来,这笛声清韵入耳,扁儿一个激灵缓过神来,双脚一软整个便倦缩在石堆缝中,兀自吓得牙齿还直打颤。
那血盆蛇口直扑了个空,只把尖齿在白石上刮磨不已,那声音刺得扁儿的耳朵阵阵发痛,心里便似抓疯了般数度便想要蹦蹿出去,只折磨得他双手楸住了心口上的衣裳,缩在隙缝中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那清悠的笛声又一次传来,似渐远而近,那巨蛇便似听出催促之意,竟抬起了血口,几下摇摆,慢悠悠从这座白石坟头上滑下来,不多时竟溜得无影无踪。
扁儿这下死里逃生,整个人便如虚脱一般,便深吸几口气,这心还是扑扑乱跳个不停,身上的衣裳又湿了个透,额上的汗珠更是滴落到眼上黏着睫毛,这满目的水珠也不知是汗还是泪,待得颤着手抹了一把眼上的汗泪,便瞧见从坟边缓缓走近一个人,手握横笛,素衣飘飘,容颜清丽,这相貌打扮竟是前几夜见着的,与黑衣呆在一起的那位,被自家少爷误以为是柯家小姐的少女。
这一喜也不及细想这少女怎会在此,又怎能以笛子驱赶巨蛇,张口便呼道:“姑娘,姑娘,我在这儿。”又连连招手,道:“我家少爷与黑少侠交好,那晚在集市见过姑娘一面,可还记得?”
来人正是洛影,她本看到石堆下趴着一人不知死活,便走近欲看看动静,却听到另一处传来招呼声,也不由愣住,站定脚步便看到从石堆里颤抖抖地冒出半个人身,这人边和自己挥手边往那趴着的人卧处指去,待听得“黑少侠”三字,才想起是曾见过,便也急步过去,轻巧巧地拖住了这人的手腕,略往上一提,把他从石堆中拉上来,又顺势把他一同拉至了趴地之人的跟前。
扁儿连忙把那趴地之人扳过身来,果然便是自家少爷,只见他额上一处伤口凝着发干的血渍,双目急闭呼吸微弱,似已晕迷多时,这副模样只把扁儿急得眼泪又出来了,忙晃着刑平的手直叫着:“少爷,少爷,你可醒醒......”
洛影伸手探了探刑平的鼻息,又瞧了瞧额上的伤口,搭了搭他的腕脉,对扁儿道:“这是摔晕过去了,你不要着急,你家少爷没什么大碍。”
扁儿听了此言真是千恩万谢,连忙跪在地上便向洛影磕头,直道:“求求姑娘,救救我家少爷。”
洛影忙伸手挡住扁儿往下磕的脑袋,道:“你别再磕了,我救他便是。”说着四下看了眼,道:“你背了他,跟我走。”
扁儿连忙扶起刑平,请洛影帮忙支住了,又双手撑在地上,让洛影把刑平伏在他身上,他自己的双脚虽疲软得直打抖,却还是一咬牙,强生出一股气力,把刑平背了起来,跟着洛影下了这山巅。
洛影引着他直到了一处清泉前才停下脚步,示意扁儿放下刑平。扁儿这一会也真支持不住了,路上几次咬牙撑着直把嘴唇也咬出几回血,唇上破了又结,结了又破的血渍已把嘴唇渍得又黑又干。待把刑平倚放在泉边石上,自己也忍不住趴到泉上,半个身子直接便凑到水里,狠狠喝了几口水,这脑子冰凉了许多才长长松一口气。
洛影从怀中掏出一块素帕,沾了些水帮着刑平细细洗去了额上污血,见他的伤口不很深,便从怀中取出包药粉,抖了些许敷在伤口上。见他亦无半点反应,料想他多半是惊吓过度,一口气没上来才晕过去的,便拔出腰间别着的玉锥,出手如风,几下疾点,帮刑平推血过穴,不多时,刑平才缓过这口气,悠悠转醒。
刑平恍惚中睁得眼来,眼前朦胧一张清秀绝伦的脸,似笑非笑,似嗔非嗔,竟以为是柯家小姐来到跟前,只觉得心头大暖,一伸手便紧拉住了这美人儿的柔嫩双手,口中欣喜道:“你来了,你果真还是要找我来的。”
却见这美人儿脸色大窘,立时抽出了手去转过身走开,刑平还未及呼叫留步,边上已扑过一人来,直晃着他胳膊喜道:“少爷,你可醒了,太好了,太好了。”
刑平被这一番晃,才觉得额头痛得厉害,才想抬手摸去,边上这人又抓住他手,道:“碰不得,一碰又出血。”这才回过神来,定睛一看抓住他手的却是扁儿,不由奇道:“怎么是你?柯家小姐呢?”
扁儿更奇,反问道:“哪儿来的柯家小姐?”见刑平手指着洛影离去的方向,不由笑道:“少爷嘴上说着不要柯家小姐做夫人,可心里梦里都是这小姐,这可如何是好?刚才走掉的那姑娘不是柯家小姐,是上回你见着黑少侠与一位姑娘在一处,便错认了人家是星瑶小姐的那位姑娘。”
刑平大窘,想到刚才竟还抓住了人家姑娘的手,不由脸涨得通红,垂下头来,只觉得额头疼痛更甚,不由哎呦一声,扁儿也顾不上笑他了,赶紧帮着吹吹,安慰他快些休息,这一天又惊又累的,亦实在无力再多聊,耳听清悠的笛声一声声传来,心神甚宁,不多时这二人便伏在石上渐渐沉睡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