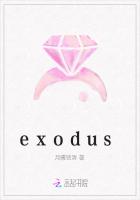这个城市在一夜之间忽然多了许多要饭的,他们衣着破烂,目光惨淡,神情苦楚。面前摆着一张大字报,写满了苦难的人生遭遇。他们亦或早年丧父,贫瘠无根,筹钱为母治病。亦或耳鸣目瞎,无法周转,讨钱要生活。亦或睡在冰冷的报纸上,脸色发青,手脚麻木,颤颤巍巍的等一张张的纸币。亦或四肢残缺,造孽兮兮,激发路人的怜悯之心。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人,成群结队的,分布在车站,商场等人流众多的地方,成为年末里的一道风景。
他们是某种有头目的组织,逢年过节,就如雨后的春笋一样,崭露头角,按部就班的执行任务,分配成果。在这样的组织里,他们必须听从头目的安排,不然就要遭受皮肉乃至饥渴之苦。他们大多数患有智障,生活很难自理。那这些人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是谁呢,怎么会这样?除了这些,剩下的呢,还有吗?是被人带走的去了哪里?有人知道,有人不知道。有人关心,有人冷却。有人还在寻找,还在期待,有人已经放弃,已经除名。找到了很好,找不到的呢?他们在经受着什么呢?看看被刻意裸露的伤痕与残疾,看看专门卖弄的贫瘠,看看故意表现出的残缺。这个里面,什么都有,什么标本都有。有专门的演员,专门的导演,专门的造型师,失明的、嘶哑的、缺胳膊断腿的、装疯卖傻的,演义生活,演义荒诞的现实。在这样纷纷扰扰的怪圈里,一个30岁不相上下的男子不顾往来的车辆,拖着一个男孩,疯疯癫癫的从马路对面冲过来,他头发凌乱,衣着脏臭,在确定没有被人追踪后松开手,然后啪啪啪的打了男孩几个耳光子。
男孩想哭,却哭不出来,从那件已经穿的分不清颜色的口袋里抓出一把钱。5毛的,一块的,零零星星,递给男子。看到钱,男子便没有了怒色,一把逮过纸币,唾了两口唾沫,打湿了手指后,扑哧扑哧的清了起来。已经是1月中旬,空气中还夹杂着冰冷的尘埃,一粒一粒的戳进红肿的脚丫里,手心中,还有那干瘪的耳朵上。男孩很冷,不停的跺脚搓手,还时不时的将手伸进那件破旧的衬衫中,抠着那发炎的伤痕。
20几块,短短一个小时,收获还不错。男子幸然一笑,露出一口的大黑牙,噗噗的亲了几口折好的零钞,塞进裤兜,接着又摸了摸男孩的脑袋,说着什么。不一会儿,男子走开了,并没有走远,只是远远的,看着男孩走向自己指定的商场门口,将一个装鞋的小盒子放在眼前,双脚盘地,还故意扯开胸前的扣子,一大块被烧得变形的肉皮贴在胸前。男孩低着头,看不清脸庞,但时不时的有人放钱进来。不一会儿,盒子就虚涨了起来。男孩左顾右盼,在确定无人注意的情况下,赶紧抱起纸盒,意欲将纸币装进事先备好的口袋里。忽然,一只手抓住了男孩,紧接着出现了一块很漂亮的蛋糕。
男孩的警惕心很强,推开来人,抱起盒子撒腿就跑,不一会儿,就没有了踪影。
看着洒落一地的蛋糕,不知是谁叹了一口气。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命运,这个东西从出生就开始了,伴随至永远。富饶的身价是如此,贫瘠的伤痛亦是如此。当初他的叔叔将他以300块的价钱租给这个男子时,不,一切的悲痛不是从这里开始的,或许,是从那个飞走的气球开始的。总之,他成了一个傻子的孩子,还经常被扔在狗窝里,成了名副其实的狗孩子。那个所谓的叔叔看不下去,给了他一口饭。男孩8岁的时候,村子里忽然兴起了一种职业,而那位男子就是这项事业的发起人,短短半年,他就给家里增加了两间新房子。乞讨从此就成为一种时髦,一种职业,男女老少,摒弃土地,大包小包的进城了,十几个人蜗居在几十个平方的难民窝里,同吃同住,过着另类的农村生活。
这是一间坐落在高楼大厦背后,泛滥着臭水味,充斥着噪音的破房子。租金只要200块,是个响当当的瓦棚。一到雨天,水流成河,到处都漏水。现在是冬天,天空灰蒙蒙的,看不到太阳的影子,房间不大,约莫30几个平方,混乱脏臭,被纸板隔成了10个小空间,每个空间里有一张用砖头和木头搭成的床,窗户上糊了报纸,有的已经劈裂,嗖嗖的舞动着。
门开了,一个小女孩蹑手蹑脚的进来了。她光着脚,提着一个口袋,浑身脏兮兮的,脸蛋上印彻着太阳的颜色,但她目光空洞,黯然无神。站在门口踌躇了一下,好像在等什么,但很快放下手中的袋子,朝一个小隔间走去,不一会儿,脚上多了一双男人的烂皮鞋。可能是饿了吧,她打开那个提回来的口袋,拿出一包似乎是麻辣条的小零食吃了起来……
远处一个森林公园的施工正在有序的进行着,一个头戴安全帽的男子,手持拐杖,同一些施工人员商榷着什么。忽然,有人惊叫了起来。这个男子抬头一看,只见远处那所垃圾站的大火熊熊的舞了起来。
男孩手里的那块蛋糕忽然融化了,他惊恐的撇开一切,朝大火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