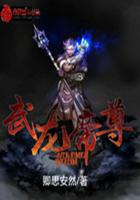“他外出求学去了,今天早上刚走,你找他有什么事?”雀儿仔细打量了少年一眼,越看他越面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是星弟的朋友刘识睿,对吗?今年他生辰那天你还送给他蛇胆做礼物,他很感激呢。”想起张星看到蛇胆时脸上茫然又无地自容的表情,她不经意间笑出了声。
“在下正是刘识睿。由于当时张兄一直咳嗽却不肯看病,所以在下才送他蛇胆做礼,蛇胆有清热解毒、化痰镇痉的功效,生******,易引起中毒,可配酒吞服或蒸食。”一提到药材,刘识睿眯成线的眼睛立刻放出了异彩,恨不得席地而坐,和眼前这个姑娘说上个三天三夜,可转眼想到他此行的目的,又不由自主地愁眉苦脸起来,“既然张良兄不在,那在下就先告辞了,改日再登门拜会。”
雀儿看他似有难言之隐,而且事关重大,非同小可,关心道:“如果你有什么事找他,可以先找告诉我,等他回来了,我一定会转达给他,或者现在写信给他也行。”
刘识睿沉吟着,叹了一口气,“那时恐怕张星他们已经……哎呀!我还是另想办法吧。”坏了!刘识睿暗叫不好,自知失言,立刻住口告辞。
“等等!”雀儿拦住了欲言又止,遽然离开的刘识睿,问道:“你刚刚说张星怎么了?”
刘识睿支支吾吾地掩饰道:“我,我没说他,你听错了。”
雀儿睇了他一眼,冷然道:“知不知道你撒谎的本事糟透了,连张星的万分之一也不如。我奉劝你一句,你最好给我说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不然我这就喊人把你当做在丞相府行窃的小偷送官。”
“别别别……我说我说。”老实的刘识睿禁不住雀儿的威胁,立刻吓得求饶,把全部都给交代了。
雀儿这才知道张星和一群官宦子弟去五音瑶席寻欢作乐遇到了漆雕函和他的跟班,这个漆雕函可不是普通人,他是漆雕旬最宠爱的孙子。在朝中,张平和漆雕旬水火不相容,大人的纷争间接性的影响到了孩子的想法,张星等人看到漆雕函一行人简直就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双方一见面就互相讥讽,各不相让,更是因为同一位舞姬而争吵不休。
胆小如鼠的刘识睿看苗头不对,担心双方因为冲动大打出手,赶紧跑了出来搬救兵。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张良,因为他认为张良不仅仗义豪爽,还是个打架的好手。今天这档子事,刘识睿全靠他了,哪知他竟外出了。
“带我过去找张星。”雀儿撂下一句话,拦住一个下人,把手里的竹牍交给她,托她送到西苑去。
刘识睿瞳孔突然放大,捏着自己的耳朵,怀疑自己听错了。“你说什么?你要去五音瑶席?”
“我说我去帮你们解围。别担心,对付轻狂之徒,我可是很有一套的。别再犹豫了,时间紧迫,我们快走吧。”雀儿催促道。
刘识睿想拦又拦不住她,只好由着她去。走在路上,他忽然想起了什么,问道:“认识半天了,还不知道姑娘芳名呢,姑娘可否告知?”
雀儿温声道:“我是张星的姐姐……”
“姐姐?张星说他没姐姐啊!”刘识睿打断雀儿的话,停下脚步,严肃的看着雀儿,他担心自己被戏弄了,事情紧迫,他可不能在这种时刻被骗。
???雀儿想了想,问道:“他有没有和你说过自己有个妹妹?”
刘识睿不解,两道浓眉快愁成了一条辫子:“是说过一次。”
“那就没错了,我只比张星大一天,他不爱叫我姐姐,总是把我当做妹妹。”
“原来如此,可是张星兄为何不爱叫你姐姐?”刘识睿好像对此事很感兴趣。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还是等你见了他,让他给你解释为妙。”雀儿没心情多言其他,只顾的加快步伐,逐渐把文弱的刘识睿甩在了身后。
五音瑶席是一个让人纵情娱乐的地方,里面有如烟如云的漂亮姑娘,还有精妙绝伦的歌舞和应接不暇的雕梁画栋、奇花异草。这样一处人间仙境对客人的钱袋还没有任何要求,只要你想进,无论你是乞丐还是贵人,五音瑶席都敞着门欢迎。这里的主人曾说过:“人人都有寻欢作乐的权利,毋论高低贵贱,皆可在此畅所欲言,纵情欢笑。”
估计说这话的人从未料到,这句话会让五音瑶席从此客人如织,热闹非凡。
来这儿的有普通百姓,还有达官显贵,由于这些贵人们特意打扮的不显眼,五音瑶席里的下人唯恐一个不留意惹到了谁,所以对每位客人的态度都是恭恭敬敬的。
五音瑶席由四栋楼组成,其中数云霓楼最为有名,这座楼里有金碧辉煌的舞台和奢华的雅座,客人在这里可以欣赏到五音瑶席最优秀的乐舞,享受到最舒适的待遇。能来这座楼里的人,非富即贵,因为要看这座楼里的乐舞少不了花钱。
张星和漆雕函一行人在云霓楼相遇,自从他们发现对方坐在自己对面后,美姬和乐舞就再也入不了他们的眼了,他们的眼中只有难以容忍的彼此。
明眼人一看他们的穿衣打扮和言谈行止就知道他们出身不凡,下人也不敢插手管束他们,纷纷装成聋子哑巴各自忙着手里的事。旁边的客人对这种少年斗狠情况已是司空见惯,也不闻不问,只是自顾自的喝酒行乐,只有几个守卫五音瑶席的壮汉在一旁看着,专门防止他们打起架来伤及无辜。
张星他们都是达官显贵家的子弟,接受着良好的教育,所以即便斗狠,也不过是跪坐在席子上使出唇枪舌剑,冷言冷语,互相贬损奚落,言行举止全然不同于街头混混那般粗鲁泼皮。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就算是在这里也要讲规矩,你们不懂先来后到,胡作非为,如此无法无天,亏你们还是学孔孟之道的,某人的高堂不是被称为贤者吗?难道贤者就是这样教自己儿子的的?”一个细竹竿般的瘦高少年蔑视着对面的张星,嗤笑道。
张星和同伴跪坐在舞台下的另一边,缄口不言,好像没听到竹竿少年含沙影射的话,不屑于搭理他,冷傲的眼神不知落在何处。
竹竿少年认为张星是词穷了,得意地吸吸鼻子,脸上的雀斑一抖一抖的。
这时,张星身边一个长得虎头虎脑的少年开口了:“规矩都是人立的,在这里,五音瑶席的舞姬就是立规矩的人,既然她们愿意跳我们想看的舞,你们就算比我们早来一年也不能强行改变人家的意愿,莫说贤者,就算是王公国戚不也得入乡随俗,听从于主人?”
别看这个少年长得比刘识睿还要朴实憨厚,可说起话来头头是道,不卑不亢,把对方对张星的讽刺原封不动的返了回去,堵得竹竿少年无话可说。
被同伴围绕着的漆雕函一直在冷眼观察着张星的一举一动,其他的他一概不感兴趣,就连别人对他这个王公国戚的讽刺也抛给了同伴,只听他身边一个紫衣少年笑道:“说到底,这里不过是个花钱买乐子的地方,又不是贵庄,大家都是来消遣的,分什么主客?娱乐尽兴才是要紧事,我们这边想看气势强健的《干戈之舞》,你们那边想看旖旎温和的《白驹》,两支舞都是难得的好舞,又是同一伙人表演,分什么先后?既然舞姬说要先跳《白驹》,咱们又能说什么?”
这一席话引起了一阵骚动,对面的人怀疑他心里叵测,自己人觉得他临阵倒戈。只有张星和漆雕函无动于衷。
紫衣少年貌似对现状很满意,琥珀色的眼睛里的笑意更加清晰,直勾勾地盯着张星道:“《干戈》节奏壮烈威武,恐怕舞姬表演后会无力再舞,倒不如先跳一支婉转的《白驹》活动下筋骨。我们也好久没看过这样美丽婀娜的舞了,这次正好借了你们的光了。”
话音一落,紫衣少年的同伴们纷纷笑了起来,拍着紫衣少年的肩膀,夸他说得好,有的人干脆就说对面那些人阴里阴气。就连漆雕函都笑出了声。
这次张星他们受到了对方恶毒的侮辱,个个都是怒不可遏的模样。
张星的脸色冷到了极点,浑身上下散发着寒意,他望着对面,凌厉的目光扫过漆雕函他们每个人,最后落在紫衣少年身上:“陈凹,听你刚才对这两支舞的见解,貌似你对乐舞颇有研究。”
“略知皮毛而已,在张星兄面前献丑了。”紫衣少年在张星的注视下,显得很不自在,但他话里行间还是十分客气谦逊的。
张星冷哼一声:“算你还有自知之明。”
接着他又问道:“你知不知道《白驹》的深意为何?《干戈》的深意又为何?”
???问话的张星咄咄逼人,回话的陈凹却一脸恭顺,小小年纪就能沉稳自持至此,实在难得,“据我所知,《白驹》出自《诗三百》,原为留客惜别之诗,是为知己离去,挽留不得而发出的无奈,哀怨情深。而《干戈》则是根据护国将军漆雕旬大人在战场上的英勇事迹改编而成,舞出了韩国将士的一腔热血。”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白驹》岂止只有惜别之意,它还有王者欲留贤士不得的悲叹之音,这一点,从‘尔公尔侯,逸豫无期’一句中就可看出来,这世上除了君王,还有谁能给朋友以封公封侯的承诺?如此贤舞竟被你说成女色阴舞,也不怕贻笑大方。我之前说你有自知之明还真是抬举你了。”张星将《白驹》的寓意重新解释了一遍,最后还不忘给陈凹一记鄙夷的眼神。
陈凹白净的脸上唰的一下红了,眼睛里燃起了怒火,可他又不敢对张星造次,只好向漆雕函求助。
张星扭过头,用余光睨着对面的漆雕函,冷不丁冒出来的一句:“怪不得人说物以类聚。”
“张星,你算什么东西?也配对我的人指手画脚。”一直作壁上观的漆雕函再也坐不住了。
“陈凹对儒家经典有所误解,我不辞辛苦地纠正他,怎么就成了指手画脚?”
“不过是首诗而已,也就你们这些儒生拿它当宝贝,我们兵家的人根本不屑于此,用不着你来纠正。”
在韩国,兵儒两家不睦已久,儒家觉得兵者粗鲁无礼,好战残忍;兵家认为儒生腐朽多事,懦弱无能,双方互相嫌弃,犹如水火不相容。其中尤以崇尚儒学的丞相张平和出身兵家的大将军漆雕旬斗得最为激烈。这种斗争自然而然的延伸到了下一代的身上。
“明明不懂,还要妄言多舌,我好心纠正讲解,他们还说我多事,对于这般的南郭先生,我还能再说什么?”张星看向同伴,摇着头,扼腕叹息。
一个机灵的同伴讥笑道:“子不是已经替你说了吗?‘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
话音一落,张星等人皆哈哈大笑起来。
“你放肆!”漆雕函拍案怒道,四周不明现状的人好奇的看着他们,气氛一下紧张起来,眼看着“战争”一触即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