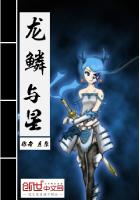那老丐一只吃完,意犹未尽,又在土中踅摸,又掏到一只。片刻过后,山鼠下肚,老丐自背后掏出个葫芦,咕噜咕噜喝了两口,伸了个懒腰,打两个哈欠,倒头睡了,不一刻便鼾声大作。
苦儿见他睡得熟了,轻轻站起身来,走到那鼠洞之旁,也学着老丐的样子在土中乱摸,果然摸到一只,可惜略小。他学了老丐的样子斩头去尾,剥皮掏肠,不过两三口便已吃光。他肚子饿得厉害,沿着鼠洞继续挖,又挖到一窝小山鼠。那小山鼠刚刚出生,身子粉红,连毛也未长出,早已烤得熟了。不过两三口又已吃光。他还不死心,继续挖掘,山鼠再也没有了,却挖到山鼠储存过冬粮食的鼠仓,掏出一堆栗子、榛子之类坚果。好在鼠穴中很是干燥,干果也未受潮。他将这些干果投入火堆,待烧熟了又用树枝拨出吃了,这才饱了。
他见火焰渐熄,又去旁边树林中拣拾木柴投入火堆,又扯了一堆干草垫身,这才沉沉睡去。
他一会梦到柳先生教自己读书识字,一会又梦到柳先生教自己甩石子,忽然柳先生脸上面巾落下,露出一个蛇头,狠狠向他咬来。他转身欲逃,却被那蛇缠住不放,只觉那蛇身冰冷刺骨,一条蛇舌向他脸上舔来,只觉又滑又腻。他一声大叫,醒了过来,却见火堆早已熄灭,那老丐也不见了踪影。
此时天光大亮,他四周打量,只见身在群山峻岭之中,却不知身在何处,一时间,仿佛空旷天地间再无他人。
他这些天一路游逛过来,自己虽不知道,其实在内心深处却有一个念头,那便是要远离严家庄,就算死也要死得远远的。如今在山中迷失了方向,也不知道该往何处去,只是信步行止。
他这一天便在山中游荡,正午时分,他绕过一座山岗,面前出现一座高山,山势挺拔,屹立于苍茫世界之间,于白云苍狗间岿然不动,有傲视天地之势。他本已精疲力竭,见了这座大山,突发豪气,心中便想:“便是要死,也得死在这座山上才爽快!”
他举目四望,寻找上山路径,却见白雪皑皑,山势陡峭,竟是连小径也无一条。他发了狠,便踏雪攀石,向上攀去。
到了傍晚,总算攀到山腰上平坦处,却再无力气。此时夕阳西下,天边万道红霞,将整座大山照得分外妖娆。苦儿长出了一口气,在山间松林中寻些松子充饥。此时天色已暗,朔风渐紧,他转过一块巨石,见石后有一间小小石屋,想来是进山的猎人修来临时居住之用。
那石屋很是简陋,一扇柴门半开半闭。门前积雪盈尺,并无脚印,想是无人居住。
他推门入内,石屋内倒很干净,石头垒就的炉灶上尚有一口缺口铁锅,炉灶连着一盘小炕,墙上钉着两张兽皮,墙角堆着些木柴。
眼看天色已暗,寒风自门缝中吹进,遍体生寒。苦儿在墙缝中摸索了一会,果然找到火石火绒等物。他匆忙生了火,又将墙上兽皮揭了,一张挡在柴门上,另一张用来做被子。
房间里渐渐温暖。他虽一天未吃东西,却不觉饥饿,只是自怜身世,忍不住流泪。半夜时分,忽然柴门一响,一人钻进石屋来,“咦”的一声,却又是那老丐。
那老丐见了苦儿,摇头叹了口气,甩手扔过一件东西来。那东西毛羽鲜亮,长翎短翅,却是一羽山鸡。苦儿起身接了,触手之处,那山鸡身子尚温暖,脖子却断了。
苦儿猜想这石屋必是老丐的居所。他既闯进别人屋中,心中略感歉意,也不待老丐开口,便到门外抱了一大块雪,放在破锅中化了,又在锅台上寻了把生锈的钝刀,到了门外,将山鸡开肠破肚,剔肠去肚。再进石屋时,锅中雪块已然融化。
他伸手在炉膛中掏出灰渣,倾了锅中雪水搅拌,将山鸡全身裹了,便架在灶上烘烤。
他自幼便在山野中放牛牧羊,常于山间捉得小鸟小兽。山间既无炉灶,又无油盐,便是这般调制,因此如今做来,俱是轻车熟路。
炉中火光熊熊,苦儿偷偷去看那老丐,此时离得近了,便看得清楚些,原来他年纪并不多老,只不过四十几岁模样,只是须发俱已花白,生得细眉长眼,五官很是精致。苦儿心中叹一口气,只觉造物弄人,殊无情理可言。他本是个快乐少年,很少忧伤,但近来遭逢大变,一时间觉得在世上为人,实在没什么趣味。
眼见火候已到,他在墙边捡了两块碎石,将包裹山鸡之泥沙敲开,顿时肉香四溢。那山鸡连皮带毛俱随泥沙掉落,只露出白嫩香甜的肌肉来。苦儿将山鸡用破锅盛了,放在老丐面前。
老丐馋涎欲滴,自怀中掏出数个小包,却是盐末、胡椒、辣椒等物;又掏出葫芦,这才伸手撕了鸡腿,在辣椒上乱蘸,塞入口中大嚼。
那老丐两只鸡腿吃下,已辣得面红耳赤,大呼过瘾,便抱着葫芦狂饮,又吃了一只鸡翅,酒却没了。老丐大呼扫兴,跳起身来,开门去了。
苦儿等了半晌,却不见老丐回转,想他定是另有去处。他这一日攀山登岭,早已饿了,当下风卷残云,饱餐了一顿。
他打定主意,待明日一早便再出发,定要登上山顶。他心中盘算,上下眼皮不断打架,终于睡着了。
次日一早,他醒来后,却见身旁放着一套棉衣。他拿起一看,棉衣质地做工均好,虽是旧衣,好在洗的干净。他身上衣服已有十余天未换,这一路来爬冰卧雪,早已破烂不堪,当下换了衣裳,出门寻路。
他举目四望,计算攀援路径,却不由大是灰心。原来这山峰甚高,峰顶积雪终年不化,早已凝为坚冰,远远望去,便与普通山峰无异,到了近前,才看出不同。此时旭日初升,眼前山峰便如一根巨大冰柱闪闪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