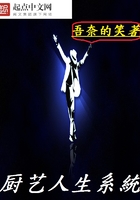那个时候贪玩,学习很差,什么都不会。
陈小茗每每会教我,把她的笔记借给我。我问她问题,她都会很详细的给我解答。比如数学,再譬如物理,我的启蒙老师都是她。我习惯叫她小师父,抗议无效后,她只能默许。
每每秦谨看到她教我的时候,都会停顿一下,然后哼一声,撇过头继续做她的事。
日子过得就像我们学的抛物线,到了后来斜率越来越大,过得也就越来越快。
唯一值得回忆的,也就是元旦了。
彼时的元旦是喧嚣的,住校的同学们很早就去了教室,准备着即将来临的元旦晚会。
是的,白天开晚会,他们把班里布置的很漂亮,桌子都被排到了两边,在屋顶挂上气球和彩带,搬好电视和CD。以致于我们跑校的来的时候,一切都准备好了。
我坐公车来的时候大概七点钟,太阳刚刚升到一半,正是清新的好天气。
走进颓圮的东方红小学,路过车棚的时候,一眼就看见了不远处的陈小茗。她背对着我,一个人默默地慢慢地走着。
我喊了一声,她应着,回过头来已是满脸的喜悦,蹦蹦跳跳的跑到我眼前,仰着头,望着我。
这才注意到她一身粉红色的小礼服,长长的裙摆一直拖到脚踝。
下面再配上干净的白色的帆布鞋。光鲜动人,煞是可爱。
“哎,干什么呢,还不快走!”她说着便拉着我朝教室奔去。
“你今天穿的好漂亮呢。”我突然说。
她听到这话蓦的停下了脚步,然后回过头,给了我一个大大的笑容,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
然后我们便一起往教室走去,她边走边问:“吃了么?”
“嗯,早上在家吃的。”
~
教室里面很吵,跟炸开了锅似的,特殊的日子特殊的季节,总是容易让人们倍加兴奋,况于十几岁的稚气未脱的孩子,他们吵着,闹着,跟一群神经病一样。老班还没来,晚会还没开始。坐到座位的时候,我身后那群“熟人”们早就聚一起聊天了。
大家今天穿的都挺漂亮的,我记得有一句话叫,孩子在外面就是父母的脸面,父母再苦,也不会苦自己的孩子。他们能给你买新衣服,绝对不会舍不得给你买。
我向后看去,梁姗,小茗,林小婉,阿荣。五个,又数了一遍。
终于发现哪里不对了,秦谨呢?
我问珊姐,珊姐说,逛商场去了。
我无奈的皱了下眉头,还真是她啊,向来对这种聚会不感兴趣。偶尔兴致来了,翘课也是家常便饭。鬼知道她现在在哪,说不定正抱着酒酿小元宵吧唧吧唧的吸呢。
没多久我就被两个平时玩的要好的小玩伴赵洋和周扒皮拉去讨论龙珠和数码宝贝了。
耳朵里却清晰的听着后面一群美女的聊天声音。
小茗一进教室的时候就引起了无数的惊叹,林小婉打趣道:“哟,小茗,今天穿酱漂亮啊,不就当个主持人吗,看把你美的。”
珊姐也乘机帮腔学秦谨的口气说“瞧你穿的那副德行,一辈子也就那样啦~”
然后她们女生都笑了。茗儿也笑了,但就是不反驳,对于别人,她永远是那副温柔的样子,只是单单偶尔对我会外向霸道那么一点。
我这才想起今天的主持人是陈小茗,突然就对两个好基友的喋喋不休厌烦了起来,心里有点兴奋还有点期待晚会的快点到来。
对于老班的姗姗来迟,大家也不在意了,毕竟今天是喜庆的日子,大家开开心心最好了。老班一来,元旦晚会就正式开始了。
首先,老班走过来对小茗说了什么,她点点头,接着便走上台,宣布晚会正式开始。台下的,起哄声一片。那群饥渴的叼丝,手持着可以喷出彩条的东西,朝着我的茗儿一气乱喷,春天啊,躁动的雄性。其他女生们都被冷落了,如果小秦在,她也会被喷吧。
可怜的陈小茗刚刚还是春日里的一朵花,现在就成一雪人了。
看着她狼狈的整理头发的样子,我不住有种奇怪的快感。好像这事我也参与了一样。心里却虚伪的想:这群叼丝,一点都不懂得怜香惜玉。
待她整理好发丝,party就继续了。
她那粉红色的蝴蝶结发卡特别的显眼,貌似整个舞台都是她的一个人的,大家的焦点都在她身上。
接下来是文艺表演,当时演了什么不记得了,只记得当时有两个妹子搞了个组合,跳了个神马美少女组合的舞。然后,老班就笑嘻嘻的给我们介绍他的儿子,嗯,说他儿子在学小提琴,让他儿子来给我们表演一个。
进场时,那小子比他老头还道貌岸然样似北大校长,闭着眼颌抵着琴,头部随着音符甩动,俨然拉出一首宛如天籁的《一闪一闪亮晶晶》。一曲拉完,场上是寂静的让人害怕的沉默。不知是谁看到了老班脸上阴晴不定的神色带头鼓了掌,于是台下掌声一片。
老班这才不好意思的跟我们解释:“他才刚开始学。”
之后的节目就不具有什么观赏性了,而且我也不记得了,不记得那就是不好看。
最后,重头戏来了,发吃的了,一人两颗巧克力,两颗糖,一个橘子。
对于吃的东西一向是我不变的最爱。当然会记得特别清楚,-),东西刚发下来我就在一分钟之内把它们解决了,这个·时候party也快结束了。
大家都跑去照相了,老班在帮拍。我索性站了起来,正想过去。猛地一袭可爱的身影飘来。想着这是谁呢?陈小茗就又出现在我面前了。
奇怪,为什么要用又呢。
她那份可爱真的可以折杀人,在我面前的她剥了一颗大白兔奶糖放进嘴里嚼的开心,那个样子,意志不坚定地早被她勾去魂像痴汉一样流口水了。她的模样整个人活脱脱就像一颗大白兔奶糖,让人想一口吃了她,见我垂涎的看着她,便问我:“怎么?你的糖呢?”
我拍拍肚皮丧心病狂的说:“这儿呢!”
她睁大眼睛跟看怪兽似的说:“天,本来还准备骗你几颗呢。”
然后她无奈的摇了摇头,从胸口的口袋里把她所有的“工资”都掏给了我,说:“给,还是我请你吧。”
我毫不客气的一把抢过,以迅雷不及掩耳风卷残云之势搞定了她的那一份,她愣了好久,拍了拍我的后背说:“别噎着了啊。”我心里顿时涌上一种温暖,母性的温暖。
然后,她拎起她的裙子,转了一圈问:“好看么?”顿时我便被乱花渐欲迷人眼了,迷糊的答了个:“嗯。”
那时的我应该想到以她如假包换的班花,甚至校花的身份,送糖的男生肯定多的比二狗子身上的虱子还多,怎么会图我那几个糖呢?
她绰约的身姿被她的小礼服呈现的淋漓尽致,嗯,茗儿开后百花煞,后来我如是评价。
老班拍完了照,就宣布晚会结束了,大家可以回去了。时间还早,我正想要卷铺盖走人,我那让人憔悴的姑娘又来了。她今天怎么尽找我呢?不会是看上我了吧?
她拉了拉我的胳膊说:“吴错,陪我到后面走走好吗?”
呃,这种要求一般很难拒绝的,再加上她那天魅力值太bug,就答应了她。她开心的要死,倾城的笑容一直挂在她脸上。
我记得很久以后我坐火车回家,看着窗外似水般薄凉的夜色,迎面奔跑过来的电线杆,还有,一条碧绿幽蓝广袤无垠的河流。
从西向东,一眼望过去,水天接在一起,一样的颜色分不清哪里是河水,哪里是天空。
我的目光停驻在视线尽头的河水远方。
远方的远方,一个叫下龙爪的地方。
传说下龙爪的下面有龙宫,古代小城的野史、县志上曾有过记载,而现已无法考证这种说法的真实性。
撇开这些牛鬼蛇神不说,每年淹死在这里的冤魂怨鬼的事情倒是总有听说。
我和陈小茗走在学校后面的公路上,下面便是护城的淠河。不远处,便是第一次和她认识一起回家时路过的那座桥,我们现在处的位置,便叫做下龙爪zhao。
往下看去,是一大块光滑的有些耀眼的花岗岩,接着河水,幽幽的,泛着死气,不知道这底下有多深。传说这里深不见底,底下的龙宫通着东海。溺水在这里的人,尸首有些就打捞不到了。
所以,我是不敢在这里多停留半分的,便拉着她往前赶。
前方快到桥的地方,河水就很浅了。淠河的其他地方还是很正常的,唯一不正常的就是下龙爪,下龙爪是河里的一个深潭,天生就在那里,入之必死。
所以,避过了那里,其他的地方,都是可以快乐的玩耍的。
我跟着她过了马路,来到下面的河滩,河滩的地方满是沙粒,构成了一个浅浅的沙滩,沙子被阳光晒过,暖暖的,干干的,看起来踩上去应该会很舒服。
我们站在沙滩上,风吹过脸庞,撩起她的发丝,她用手挡在额头上,向前方看了看,然后惊喜的用手指了指远方。
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看到一群半大的孩子,嗯,小学生吧,在打水漂。
“嗖”的一声便有一个石子旋转着呼啸的跳跃到远方,湮没在安静的河流中。
呵,打的还很精彩,可是这种东西,像我们这样已经脱离了小学生的人应该不会再感兴趣了吧?虽然我很爱玩。
只是这样想着,手却被人向前拉去。
对的,我被一个妹子拉着向湍急地河流跑去。
“走吧,陪我去看看,我没见过。”她说。
在河边的浅滩上我们脱了鞋,便准备从这处狭窄的水深只到脚踝的地方趟过去。
她一只手拎着一只帆布鞋便要过去,“等我,我拉你过。”才脱了一只鞋的我连忙一把拉住她的手。
她愣了一下,接着便低下头,从手红到脖子再到脸。我又连忙放开了她的手,继续脱我的鞋。
就这样,不久之后,一个男生一只手拿着两只鞋,一只手拉着一个美丽动人活泼可爱的一只手拿一只帆布鞋的脸红扑扑的女生在浅浅的河水中行走。
她一边低头看着脚下湍急的河水小心的走着,一边哼着一首欢快的歌。
是一首很好听的儿歌。
走的时候没有工夫去问,等淌过了河流,到了河的对岸,我们在沙滩上穿鞋的时候我才问她。
她笑了笑,看着我说,你不记得了呀?
幼儿园的时候没有学过么?
我摇了摇头。
她露出了无奈的表情,然后就是一副拿我没办法的样子。
就这样看了我有两秒多钟,然后突然很认真的对我说:“这首歌,叫洋娃娃和小熊跳舞。”
“哦。”我实在没从想起,幼儿园的时期毕竟对我来说太遥远,能记得的也就是那年刚出了旺旺仙贝,嚷嚷着要姥姥给我买,不买就不上幼儿园的事。
见我没有什么反应,她也没管我,自顾自地把鞋穿好,也没有再哼歌了。我默默的系着我的鞋带。想着一会儿怎么秀一下我打水漂的技术,然后抬头看着不远处那群小学生们还在那儿不知疲倦的玩耍,心里满是不屑和鄙视。
接着,系了最后一个结,手还停留在鞋带上没有拿来。
猝不及防的,肩膀一沉,还没来得及扭去看,扑面而来的又是一阵让人神魂颠倒的迷离的香气。
然后听到她的呼吸声仿佛就贴在我耳边。
还有那似乎能感觉的到,又似乎感觉不到的心跳声。
我僵在那里,无法动弹,感觉浑身发热,从脚红到了脖子。
心脏嗅觉和触觉的刺激下,跳动的异常厉害,似乎想要跳出我的肉体。
她就这么静静的靠在了我的肩膀,在我正要站起来的时候。
那时我没敢看她,大约感觉到她的视线是看着正前方的。于是我也顺着感觉的目光看过去,那是夕阳下被染红的小城。
渐渐变得拥挤的道路满是车流,三三两两已经打开了车灯,远方的钟楼孤独而又倔强的伫立着,而在那楼下同样伫立着几棵一样孤独而又倔强的不知名的树。
在我们的前方是交错纵横的老街和古巷,被夕阳染过,透露出无比的沧桑和厚重的感觉。
平日里上学放学,忙碌着,心里不安定的时候从来没有发现,这每天走无数次的街道会如此之美。
无论是人还是物,这一刻,仿佛都和傍晚这一个词完美的融合到了一起。
她就这么靠着我,久久没有离开,我不知道她在看什么,视线停留在哪。
可能是和我一样在看傍晚的风景,或许也有可能在看别的。
我所知道的是,那一刻,我能体会到她的茫然和无助。
当两个人靠的越近,就会愈加能体会到对方的心境。
当然具体是为什么而迷茫无助,我无从去想去猜。
换做现在,我依然是束手无策。
我能做的,仅仅是为她提供一个肩膀。
让她暂时的停靠一下。
就这样维持了有五分钟左右吧,具体时间也记不清楚了,我感觉肩膀一轻。然后扭头去看,她脸红红的,又坐回了原来的姿势。
我尴尬的把目光移向了别处,虽然没有再看她,却感觉她一直在看我,两道如炬的目光让我有点无处是从。坐立不安,于是便站了起来,干咳了一声,说:“走,我们去前面看看那所打水漂的孩们。”
她不答话只是微笑的站了起来,拍拍身后的沙土,然后把手伸在了我面前。
我看着她伸过来的手,犹豫了一会儿,就在再也不管的一把拉着她往前走,可能力道有点大,差点把她拉倒。我又怕她摔倒的凑过去扶她。
结果她自己稳住了,顿时让我脸红到了脖子梗。
好吧,我再也不敢看她,安心的慢慢的拉着她往那群孩子的地方走去。
那是一群半大的孩子,还在上小学的样子,现在刚好放学了,一个个背着双肩的书包,上面印着米老鼠之类的特别大特别夸张的卡通人物。在河岸边的沙砾堆里挑捡着又扁又平的石块,然后依次斜着身子往水里射。比比看谁射的更多,不,是更远。
其中不乏有打的很好的,能打到河中央还要开外的地方。不过大多数的孩子都是往水里乱丢,没有丝毫的技巧可言。
我看着那群打水漂的小屁孩们,不觉技痒,但是想了想,出于那种骚包的装X心理,还是嗤之以鼻的说:“嘁,真幼稚。”
是嘛,在茗儿面前,我想,我已经有点学会收敛自己的本性了,就算没学会,装也会装了。
然而却不想,回头正看见她在石滩上仔细的挑选着石片。
她找的很认真,右手一片一片的筛选着石块,然后在放到左手,把中意的轻轻的攥在手心。
我看着她重复着这个动作,一直到她捡完,站起来,走到我面前,然后朝我伸出了左手,慢慢的张开,然后微笑的跟我说:“我们也去玩吧。”
我突然觉得我的装B有些多余了,在我恍惚的罅隙间,她已经绕过我,去到前面的浅滩开始扔了。
举目望去,她扔的并不怎么好,也就被划分在中等的水平,能打到四个或五个水漂。
偶尔打出五个水漂的时候,她的脸上就会浮现出欣喜的神色。很浅很浅,不那么张扬却又让人能够感受到她内心的喜悦,很坦诚。
见她玩的那么开心,天**玩的我立马捡了几块石片站到了她旁边一起打了起来。
只不过小时候经家在农村,经常玩,所以技术自然高出她一大截。五个算失误,一般都在六七个。
她在一边看了,微微笑着对我说:“很厉害呀!”
我不屑的回了句:“那当然!”
之后我便义务的开始教她,从甩腕的手法到倾斜的姿势,选石片却不用我教。可能是她物理学的好,大概懂一点,找的都是重量刚好有两边偏薄的,简直不能再赞。
所以到最后变成了她去找石片,我来扔。
我心里很得意,终于有一样我可以教茗儿了。
现在想起来不免有点太幼稚,最后变成我一个玩,她默默给我挑石头,回想起来,当时她的额头貌似已经渗出了一层细汗。却依然陪着我玩。打的好的时候会夸我好厉害,打失误了她也会看着,默不作声。
而我却只顾着玩而已,从没有在意过她。
华灯初上,大桥上开始声色犬马的时候。我们才离开了沙滩,在大岩石休息了一会儿才爬上公路,站在桥的一端。
仿佛回到第一次一起回家的那一晚,我下意识的去看她的头发,她的头发虽然有一两根凌乱的贴在耳边,整体上还是整齐的扎在了身后,梳成了一个青春靓丽的马尾。
昏黄的路灯照在她的脸上好像镀上一层虔诚的金色光芒。
她的目光突然对上了我的目光,我一惊,想要移开却突然没能成功尴尬的看着她那两双清澈的眸子。
越看越美丽,内心突然有了一种想要亲过去的冲动,就这么慢慢的靠近,再靠近。快到二十公分的时候,我突然想触了电似的,一把跳开了。
然后两脸通红,又偷偷的看她,发现她低着头,两鬓微红。俨然和我一个模样。
之后便没有什么要紧的事了,看时间已然不早了,我便拉着她像那天晚上一样,走过大桥,横跨着半个小城回了家。
中间一直拉着她的手,她喜欢出手汗,等到送到她家门口的时候,她的手和我的手就像刚洗过一样。
送她回了家,我也就回了家。
后来无数次回忆起这天的场景,总觉得,如果当时我亲了下去,那么之后的事情。
会不会变得不一样?
可是,当时如果拥有什么,又会怎样呢。
谁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