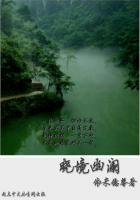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突然骑坐在刘建仁的身上,抡圆了臂膀一个大耳刮子抽在他的脸上,接着怒喝一声,“够了!你还要任性到什么时候!”
“非要杀人灭口才到头吗?”我手指刘建仁,“他是个贱人、渣男,他玩弄别人的感情,他该死,该挨雷劈!但是你呢?难道你就有资格去伤害别人吗?爱上这么个贱人、渣男,不也是你自己的选择吗?既然是自己的选择,那么无论结果是甜蜜还是痛苦,不是都应该自己承担吗?相爱的时候,浓情蜜意,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当爱情已经逝去之后,就不敢正视,不愿意去面对那撕心裂肺的疼,这样的你……也太狡猾了吧!冤也冤了这么多年,恨也恨了这么多年,难道你就这点觉悟吗!”
我逼视着刘建仁的双眼,那双血红色的眼睛,那双已经不属于人类的眼睛,无视他那微微颤抖的身体,继续厉声道:“相爱是两个人的事,不爱了也是两个人的事。他已经不爱了你,你难道还爱着这个趴在地上,像阴沟里的老鼠一样的男人吗?既然已经不再爱了,就不要再纠缠彼此了!我已经看够了!看够了你们女人失去爱情以后,一边抱着过去顾影自怜,一边无妄得祈求爱情能够重来!我还以为……我还以为你会稍微更优秀一点呢?!”
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刘诗诗这么多年还没放下这份执念。被爱人所伤,在身边人的嘲笑中被遗弃,在每一个无眠的夜晚反复煎熬,冰冷的池水无法洗净伤痛,岁月倏忽也带不走悲伤的回忆,她被天地遗忘,只能无助地在束缚之地日复一日地等待,等不到解脱,等到的只有被全世界遗忘。
其实她只是寂寞太久了。
那些不愉快的回忆突然涌上心头,紧紧揪住了我的心,久违的这种心痛的感觉啊。我狠狠地甩了甩头,赶走那痛苦的回忆,沙哑的继续说道,但那话语仿佛已经不是说给刘诗诗听,而是说给另一个女人听了:“坚强一点吧!虽然会很痛苦……但是只要坚强一些,一定能熬过去的,一定会有好事在前面等着我们的。”
话音刚落,刘建仁的双手突然松开了,双腿也停止了挥动。一个模糊的身影离开了刘建仁的身体,默默退到了一边,她那飘散的黑发垂落下来,耷拉在额前掩住了血红的眼睛。周身弥漫的黑气渐渐消散,那暴戾气息也荡然无存。那袭惨白惨白的连衣裙,就如同梦中所见,透着伶仃寂寞,教人怜惜。她也不过只是一个过于倔强的女孩而已。
耳边传来啜泣的声音,循声望去,却是刘建仁不知为何竟哭了起来。他躺在那儿,闭起双眼,任由眼泪汩汩地淌下。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他的用颤抖着手抓紧了胸口的衣襟,这样反复道歉着。
同样一个人,无赖的时候让人恨之入骨,软弱地哭泣时竟让人为之酸楚。也许他,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只有平时看到的那一面,还有另一面由于伪装得太久连我们自己都记不起了吧。
张老师被沙发挡住了视线,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瞧见一直看着我去的方向的胖子突然一愕,还以为我遭遇了什么危险,嘶哑着大叫:“胖子,咋啦?你快抬我起来!快呀!”
胖子这才回过神来,再次尝试去搬抬沙发,不想这沙发竟然可以稍稍被抬动了。沙发毕竟是重,一个人只能抬动一点点,但已经足够让张老师奋力把下身抽出来。他二话不说,就蹦了起来,定睛一看,见我身上也没哪里缺了块料,顿时松了口气。
他强忍着腿部的疼痛,一瘸一拐地到门口取过来那把黑色长伞,撑开伞遮住刘诗诗全身。刘诗诗的身形在黑伞下渐渐变得模糊起来,直至消失不见前一刻,我看见她那被风拂散的刘海下再次露出那双温柔清澈的眼睛,那无声翕动的嘴唇,仿佛说着感谢的话语。
我还愣着神,回味刚才那一幕,张老师便收起了长伞,拍了拍我的肩膀,笑着说:“想不到你小子,啧,真有你的。差一点,这事就没办法收拾了。”
我刚回过神来,胖子就急急地从后把我架起来往门外走,抛下一句,“张老师,我俩伤重,得赶紧包扎,剩下的你看着办。我们先撤!”
这酒吧算是玩完了,沙发、桌椅七零八落,玻璃渣子满地都是,还一动不动的躺着几个不知死活的人。面对这么一个烂摊子,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了。
逃也似的离了酒吧,我俩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互相搀扶沿着河边走廊走了一段,走不动了才倚着河堤护栏歇会。我俩互相甚是稀奇地打量着对方,不由得哈哈大笑。我俩都破了相,鼻青眼肿,头发凌乱,没个人形。胖子本来就胖乎乎的脸,现在更添了几个包子,额头一个、眼角一个、腮帮子一个,而且都在一边,整张脸显得极不对称,让人发笑。当然看起来我也好不到哪里去。这一笑,算是吐出了胸中块垒,把今晚上所有憋屈、担心、惊恐都一扫而光。
“我这辈子都不敢得罪女人了。一想起刘建仁的样子就疼啊。女人,太他喵可怕了!”胖子回想酒吧内发生的一切,尤有余惊。
我笑了笑,啐道:“就你这副尊容,不怕你把人家得罪了,就怕你把人家吓死了。”
“哎,小灵,多亏了你,不然指不定我们今晚全部都要搭进去。你这嘴炮行啊,这么凶的东西,你两句话就镇住了,都比得上涡旋鸣人之奥义,嘴遁之术了。”胖子对我最后那几句话很感兴趣的说。
我不愿多提此事,怕再次勾起那些不愉快的往事。只是笑骂他一句,摊开手掌耸了耸肩,不置可否。
“话又说回来,张老师也真有两下子,虽然差点扑了街,但那两下子把式对那东西还真管用。”
我点了点头表示肯定:“这家伙平时不显山不露水,但绝对懂点门道。这些天邪性的事儿接二连三,要不是每次都是他及时出现,恐怕我和黎老师早就成了刘诗诗的替死鬼了。”
“也不知道张老师现在怎样,他应该有办法脱身吧!”胖子望着酒吧方向出了会神。刚才和张老师共厉生死,一起在鬼门关走了一遭,胖子显然是对张老师萌生了革命同志的情谊了,竟然担心起他来了。
过了会,见我没回应,掉过头来一看,人呢?!四周寻视了一番,才看见我已经半截身子坐进了出租车里面。胖子飞奔上车,使劲把门甩上。
“你不是担心他,赶紧回去陪着他呀!”
“有毛病,老子现在只想躺床上一觉不醒!”
虽然满身上下没有一处地方不痛,但这一觉却是过去一个星期里面最酣畅淋漓的。那天晚上,张老师没回来宿舍,我们俩也没有半夜三更被警察闯进来捉局子里去。第二天早上,嘹亮的《运动员进行曲》照常扰人清梦,而今天扰人清梦的却不单单是广播声,还有满宿舍此起彼伏的惊呼声。
“开来看,快来看,这被揍得整个杜海涛似的是谁呀?”
“哎呀,这张脸去演猪八戒都不用化妆,直接上,绝对像。”
“八戒八戒,不,小灵小灵,你醒醒,没事吧你?”
“这死小子,昨晚我们晚自习回来就看见他在那儿蒙头大睡,当时没去掀他被子,没想到一晚上弄成这幅德行。”
“哎,这小子越来越不像话了,前几天撸管撸到脸青腿软的,现在逃课斗殴,鼻青眼肿的回来。”
“青春期的小屁孩都有这么一个阶段,以为通过打架、逃课、吸烟才能成为大人。小灵怕是进入叛逆期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