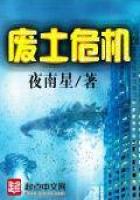她这辈子还没有干过这样的事,捧着许承宗的脑袋,端详了好久,这第一下该从哪儿推呢?想想他一直仰卧着,后脑壳的地方该是最容易起痱子的了,搬着他的脑袋,将推子抵着他的脖子上肌肤,慢慢向上推。
乌黑的头发刷刷地落在塑料上,长及颈项的头发,片刻功夫,后脑壳处就光秃秃的了。剃完了后面,叶望舒自己觉得熟练多了,许承宗因为不能动,一切听她摆布,脑袋前面比后面更容易剃,她的推子在他脑门正中央走了一趟,头发落下来,倒好像在脑门上开了一个青底的壕沟,她看了一眼,第二下就没推下去,此刻旁边没人,她尽情地笑个够,前仰后合,肚子都疼了——小时候看日本电视剧,里面的日本武士好像都梳着这个头型,这个许承宗看起来雄赳赳气昂昂的,比那些日本武士还有气势,可梳了这样的头型,就要笑死人了。
她笑够了,才把他脑袋上剩下的头发剃光。光亮的青头皮趁着他满脸的大胡子,看起来实在不清爽,她早就打定了主意,此刻一不做二不休,他这胡子也没必要留着了。望舒拿点水把他胡子打湿,抹上肥皂沫,左手按着他的脸,右手拎着剃刀,沿着他的鬓下,刷刷刷地一点茬子都没留,左脸刮完了刮右脸,连他鼻子底下的都一根没留,剃了个干干净净!
把塑料上的头发收拾干净,手里拿着块布,用水沾湿了,慢慢地擦拭他脸上剩下的肥皂沫子。一点一点地,她眼睛看着他,不知不觉地手里的布停在他的嘴唇下,眼睛盯着他的紧闭的双目,半天动不了。
这人竟然有这么好的相貌!
没有胡子的遮掩,他薄薄的嘴唇棱角分明,唇角微微翘着,让人禁不住觉得这人是个爱笑的家伙;浓密的眉毛下,鼻骨很高,眼窝很深,一张脸极有气势,只可惜一双眼睛紧闭着,让人不自禁想象他若睁开眼睛,会是什么样子。
她愣了好久,才醒悟过来,自己一个大姑娘盯着人家男人的相貌发呆,太不像话。她下地把手里的布在水中仔细地搓洗了一遍,再帮他细细地将脑袋和脖子擦洗干净,如此反复,换了好多盆水,才勉强让自己满意,端着水盆出去了。
这通忙活,她又出了一身的汗,两个孩子醒了之后,也热得难受,闹着要去湖里洗澡。她拗不过,进屋看许承宗,脑袋和双鬓都光溜溜的他,仍闭着眼睛,没有醒过来。
她关上屋门,再关上院子大门,带着两个孩子去后山的湖里。中间催促了几次,这两个孩子就是不肯上来,她毫无办法,一直玩了将近两个小时,小宝和小燕才算玩够了,慢腾腾地跑上岸来,换了衣服,光着脚丫子跟着姑姑回家。
叶望舒想着屋子里的病人,万一这时候醒过来,看着旁边陌生的环境,一个人影都没有,那他可怎么办?想到这里,加快脚步,打开院子大门,再开了屋门,进去检视许承宗,还好,看来这两个小时他不曾动,看来没有醒。
晚饭后,带着两个孩子看了一会儿电视,到了八点半左右,小宝小燕就都困了,躺在炕上很快就睡着。望舒下楼,从井里拎些水,把房子内外拖拭擦抹一遍,放好水桶和抹布,锁好前后门,到原来母亲的卧室,现在变成自己的屋子里,拉上窗帘,脱光了衣服,悄无声息地洗澡。
月光从窗帘外透进来,洒在她身上,抹了白粉一般。她端详着自己粗糙的手,**五指,举在自己眼前,月光就形成了一个手的剪影。把手放在胸口处,被太阳烤黑了的手背肌肤,跟胸口雪白的颜色形成鲜明的对比。她叹口气,把手攥成一个拳头,泡在水里,头靠着炕沿,轻轻地闭上了眼睛。
她这么放松着,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听见走廊对面屋子有人轻轻“啊”了一声,望舒猛地睁开眼睛,知道那个许承宗醒了。
她抓过毛巾擦干身上,套上衣裤,走到对面屋子里。淡淡的月光里,原本在炕上一直紧闭着的眼睛这时候睁开了,正在四处打量,听见门响,许承宗望过来,看见叶望舒,问她:“这是哪儿?”
他的声音倒是本地口音,有些低沉,因为昏了两天的关系,声音也很轻。望舒站在炕梢处,隔了一间房子的距离,被他审度的目光看得浑身不舒服——她就没有向前走,站在当地道:“这是我家。”
许承宗皱着眉头,仔细打量叶望舒:“我不认识你吧?”
望舒点点头:“你是我大哥带回来的。我大哥名字叫叶望权,你俩以前在一个监狱服刑。”她说完,看着许承宗,心里暗暗想大哥在家的时候,自己怎么一着急之下,忘了问这个许承宗犯了什么法呢?
她打量着他健壮高大的身材,他审度人时眼神间一闪而过的凌厉,觉得抢劫犯、杀人犯都挺适合他——哦,天哪,他不会——不会是**犯吧?!
想到这,她立马向门口缩了缩,心里又怪起大哥来——好端端地出了狱,偏要带这样的朋友回家!万一这个人真是**犯,自己带着两个孩子,家里连个可以依仗的人都没有,可怎么办呢?
手摸着门把手,凉凉的感觉让她定心不少——大哥虽然糊涂,可断断不至于把个**犯带回家让自己照顾。唉,其实不管是什么犯,带这样的朋友回家,也只有自己那个糊涂大哥能做得出来。
炕上的许承宗听了叶望权的名字,迷糊道:“叶望权?不记得这个名字。”
叶望舒瞪大了眼睛,他不记得大哥的名字?他是不是被砸得失忆了?
“你是不是什么都不记得了?”她试探着问,如果那样就遭了,他会不会就这么赖掉欠大哥的四百块钱呢?
许承宗摇摇头,这么一摇头,他似乎感觉到自己头皮擦在枕头上,他眼神里满是诧异,抬起手摸了一下头发,吃了一大惊,沿着头皮向下摸到自己脸上,留了几个月的长发和连鬓胡子一根毛茬都没剩,不知道被谁刮了个干干净净!
“谁给我剃了头发?”许承宗恼怒地问,一边问,一边感到自己周身疼痛,尤其是脑袋上和胯骨上,火烧火燎地,头昏目眩,胯骨上似乎有一块肉被人剜掉了似的。
“哦,是我剃的。天太热了……”
叶望舒还没有说完,被许承宗脸上的表情吓得闭上嘴,他那双眼睛,在昏暗的室内看起来有些凶狠。他直愣愣地看着叶望舒,气恼着问:“你没有我同意,怎么能随便剃我的头发呢?还——还给我剃了个光头!”
这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呢?
叶望舒没指望他就剃头这件事跟自己道谢,可也不用这么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啊!她不想再跟这个不知道是杀人犯还是**犯的什么犯说话了,转身出门,边走边道:“不然剃什么头?我又不是专业理发师。”
“喂,你别走。”许承宗在后面唤她。叶望舒脚步不停,本打算回自己屋子,听见身后的许承宗似乎因为动作太猛,大声地啊了一声。她转身回头,那许承宗正疼得长大了嘴吸气,手按着他的大腿根处,似乎疼得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