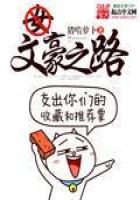一九九〇年七月六日
我故意用手拍了豆屁股一下,她大叫,带着哭腔大叫“打、打、打”。她在怨我打她。我说:“不是打,是拍一下。”“不是,打一下,是打一下。”她十分不满地更正我的话。我又不轻不重地掐了她屁股一下,说“捏一下”。“不是,不是捏一下,是掐一下。”她大声地更正说,面带怒气地望着我。我强忍住笑,不看她。
一九九〇年七月十五日晚
现在,我和豆躺在床上,林在一边看电视。豆儿向我爬来,向我嘴里塞东西。我知道不是好东西,闭上了嘴。她把那东西放在了我唇上,笑着说“大鼻涕”“嘿嘿”。她把鼻嘎嘎(东北话,鼻屎)往我嘴里塞,然后开怀大笑。她耍我。
一九九〇年七月二十七日晚
孩子,我们搬家了,从二楼搬到了一楼。
学院为了便于管理,把一楼西部的几间厢房简单归弄了一下,让住在二楼的几户都搬到一楼去,并宣布谁先搬,谁先挑房。一楼潮湿,门又对外开,不安全。几个住户聚在一起订了攻守同盟,信誓旦旦地表示不搬。
两天以后,姓孙的男教员来找林惋卉,说自己顶不住了,校领导对他说,”你是党员,要带头搬,如果不搬,党纪处分。“他弃阵了,挑了间最好的房子。
林氏知道阵地守不住了,她怕被同盟耻笑,想等两天再说。想不到第二天上午,余下的几家纷纷倒戈,排队到总务科挑房去了。诚实守信的林惋卉被几个战友遗弃在战场上了,抵抗已经毫无意义了,房子也只剩下最差的紧挨厕所的一间了。为了挽回点颜面,只好提点条件。地潮湿,孩子小怕生病。总务科的人表示理解,派人把那间房装上了地板。
一九九〇年八月十九日林惋卉记
老黄去SD出差了,我和豆在家里。她在床上,我在地上洗她的衣服。突然她问我:“妈,你管我奶叫啥?”我顺口回答:“叫妈。”“那你妈呢?”我明白她的意思,故意问一句“谁?”“我姥”,她说。我答“也叫妈”。“你怎么两个妈呀?我就一个。”我禁不住笑了,“因为你小,我大,等你长大了,也有两妈。”我这儿真逗,现在正熟睡在我身旁,头已远离枕头了。
一九九〇年九月一日晚
林氏去了沈阳,要在那学习一个月。又是我和豆在家,刚才来了两个小姑娘(邻居),同她玩了一会,就走了,豆不想让她们走。我告诉豆儿,她妈妈叫她们,不回去不行。豆马上问“她妈没上沈阳呀”?我只好答“没去”。“她妈没去,我妈去了哟,让她妈上沈阳,我妈不上沈阳。”
一九九〇年九月七日晚
豆躺在我身边(我这些笔记多数是趴在床上写的,我不能离她太远)低声哭泣,自言自语道:“想妈妈,你干吗不要孩子?我要上沈阳,我要上沈阳。”她大声叫了两声“我要上沈阳”。看样子是真想妈了。
“爸爸呀!我要写找妈妈(她见我在写字)。”
“我看你这铅笔。”她拿过我正写字的钢笔。
“你不会写字,还给我。”我对她说。
“我妈怎么还不回来呢?”她又问。
“明天,明天差不多能回来。”我答。
“再回来不让她走了。”
“好,我把你这话记上,说得挺好。”
她闭上眼睛要睡,我忽然想起她没尿尿,就叫她起来“尿床怎么办”?
她闭着眼睛说:“我妈洗。”
一九九〇年九月十八日
电视又在唱《亚洲雄风》,烦死人了,开始听的时候还可以。半年来,电视、电台经常放这歌,唱臭了,词曲也不好,像是要和谁打仗,不详和,典型的冷战思维。
亚运会要开了,赶紧开完算了,电视台也不放别的节目了。
“黄豆,走啊,去市场买点菜。”我领着黄豆去了市场。回来时,她走不动了,我看到了,假装看不见,暗自观察她。她对我说:“爸爸,我不认识家,你抱我吧!”我抱了她一会,手臂支撑不住(一只手提菜),放她下来。她走了一会,就叫“肚子痛”,又装作很疼难忍的样子蹲在地上,不肯走了,我只好又抱起她,告诉她:“别跟我耍赖,走不动就说。”
小丫头知道使诈了,哈哈!
一九九〇年九月三十日晚
因为白天在奶奶家,我的老弟总喜欢撩她,一不留神就撩过了火。她就哭着说:“我爸打你。”然后哭着向我求援。我不能打弟弟,像她希望的那样,又怕她失望,从此不再信任我,就装作打弟弟几下,安慰她。
“啊!黄豆,怎么又吃我们家饭?”老弟故作惊讶地大声问。
豆坐在饭桌前,头也不抬,愤恨地回答说,“嗯!就吃你们家饭,把你们家饭吃了(liao第三声)。”
还有一天,豆穿了件网状的上衣。老弟见了,凑近黄豆,用手拽着那衣服表情庄严地问,“黄豆,你妈怎么给你穿这么破的衣服?全是窟窿眼!”我看到豆儿有些不安,她低头很认真地看着衣服,又抬头看看我,等我回答,我假装没看到,转过了头,暗自观察她,她又低头看看衣服,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呵呵!孩子,你要学会判断。
好像是前五天,林氏告诉我,邻人来借钱,林借了。豆看到了,有些疑惑地问林:“我爸不打呀?”林问:“打谁?”豆用手指林。林问:“为什么打我?”“你给楠楠她爸钱了。”豆说。林大惊,忙跟她解释钱是借给他的,过几天人家就会还的。当天晚上,我回家时,豆已睡了。林很惊奇地同我讲了这事。第二天早晨,豆小声对我说:“爸爸打她(指林)。”我问:“为什么打她?”“她给楠楠她爸钱了。”豆平静地说。我告诉她“不是给是借,人家会还的,邻居间借钱是小事”。她好像没听懂。
这孩子来到这世上二十九个月了,她爱母亲,更爱钱,爱没有压倒理性。这家里有个卧底。
一九九〇年十月十一日晚
“我这头型怎么样?”我问黄豆。
“是怎么样(很好的意思,她不会说很好,让她犯点错,听着好笑)。”
“我这头型好,还是你妈头型好?”我问。
“你头型好,我头型比你好。”她答。
“我跟谁最好?”林氏问她。
“跟我。”豆答。
“跟谁第二好?”又问。
“他。”她用手指着我。
“跟谁第三好?”又问。
“不知道。”她说完,就来抓我的笔,说:“我写林。”
“你长大了这个本给你,你要不要?”我问她。
“要。”她答。
“要这干吗?”我又问。
“拿着上美国留学。”豆答。
她还不知道美国是怎么回事,只知道那是个好地方。有人对我说美国比中国先进一百来年。把孩子送到美国,就等于送到了一百年后的中国。为此,无论费多少力,花多少钱,都是值得的。
“写黄,给我写黄豆的‘黄’。”她这样命令我。她爬过来,我拽过她的小脚。这小脚真中看,脚趾呈坡状排开。
我忽然想到要把这小脚印留下,就拿过一瓶墨水,往她脚底涂。她以为在同她玩,也没在意,突然看到我把她脚掌涂满了黑色,哭了,看着我不满地喊:“你干吗把我的脚弄黑了?”
我忍住笑,翻开她影集的扉页,把她的脚按了上去。告诉她“我为你留下了生命的足迹”。
林氏看到了,连忙端过来半盆清水,给豆儿洗脚。笑着对豆儿说:“没事,一洗就干净了,别怪你爸爸,你长大了,会感激他的。”
明年我还会给她印一下,就像每年都要给她拍一卷照片一样。
一九九一年一月十九日晚
林氏去广州看服刑的弟弟去了,已经去十三天了。今晚我从母亲家带豆儿回家,她坐在我自行车的后架上。我一边骑车一边对她说:“豆儿,我这几天有点想你妈了。”她没说话。
我问:“你想不想?”还是没有声音。
我提高声音问:“我跟你说话,你没听着噢?”
“听着了。”她平静地答。
“听着你怎么不吱声?”我问。
“我点头了。”她还是平静地答。
“你点头我能看到吗?”我问。
“你回头呗!”“你下车看呗!”她一直很平静。
一九九一年二月二十日晚
林从广州回来了,豆又同我疏远了,整天缠着她妈。我心中很不是味,隐隐有一点怪她,怨她见了娘不要爹。她鼻子凸出来了,头发也逐渐黑了。
一九九一年五月六日晚
林氏又出差了,我和豆儿在床上看电视,新闻正播放中东的事。豆爬过来缠我,我告诉她,“别闹,美国和伊拉克打起来了。”她停了一会问我:“爸爸,伊拉克怎么和美国打起来了?”国际上的事谁能说明白?不回答她还不行,我耐心告诉她说:“伊拉克抢科威特的钱,科威特打不过伊拉克,就求美国帮忙。”
“科威特没有劲哟?”她疑惑地问。
我知道她在想两个人打仗,有劲的人能打过没劲的人。我没有办法解释清楚,就不耐烦地说“嗯,科威特没劲”。她想了想又问“给没给伊拉克眼睛打出血”?我“哈哈”大笑,点头说:“出血了。”她爷爷就爱坐在电视机前看拳击比赛,她一定是看到过把对手眼睛打出血的场面。
她有点困了,我没话找话,问她:“你困了,我怎么不困呢?”“你能坚持住,我不能坚持住。”她答。
林氏不在家,她成了我最好的伴,如果没有她,我的生活将会是什么?
“床前小儿女,人间第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