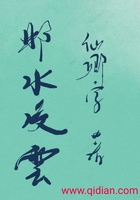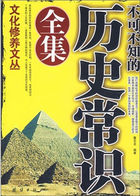第一节
溯溪姨姨
先回到殿中的是安言。在沈醉回来前,她便已经将她听到的回禀了楚帝。
“薛姑娘一切都按陛下的吩咐行事。”安言最后如此说道。
楚帝点点头,挥手示意安言退下。
安言犹疑了一下,还是开口问道:“陛下当真要对薛姑娘兑现承诺?”
楚帝似乎只是睫毛动了动,便置若罔闻。安言会意,未敢再多言,只得颔首退下。
沈醉回到席间的时候,见到兰寂林有些失神,上前试探,发觉兰寂林竟是喝多了酒。心中感慨文人毕竟是酸腐,且这体质想必在京城是不擅酬酢的,却也能稳坐至礼部侍郎,到底有几分能耐。恰借此契机,上前向楚帝告罪,言道兰寂林不胜酒力,恐其御前失仪,请求先行退席。楚帝关怀了几句后便应允了,待沈醉携兰寂林退出殿门后,安言上前询问是否还要跟踪,楚帝先是摇了摇头,忽然像是想起什么似的,眼中一道精芒闪过,沉声对安言道:“你去跟着他,说不定能查到溯溪的下落。”
沈醉送兰寂林回到客栈房间后正欲离去,兰寂林却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
“怎么?”沈醉一惊。
兰寂林的脸色有些泛红,但眼神却很是坚定清明,直视着沈醉,压低声音道:“我总不踏实,似乎有什么危机就在附近,你此行需格外谨慎。”
沈醉怔了怔,聚功凝神仔细听了一番,却未感到异常的声响。再看向兰寂林的时候,只见他已昏昏入睡,只道他是说了胡话,给他盖好被子后便离开了。
子时将近,沈醉依约来到那张纸上所写明的地址处。此处乃一街角暗巷布庄后门,偏僻之极,不见灯火。沈醉徘徊了一阵子,心中盘算着似乎子时将过,却仍不见有任何人来与他会面,正在疑惑莫非是自己会错了“子”字之意,忽听不远处的屋顶上有一阵窸窣的瓦碎之声,心头一紧,紧跟着便听到有人跌落地面的声音以及一声痛苦的闷哼。沈醉循声悄至,却惊见安言倒在暗巷的血泊之中。沈醉虽不知安言功力深浅,但只知晓楚帝肯把自身的安危全盘交给这一女子,便可窥见一斑。沈醉忙匿迹于墙角阴影下迅速观察四周,竟未见任何异动,心中大骇。忽而感觉一阵劲风自上而下袭来,沈醉惊慌间只来及抬手以奉天之壁相挡,却感到无孔不入的寒气扑面入骨而来,使人如坠冰窟,竟挡无可挡,再下一个瞬间,就已什么都不知道了。
沈醉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正伏在一个案子上,试着起身,发觉并无束缚且未曾受伤。环顾四周,似乎是一间民宅的厢房内间。沈醉推开门,只见外间的藤椅上正坐着一个女子,看上去似乎已是徐娘半老,却身着一身夜行之衣,头上亦戴着重重黑纱,让人看不清其真实样貌。
“见过溯溪姨姨。”沈醉大致已猜到此人身份,故上前行礼道。
“小子眼力不错。可有薛姑娘的信物?”溯溪的声音似有些喑哑,与窈窕的身姿全不相符,给人以突兀的感觉。
沈醉忙将怀中玉坠取出,递到溯溪手中。
溯溪将玉坠放在手中摩擦了一会,点了点头,递还给沈醉,道:“不错,确是薛府的信物。只是小子你究竟是什么人,为何竟能使出奉天之壁?你又是如何取得薛姑娘的信任?”
沈醉重新将玉坠揣进怀里,坦白道:“我叫沈醉,是越国礼部侍郎,今次是来楚都和谈的。奉天之壁是我师父所授,但正如姨姨所见,我只修到第三层,是故未能接住姨姨的寒劲掌。至于珑儿姑娘为何如此信任我,我就不得而知了。不瞒姨姨,我确有一番异志,所以才斗胆前来请姨姨助力。”
溯溪沉默了一会,忽然起身面向沈醉行了个礼,道:“你既有此信物,薛府暗人皆会听你调遣。”
第二节
奉天之壁
沈醉忙扶起溯溪道:“姨姨客气了。以后诸事就劳烦姨姨关照了。”
溯溪也未再客气。忽道:“奉天之壁你为何只修了三层?”
沈醉苦笑道:“后面的练功法门我早已烂熟于心,只是不知为何,我依照第四层的法诀运功,可力道较之第三层却尤有不及。师父也未能看出其中症结所在,只当我有越人血脉,无法练楚国秘功罢。”
溯溪摇头道:“姜国分崩离析前,楚人越人本无差别。你定是在哪里练出了差错。”
沈醉不置可否,只得叹气苦笑。
溯溪似乎认真思考了一会,道:“寒劲掌亦是将体内阴寒之功力打出体外,你若找不到继续修习奉天之壁的法门,不如试着修习寒劲掌的内功心诀,或许可以助你打破局限。”
沈醉喜道:“姨姨肯教我?”
溯溪淡淡道:“暗人们虽任你调遣,但我仍要留在渭城保护薛姑娘。我教你一些自保之术,也可省我烦忧。只是这寒劲掌寒气凶险,你切记要依我所授的法门运功,否则危患无穷。”
“是。”沈醉忙点头应允。
片刻后二人席地而坐,溯溪指出数个穴道,教沈醉循序将内功于穴道内交互运行,此法可使得内力脱离经脉避开周天而在体外运行,果然与奉天之壁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沈醉愈发觉得,这寒劲掌的功力阴寒异常,稍有差池即有寒功侵体伤及脏腑的危险。好在此功法大成后是在体外运行,否则以人的体质恐怕难以承受其巨大的寒气。
待溯溪将寒劲掌的功法及心诀尽数讲给沈醉之后,天已蒙蒙发亮。
“你先回去罢。这心诀你若记得清晰可依法修习,但若有半分含糊便不可再练。此法凶险异常,你需慎重。”
沈醉点头,复道:“若我有事,要如何与姨姨及其他暗人取得联系?莫非要回渭城来吗?”
溯溪想了想,从屋角的箱子里取出几只奇小的烟火棒,递给沈醉道:“我会教一两个人跟着你,若你有事,点燃烟火棒即可。”
沈醉双手接过,仔细收好,郑重行礼道:“多谢姨姨。若姨姨与薛姑娘有什么事是我可出力的,也请务必告知于我。”
溯溪点了点头,便打开屋舍的门送沈醉出去。
忽然,沈醉停下脚步问道:“那锦衣卫指挥使怎么样了?”
“她被锦衣卫救走了,应是无性命之忧。”溯溪顿了顿,又道,“我不知她身怀六甲,她腹中胎儿应是难保了。”
沈醉撇了撇嘴,未再说什么,施了个礼便离开了。但仍未敢走大路,在巷子里转了几个圈,才转回客栈去。
溯溪愣了好一会,才缓缓关上门。她轻轻叹了口气,然后抬起手挽起垂在脸前的黑纱。只见重重黑纱之下,溯溪清秀白皙的脸颊和脖颈上,竟有几条深红色微微凸起的疤痕,狰狞而可怖。
和谈金由于数额巨大,楚国将遣军方部队押送至越京,会晚一步出发。沈兰二人的队伍可轻装先行返回复命。天既大亮,沈醉与兰寂林便开始打点行装,安排马车,准备回越。安言再未露面,奉命前来送别的是另外的两名锦衣卫,这二人亦未提及昨夜发生的事。一切按部就班进行,很快,沈兰二人便已登上回越的马车。此时二人尚在楚都,并不太过担心安全的问题,于是分乘两辆马车,正如来时那样,开启了漫漫的归程。
第三节
踏上归途
又行半月有余,初冬已至。队伍行至楚越边界的最后一个城镇。此地名曰岩城,其繁华程度可与渭城相较,有楚国南都之称。出使的队伍在此地休憩整顿,兰寂林又遣人去购置了一些御寒的衣物。
沈醉安顿好人员车马后,看似百无聊赖地在街市中闲逛。沈醉确是第一次在岩城漫步,周遭的繁华与喧嚣很像大越的京城,给人纸醉金迷的感觉,心中的理想抱负似乎不经意间就会在这样的浮华中消磨殆尽。沈醉叹了口气,恰看到街角坐着一个年约十五六岁的小乞丐,心中思虑一番,挑了挑眉,走了过去。
那小乞丐独自一人,正坐在街角懒洋洋地晒太阳,忽然只见一只清秀得像是大姑娘一样的手伸了过来,并且握着一个银锭子。小乞丐眼中放光,忙伸手去接,可那只手却又收了回去。小乞丐抬起头,正对上沈醉幽冷的眸子,竟吓得蓦地缩到一边去了。
沈醉不想竟吓到这个小乞丐,笑了笑,道:“小兄弟可是丐帮的人?”
那小乞丐紧张兮兮地打量了沈醉一番,故作镇静道:“我是丐帮岩城分舵的!八袋舵主是我阿爹!你是什么人?”
沈醉颠了颠手中的银锭子,只见那小乞丐再次被那银锭子吸引,不由自主地凑了过来。沈醉笑道:“你们丐帮向来消息最是灵通,我问你几件事,你若是如实告诉我,这钱就是你的了。”
小乞丐立时警惕之心大减,脸上浮现出骄傲的神情,道:“你若是来问消息的,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整个岩城分舵,除却舵主,便数我知晓得最多了!”
沈醉笑问:“你可知道,南越的霖泠公主是否婚嫁?”
那小乞丐一本正经道:“并没有!此事说来蹊跷,本来都给人家公主找好新的驸马了,不知越国皇帝怎么突然就不高兴了,竟再也不提赐婚的事,就像把公主给忘了似的。诶,这苦命的公主,上个驸马还没拜堂就死了,现在也没嫁出去。果然不是皇帝生的公主就是不一样呀!”小乞丐说着,一瞥沈醉,却见沈醉的目光愈发冰冷,忙住口不语。
沈醉的心里也不知怎的,竟生出一种不可名状的情绪,只觉得气血翻涌,心中惊诧,以为是练寒劲掌有所不妥,调息压了一下,感觉稍有平复,继而再问:“南越朝堂近来可有什么大事发生?”
小乞丐转了转眼珠,神秘道:“若说大事,有一件事可说再大也没有了!可我说了,你需立刻将那银锭子给我!”待沈醉点头应允后,小乞丐顾盼了一下,凑到沈醉近前悄声道,“南越要废太子了!说是查到太子贪渎太过,民怨沸腾!现在洵王风头正盛,大概很快就是南越东宫的新主了!这件事在南越知道的人都不多,可值这个价啦!”
沈醉愣了愣神,叹了口气后将银锭子交给小乞丐。小乞丐笑嘻嘻接过后,又道:“你可真大方!那我不如再告诉你一件事吧!”
“什么事?”
小乞丐指了指沈醉身后道:“那个俊俏的姑娘看了你许多时了,八成是看上你了!”
沈醉一惊,此处正是喧闹的街市,身后脚步声车马声络绎不绝,竟没察觉到有人停驻下来看着自己。沈醉在这一瞬间脑中想到了很多人,包括锦衣卫,相府暗人,甚至绿豆糕都有想到,但他一回头,看到的竟是冷嫣的那张毫无表情的脸。
沈醉有点吃惊,走过去看着冷嫣询问道:“你怎么在这里?”
冷嫣也看着沈醉,眼中似乎红彤彤的,嘴角动了动,却没有说话。
沈醉见冷嫣脸色似乎红润了不少,复问道:“你可还好吗?”
冷嫣的表情似乎有些不知所措,继而眼中的悲伤仿佛如决堤的河水一般崩塌而出,凄然道:“我……我没有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