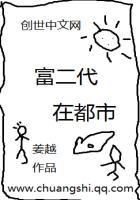只看见花见青拉走了风祁墨,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话,眼神却是看向我的。风祁墨被拉远了,却也是一副笑意盈盈的模样,和对待丁杏又是截然不同了,甚至不是对待阮盈袖时的温文尔雅,只让人觉得他二人之间十分亲密。他也看了我两眼,笑着说了几句话,声音放得很低,花见青狡黠一笑,说了两句话,风祁墨便皱了眉头,仿佛并不赞同。
然而花见青噘了嘴,十分不乐的样子,风祁墨也不再说话,只是摇了摇头,又同花见青说了些什么,就慢慢向我这边走过来。
他过来时已经又笑起来,问我说:“你怎么一直盯着我?”
我这才一窘,想起来刚才确实一直瞧着他和花见青的一举一动,委实丢人,默了一下,还没说话,花见青已经跑过来,笑意嫣然道:“走吧,我休息好了。”然后又挽住风祁墨的胳膊,撒娇说:“二哥,到下个镇子时,你记得给我买个柔软些的马鞍。”
风祁墨将手抽出来,叹口气:“知道了,记得的。你太顽皮,再这么下去,回去我会让瞿大哥把你送到山里清修。”
花见青做了个鬼脸,显见的是并不怕她二哥这话,翻身上了马,对我们说:“秦姑娘,阮姐姐,我们走吧。”
我心下默然。花见青将对我和阮盈袖的称呼分的这样开,对我的敌意已是昭然若揭。阮盈袖有几分疑惑,看了眼花见青,终究什么也没说,上马仍旧往雾云山庄的方向赶。
星夜兼程,我们在第三天的晚上,终于到了雾云山庄。
有风祁墨带着,一路就往正堂去,然而雾云山庄的仆人也是聪明得很,我们到正堂时,瞿映月已经接了通禀,在主位上好好坐着了,甚至连茶,都恰恰泡好。
风祁墨半点不惊讶,和瞿映月点头笑笑,便在下首坐了。阮盈袖见我有些疑惑,就小声解释说:“雾云山庄是做什么的?倘若连个雾城都控制不了,也不能有那样大的名声了。恐怕我们刚进城,瞿大公子这里就得了消息。”
我赞叹一番,同阮盈袖一起上前见礼。瞿映月面如冠玉,年纪大约三十上下,仍是风流倜傥的模样,说起话来和风祁墨给外人的印象一样,如沐春风,又温雅有礼。他先起身拱手向我道:“秦姑娘名满江湖,得见真是幸运。”
我连忙说“不敢”,瞿映月又对阮盈袖一礼,说:“阮姑娘,又见了。”
我脑袋里转了一转,才想起先前程厉重伤,是瞿映月将他送到阮盈袖的医馆。阮盈袖也回礼,抿着嘴,面色凝重,却不问程厉的伤势。
瞿映月请我们坐了,这才看向花见青,目色凝重,她正自顾自地喝着茶,对于瞿映月简直要燃起来的怒火视而不见。
风祁墨倒咳了一声,开解道:“三妹这样,倒也是好事。她从没独自一人出过门,这下到底算锻炼了。”
瞿映月走到花见青身边,把她手里的茶杯重重夺下,放在桌上,冷声道:“你可知师父临终前最担心的就是你此生的安危,如此不管不顾,把师父的嘱咐放在眼里了吗?”
花见青之前好一副闲暇的样子,忽然就像炸了毛的猫一般跳起来,顶撞瞿映月道:“怎么了?师父心疼我,也心疼他的大徒弟和亲儿子,如今二哥出门了,我接应一下怎么了?”
瞿映月看她一眼,仍旧十分冷:“你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跑出家门,”说着他向门外吩咐,“来人,将三小姐关在晴屿阁,没我的命令不准出来半步。”
花见青仿佛不相信,吵闹说:“你竟要关我禁闭!师父在时谁也不敢这样!”她转脸向风祁墨,一脸哀戚,切切地喊:“二哥。”
风祁墨摇摇头,只道了一句“该罚”,便没再理花见青的眼神。
瞿映月拂袖向主位走去,话里话外仍是冰冷:“好好反思,早点想好了早点便放你出来。”花见青见求饶无望,跺了跺脚,委委屈屈地随着仆人下去了。我和阮盈袖简直想缩成一粒米那么大,究竟是人家的家事,我们却看了全程,真是不好意思……而又激起我们的八卦心理啊。
瞿映月很快调整了情绪,仍是温文的样子,向我和阮盈袖说:“让二位姑娘见笑了,舍妹顽劣,想来一路上也给二位惹了不少麻烦,这里向二位赔罪了。”
我忙推辞:“瞿公子太客气。花三小姐十分聪慧可人。”本来我还想为花见青描补两句,然而想起来她对我的敌意,委实装不出那等大度。
瞿映月点头笑道:“两位姑娘自然是大人大量。”然后又看着阮盈袖说:“阮姑娘稳重踏实,颇有耐心,没有一上来便问程公子的事,而让我先处理了舍妹的事,确是聪明人,怪道能从江家手中救回程公子一命。”
阮盈袖容颜一下粲然起来:“瞿公子是说,程大哥有救?”
“是有救,然而舍妹想来也和你们说了,情况十分不好。”瞿映月微叹,“我请来雾城最好的大夫,却只道命是捡回来了,然而重伤到底不治,三月之中,程公子怕是要五脏六腑渐渐衰退而亡。”
阮盈袖呆了一呆,我也说不出什么话来安慰,只握住了她的手。过了一会儿,她慢慢静下来,语气平缓:“那么瞿公子,我去看看他吧。”
我知道阮盈袖医术也是高明,便轻声说:“你去瞧瞧,说不定雾城那大夫竟是个庸医呢。”
阮盈袖冲我笑笑,随着瞿映月往内堂走了。
风祁墨品着茶,只笑着看我,我默了一会儿,问他:“雾城这大夫怎么样?”
“实不相瞒,”风祁墨这才和我说了实话,“我瞿师兄的医术其实已经很好了,当得起一个妙手仁心,只是他竟没把握治好,还又请了人来瞧,可见不治。说起来这个程厉,也是命途多舛,师兄第一次见他也是重伤,略略给他治了治,又续着真气,才能护住命送到阮姑娘的医馆医治。结果这次又被重伤,想来新伤旧病一齐发作了。”
我叹一回气,又问:“雾云山庄不做赔本的买卖,瞿大公子千方百计救他是为着什么?”
风祁墨赞叹道:“你竟能问得这样的问题,真是和我在一起之后聪明不少。”他不顾我黑下去的脸,接着“啧啧”表扬一番,才正色说:“其实因我走的急,具体的情况我并不知晓,只知道程厉此人,不知用什么法子,拿到了江家很宝贝的一把扇子,唤作绸云扇。那回也是巧合,我师兄因有急事赶路,走的是丰城郊外的山间小道,看到他和一位女子齐齐从崖山摔落,师兄拼尽全力接这二人。给那女子切脉之后,发现筋骨尽折,是活不过当日了,他倒还有气。我师兄救他时,又出了些波折,看到他身怀绸云扇,便留了心,先草草给他包扎了下,见有些剑伤十分深,不能车马劳顿,就带着他问了我们在丰城的势力,知晓最好的医馆是阮姑娘开的,又知晓这人是得罪了江家,具体为何一时也难以查出,便先送他去了医馆,又留了话让他来雾云山庄找我们。因江家其实和我们干系不大,只是向来名声不好,每每作恶,所以师兄稍注意了一下,却也没想过程厉不来找又如何。毕竟丰城势力错综,雾云山庄也不是事事都能插手。一个听天由命,倒害的程公子如此这般。”
我摇摇头:“这却也不是雾云山庄的错。一个人能力本来有限,管不了那许多事,这一回究竟是命中注定。且瞿大公子有制衡江家的心思,已经难能可贵。”
风祁墨笑道:“我是这样想的,然而我师兄却是心怀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