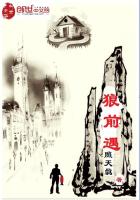令狐北显然打了个寒颤,撇了撇嘴,道:“哎,谢姑娘就没法开玩笑。我这嘴是关不住的,我还是出去晒太阳好了。”
谢姑娘应了一声,道:“别忘了,还欠我二百株湘妃竹。如今春末夏初,正是湘妃竹迁植的好时候!”
令狐北垂头丧气的跑了出去,边跑边嘟囔道:“再怎么说我也查到了华阴地宫和灵宝阁皂宗。怎么还是我输了!湘妃竹,湘妃竹,还得跑一趟河南去找……”
谢姑娘微微一笑,将木盘汤药轻轻放到童旭身旁,而后取了一床薄被,抬起童旭的脑袋后,将被子垫在了童旭的脑勺下面。
她这一动,虽说动作极其轻柔,但童旭仍觉得颈部如同万针攒刺一般。若不是他好面子,不忍在美女面前失态,只怕早已喊将出来。
谢姑娘见他这般强忍,面色一时赤红,便缓缓说道:“疼就喊出来,没什么丢人的。我是大夫,你是病人,病人在大夫面前喊疼,不算失态。”
童旭眨巴眨巴眼睛,却依旧硬着腮帮子,一声不出。汗却流了下来。
谢姑娘取出一方手帕,给童旭擦擦汗,道:“你倒是硬气。这般的伤,便是江湖好手也挺不过一时半刻。想不到你竟然跟着令狐北上蹿下跳的爬了个华山。”
童旭眼珠一转,暗自忖度:“我是爬了华山才逃脱的?”
谢姑娘摇了摇头,道:“别多想,先吃药。吃过药去,提提精神,我再和你讲。”说着,便用木勺舀了一勺汤药,伸到童旭面前。
童旭满目感激之情,忍着剧痛张开口,谢姑娘便一勺药灌了下去。
那汤药初闻气味平淡,入口之处也不怎么难喝。可等药液混合唾液流至舌根,一股难以下口的感觉登时袭来。满口苦涩辛辣也就罢了,更还夹杂这一丝腥臭味。童旭喝得直欲作呕,舌根都直了。
谢姑娘却是说道:“将舌根压住。喉管里不能跑半分药力!”说着便又舀了一勺,递到童旭面前。
童旭有了经验,竟是死活不开口。他宁愿就这么躺着挨痛,也不想再尝一口。
谢姑娘见他不动,便微微叹了口气,道:“死都不怕,还怕吃药么?”说着便随手扯出一只细如牛毛的银针,看都不看的便扎在了童旭腮边的颊车穴上。
童旭只觉得牙根上力道瞬间全无,嘴便张开了,谢姑娘毫不客气,一勺一勺的将药全部灌了进去。
童旭只觉得活了十八年,竟无比此事更痛苦的事。当那难喝至极的药入喉之后,便有一股热流直下胸腹之间,所经之处更是如利刃搅动一般,疯狂的肆虐着自己的五脏六腑。
童旭眼中全是不解,盯着谢姑娘,似乎在质问:“这不是药,这是毒!”
谢姑娘一言不发,反而将药碗放到了童旭的脑袋旁边。
所幸,童旭的混元功内力还不曾消耗殆尽,当药力到达每一处,便总有一定的内力涌出与之抗衡。但苦于内力断断续续的不能一气贯通,是以并不能将药力中途截止。
怎么会这样?受伤过重致使身子不敢动弹也就罢了,怎的内力也不能运行周转?
童旭的心里突然划过一丝不详的预感。
他急忙催动奇经八脉调动内力,却发现,无论那一条经脉,都无法将内力完全调动起来。能做到的,就是一股又一股的内力脉动。或者说,存留在奇经八脉中的内力,被硬生生截断成了一节一节。而每一节内力,只能在自己的控制下,发出微弱的回应。
自己的经脉,断了!
童旭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师父公冶琼面临过的灾难,又一次降临到了他的身上。而且,比公冶琼更为彻底的。自己奇经八脉,尽断!
难道,我就这样废了?
童旭登时眼圈一红,继而只觉得胸口处一阵气血淤积,一股比适才的药液还要滚烫的东西涌了上来,接着,便是“噗”的一声,一口黑血吐出。
谢姑娘动了。她将药碗在空中一张,玉掌晃动间,已经将黑血尽数接了下来。却只见童旭吐出的那口血液里,竟还有早已凝结的血块!
一口黑血喷出,童旭气色便弱了几分,脸上一片蜡黄,还挂着滴滴汗粒。
谢姑娘将药碗一放,用手帕擦了擦童旭的额头,然后缓缓说道:“不要以为你废了!相信我,不出三个月,还你一个生龙活虎的童旭!”
“什么!”童旭心头一惊,不可置信的看着谢姑娘。经脉不是筋骨,断了还能康复?,还有,她是如何看透我的心思的?
谢姑娘微微一笑,道:“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只是你不敢想罢了。也不要惊讶于我能看得见你的心思。因为心事这个东西,你嘴上不说,眼里就冒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