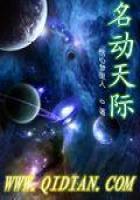午餐是茶楼妹打电话叫外面餐馆送过来的,四个人打完牌,简单收拾了一下桌面,茶楼妹拿来几张报纸铺在上面,便呈上三菜一汤,菜品是两荤一素。廉古六在旁看了,竟然搭配有致,色香俱佳,硬是引人食指大动,不由开口询问:“看上去很不错啊!不知道这几个菜会收多少钱?”
“熟人熟事的,还怕要赚钱吗?随便拿点,不让亏本就是。”其中一个肥头大耳的大汉是大嗓门儿,一开口说话,就像在吼一样,如果隔近了他那油光光的嘴巴,不免要震得耳膜嗡嗡作响。
廉古六就是被吓了一跳,赶紧闪远一点。那被茶楼妹称作老板的汉子笑了笑,说:“丘二给老板送饭,还想收高价,想被炒鱿鱼了嗦?”
廉春雷上午输了不少,此刻情绪低落,只是简单地给众人介绍了廉古六,在座的都与廉春雷平辈,廉古六只得挨个叫叔叔。
大嗓门的胖子姓赵,叫赵贵本,就在距茶楼百米之遥的地段开了家川菜馆,取名食味轩,请了个特别牛叉的厨师叫暴东,两个人都喜欢跑到汇缘茶楼来打大贰,暴东上午没事,临到中午大厨该坐镇饭馆了才被老板赵贵本替换下来,暴东刚才是输了钱走的,不过赵贵本一来,多的都赢了回去。
另一个中等身材的汉子姓冯,叫冯相义,是开鲜花店的,把店交给女儿经营,自己一天到晚泡在茶楼,也是个大贰爱好者。
汇缘茶楼的老板姓李,叫李恩生,剃了个平头,皮衣下面的身材匀称结实,给人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那茶楼妹名叫唐秋玲,与自己老板关系暧昧,打牌的几人偶尔对两人的关系调笑几句,李老板也不避讳。
廉古六在心底暗暗比较了一下,发现只有大伯气势偏弱,这就难怪要输钱了。廉古六从小智力超群,人又是特别的顽皮,比他大几岁的堂哥廉小虎都常常被他整哭。照理说,像廉古六这样的孩子一路考上大学,都是很简单的事,那为何还落榜了呢?原因嘛就是廉古六把聪明劲都用偏地方了,课外活动特别丰富多彩,像斗地主、打大贰这种带有赌博性质的事情,廉古六学会了就不会忘,这也是刚才廉春雷一见到廉古六马上就想换手气的原因。
几个人围坐成一个圈子,只有叫唐秋玲的茶楼妹在一旁站在吃,桌上菜品,色香味都合适廉古六关于佳肴的标准,廉春雷提议四个人喝一瓶白酒,名叫冯相义的男子说道:“算了,要喝晚上喝,马上就开始打牌了,晕乎乎地光吃包子。”
廉古六想想好笑,为地方语言的精炼叹服。这冯相义口中说的吃包子,就是指在牌桌上打牌时,若出现犯错又被牌友发现,就必须按规定赔偿损失。在大贰桌上,常有搞错规矩赔钱的赌友在哀叹:妈哟!这个包子才贵也,几百块!要是换在地方这么说,不免让人误会在其它涉黄的地方去了。
吃完饭,唐秋玲麻利地收拾干净赌桌,拿来一付新大贰牌,再给在座的各位泡茶。大嗓门的赵贵本一边将牌拆封,一边对廉春雷嚷嚷道:“老廉,你和你侄儿到底哪个上?先说哈,最少二十盘打完了才可以换人,中途换人不可以哈。”
廉春雷说:“行啊!我手气差得很,就让我侄儿来陪各位老板。”
四人搬庄,依次坐下。李恩生最先做庄,廉古六与其是对家,第一盘数底。一付大贰牌从一到十,各四张,再有一个大写的从壹到拾,也是各四张,共八十张。二贰、七柒、十拾这二十四张牌是红色的,其余全为黑色。胜了喊割了,也有喊胡了的。十胡起割,十胡至二十胡都为两棒,二十一胡至三十胡为三棒,以此类推。割红时(胡牌时全为红色)按棒数翻两倍,割黑(胡牌时全为黑色)翻四倍,包子按三棒计算赔偿损失。
廉古六了解清楚到底依软割还是硬割以及包子的规模后,就开始数底,留了十九张牌在桌上,其它被三个人拈到了手上,李恩生是庄家,手上二十一张牌,赵贵本与冯相义是闲家,手上二十张牌。数底的歇息,等这盘牌打完,要是对面庄家割了牌,还得继续数底。不管桌上哪家割牌,数底的人都会得到两棒的进账,所以打大贰牌的赌友都巴不得自己盘盘数底,稳赚不赔。
廉春雷在一旁看着,这时手机响了,接听原是******叫出诊的,要是廉古六没有坐下去,多半会被廉春雷推迟到散了牌局再去,此刻没事,本来又待去银行取些钱做赌资,就应了出诊的事。其它三人听了,纷纷叫廉春雷快走,有廉古六在这顶着,只是去拿钱来付账即可。
“拳怕少壮,牌怕新手!我看你三个都会输给我侄儿!”廉春雷啐了一口,笑着出门走了。
第一把李恩生便割了牌,是三棒。赵贵本与冯相义各甩出四张百元钞票在桌上,李恩生将其中两张钱轻轻推到廉古六面前,笑着说:“好生点数!割红割黑了吃喜,合作愉快!”
“哎呀!你们打好大哟?不是十块钱一捧吗?”廉古六大吃一惊,急忙问道。
“他怕十块钱一棒?!十块钱一胡,一棒十胡,百块钱一棒!”赵贵本又冲廉古六嚷嚷开了。
“你怕啥子嘛?你帮你大伯打的,输赢你又不照!年轻人得要有胆量哦!”冯相义附合道。
李恩生玩味地看了看廉古六,最后说:“你不用担心,你大伯取钱去了,你给我好生点数底就是。钱不够,找前台小唐拿。”
廉古六心中七上八下,倒不是担心牌艺不精,而是兜里钞票太少。上了这种场合,要是遇到割红割黑这种大牌,那可是连一盘都不够开的。在这巨大的心理压力下,廉古六是小心加小心再加谨慎,任何有一丝冒险成份的牌机都宁错过,也放过。也不知是廉春雷出门前的诅咒灵验了,还是新手的确手硬,二十盘下来,廉古六竟然割了有十一盘,其中还有两个红胡。
赵贵本直嚷“邪门”,冯相义也嘀咕“遇到鬼了”,有李恩生不动声色,显然牌品上流。
第二个二十盘再搬庄,廉古六换了与赵贵本做对家。第一盘又是廉古六数底,赵贵本做首庄。廉古六数好牌后,说了句上个厕所,便出了包房来到拐角一个单独的洗手间里,插上了门,然后从几个口袋中掏出一把一把的钞票理顺叠整齐。厚厚地一大摞,数了几遍,都是八千六百块,除去自己口袋中的一千六,竟然在短短一个小时赢了七千块钱人民币?!
这赚钱也太容易了吧?跟抢钱差不多。廉古六心中砰砰直跳,兴奋劲儿盖过了心底隐隐地害怕,原本白净的脸庞此时变得通红。
这个时候廉春雷急火火地赶了过来,廉古六提议让大伯换下自己,原先嚷着中途不准换人的赵贵本首先喊要得!冯相义也阴测测地说道:“老廉,找了个高手来哈!我们三个人身上的肉都被你侄儿一个人割了。”
“哈哈!终于给我报仇了!”廉春雷听得廉古六手气这么红,不免有些后悔自己坐下来。但赌徒心性又让他不服气,毕竟廉古六初出茅庐,仅仅是运气而已,俗话说姜是老的辣,自己输钱,输在运气。现在被廉古六这么横插一杠子,运气还不乖乖地给我回来?
这时,又有******找廉春雷出诊,廉春雷伸出一根手指对几人晃了晃,轻嘘一声,放下牌扣上,然后对电话里的人说道:“我现在很忙啊,实在是真的走不开。要不,我安排我们畜牧站的一个人过来?好嘛!我把你的电话给他,到了给你电话。最多也就十来分钟就到。”
廉春雷看到廉古六摸出一个新手机,便拿眼望了一下李恩生,将******的电话号码说了给廉古六记在手机里,又将一串钥匙给了廉古六,说道:“摩托车就在楼下,医厢在茶楼前台,顺着胡家坡那条大路走,过去几分钟就到,要不你就问金顺煤矿在哪里,挨着的,到了地就打这个电话,别人在等起的。”
廉古六接过钥匙,说把赢的钱交给大伯,正要掏口袋,廉春雷不耐烦地挥挥手,说:“你自己赢的钱,不用给我,各人揣着。医了猪就回畜牧站,要是遇到你大妈别说我在打牌。好了,快走!别影响我们打牌。”
廉古六走出包房,到前台找唐秋玲取大伯存放的医箱,唐秋玲媚眼放电,笑着说要廉古六请客,廉古六只得随口应了,下得楼来,骑了摩托车往胡家坡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