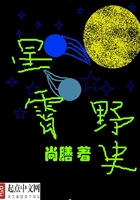蒋惟一向不是认命之人,否则他也不会这么多年里暗中谋划那么多事。
蒋家传承数代,到了他的手上,才能放出万丈光明。蒋惟自年少时就有野心,一步一步,一级一级,他从来没有认输过,没有后退过,所以才能数次向死求生,赚来这大好的局面。
朝中有培养的亲信,内有定北军的旧案可以利用,外有西凉做友军,加上对江州王的因势利导,虽然外人多半不看好他的举事,但他自己心里清楚。只要西凉一发兵,这天下大势必将混乱。燎原之势一起,诸多野心者都会借势而起。而到最后,胜利者只会是他,只有他会笑到最后,只有他能带领蒋家获得不世之荣耀,坐拥天下之权柄。
然而再多的手段,再多的筹谋,也敌不过眼前这个女子的轻轻一撞,轻轻一捏。
一力降十会,不外如是。
蒋惟心里懊恼后悔,如果不对定北军旧将抱有期待,如果在见到魏昭时能仔细地打量他的相貌,如果那时能想起京中街上的偶遇,如果能将那张睥眤天下的傲慢的脸及时跟魏昭的脸对上,那么他现在或许就不用被人塞在间破庙里受这样的折辱了。
只是有钱难买早知道,世上从无后悔药。
蒋惟在心里暗暗发誓,若有一日可以脱困,他不惜任何代价,一定要将眼前这个女人千刀万剐,火烹油煎,方能消心头之恨。
然而现在,他不能对明殊表现出丝毫的怨忿和仇恨。
想了又想,蒋惟终于开口,声音嘶哑,几乎听不出来原本的腔调。
“明将军,你在宇文焘那里不若明珠暗投。他那个人心胸狭小,睚眦必报。就算你曾为大盛立下过汗马功劳,但一旦他发现你其实是个女子,一直在欺瞒他,他必定会治你的罪。”
明殊笑了笑。
蒋惟又说:“如今天下已非向年之治平,北有北戎,西有西狄与西凉,无不兵强马壮,对我朝虎视眈眈,宇文焘和他老子于权势看的极重,当年薛靖那般的英雄,也不过是因为军中积威太盛,让先帝觉得军中只知薛帅而不知陛下,便对他有了猜忌之心,借故除去了他。你武功盖世,神勇非常,将来说不定便会成第二个薛帅。”
顿了顿,他双眼微眯说:“我知道你与庆平侯两~情~相~悦。若是将来你恢复女儿身,嫁于顾昀,焉知他将来不会成为第二个薛靖,而你又不会成为第二位阳羡公主?”
“所以呢?”明殊双手负于身后,双目平静地看着蒋惟:“你对我说这些,是想我怎么做?”
“你放了我,我与你立约。”蒋惟双眼发亮,将木然的身体微挪了挪,“庆平侯手掌云州军,监管青州军,手上雄兵三十万,龙姿凤章,较那些懦弱无能的皇子强过不知几许,又何甘俯首为臣?我与西凉太后交好,朝中也不乏故朋旧交,你我共谋天下,事成之后,可以长江为界,你北我南,分庭而治。到那时,顾昀为帝,明将军为后,子子孙孙可享富贵荣华,岂不快哉美哉?”
明殊微微一笑,脚尖在地上划了好几个圈。
蒋惟谨慎地看着她:“如何?”
明殊将头一歪:“我为何要信你?”
听这意思,竟是有几分意动?蒋惟暗暗松了一口气。
“你我可以定下盟誓,请摘星楼楼主为证。”
“她是你的盟友,又是胡人,我可不信她。”
“她虽为胡姬,但向来说一不二,十分有诚信。明将军有所不知,摘星楼在西域势力极大,多少皇家宗室都买她的情面,便是因为她守信之名人人得知。且她与我不过是金钱往来,我付钱请她做些事,并非友人。”
明殊笑了起来:“蒋大人大概忘了吧,我当年在青州杀过不下二十个摘星楼的杀手,还拐走了摘星楼七煞中的玄煞和兰煞,摘星楼楼主心里不知有多恨我,别说见证誓约,只怕她一见我,第一个便要杀了我泄愤。”
蒋惟闻言一噎,果然没有想到此处。亦或是他暗意识里也正希望摘星楼楼主能将眼前这女子除去吧。
他面上不动,口中说道:“便由明将军指定一人也无不可。”
明殊背着手走了几步:“不过一张纸,约的住君子,却束不得小人。蒋相爷您说您是君子还是小人?”
蒋惟嘴角抽了抽,抬头看着她,却见火光中,带着英气的女子嫣然一笑:“不管你说你是什么,我都不会觉得你是个完全的君子。若是君子,便不会勾结外族图谋社稷,亦不会随便寻个小子便指认他为皇室宗族,不会借着薛帅的名头,拿着定北军万余人的血骨诓骗世人,狡取天下。”
蒋惟瞳仁微缩,在她身上,他似乎又隐约看到了另一个人的影子。
“你已见过那些信函,当知我并非借薛帅之名,而是宇文焘确实做了人神共愤之事,不配拥有这天下!魏冉是定北军旧将,与薛靖情同兄弟,如今仇人就在京城端坐,踏着万千人的尸骨享受着这天下,你们父女却帮着仇人来对付我这正义之师,薛帅九泉之下,当是何等痛心失望?”
“你敢对天起誓,那些信函为真?”明殊走到他身前。
蒋惟冷笑道:“自然是真,明将军得帝后青睐,甚至居于宫中,定是见过皇后墨宝,可曾觉得那信函里的字有几分眼熟?”
明殊点头:“看着是像皇后娘娘的笔迹。”
“上面有魏王焘的私印,也做不得假。日后有机会,你可以去找来比对。”
明殊再点头:“我相信这印是真的。你既然要做伪,自然要做到天衣无缝。不止印是真的,连所用黄帛书也是宫中内造,且帛色,纸色,墨色都有年岁,找个匠人来验,他也会说,此成书必不少于二十年。”
蒋惟目光灼灼:“当是如此。”
“可惜啊,你算的再精细,也还是疏忽了一点。”明殊索性坐了下来,托着腮看着蒋惟,“魏王与北戎谋事,为何所传书信要出自王妃之手?皇上和娘娘青梅竹马,夫妻情深,的确,有时候他是会拿政事回去与皇后商量,但你觉得陷害薛靖,勾结北戎的事,他也会与皇后说,甚至请她代笔吗?”
蒋惟一怔。
“外人只见皇帝信重皇后,却不知道信重之后更有爱慕和保护。”明殊说道,“对皇后,皇上是会拿命去护着的。因为在他心里,她才是他此生最重要的那个人。就算皇上有后宫嫔妃,有曾经宠爱过的淑贵妃,你又怎知他对皇后不是全心全意,不是在拿那些女人为皇后竖起挡箭牌,让她在后宫能安全呢?”
“因为你没有这么深深地爱过一个人,在你的心里,不管是正室夫人,还是姬妾子女,都是为了权势可丢可抛之人。宜王如此,贵妃娘娘如此。你觉得以皇上的个性,应该不会亲手写信以落人话柄,便以皇后笔迹代之。却没好好想过,当年皇后叔伯和兄长都为北戎人所害,她与北戎有血海深仇,怎么可能同意夫君与北戎勾结?而且,阳羡公主与她情谊深厚,若是她参与谋划,不会用这种方式令薛家灭族,而是会想别的方法,既杀了薛靖又为薛家保下薛易。”
“可那时,偏偏有人设伏下毒,全灭了定北军前锋营,一定要薛易死,要薛家断子绝孙。”
“皇上的笔迹不好模仿,因为墨宝到处都有,有人说仿,细究之下也能查出端倪。可皇后就不一样了,除了宫中命妇,谁能得一两笔皇后娘娘的手书?女子笔力纤柔,笔锋不显,气势不足,最好仿了。”
“可是那信函之中的来往,十分真实,丝丝入扣,如羚羊挂角,没有作伪之气。那么问题来了。便是仿,也要有东西对照着描摹,也就是说,信函虽伪,但信函之事确实是真的。蒋相爷,你手上那些真信函在哪里呢?是当年的哪位殿下在与北戎谋划的呢?”
明殊嘴角始终噙着笑意,却是目光冷冰如剑,毫不容情地刺透蒋惟的身体。
蒋惟与她对视了许久,终于还是转开了视线,平淡地回答:“你既不信,那便算了。”
明殊吐了一口气,强自压下积聚多年的悲愤与痛恨。喃喃自语道:“有时候,我真想一刀砍下你的头颅就回去。可是,你活着会更有用处。”
蒋惟头皮一阵发麻,似乎此时才想起明殊曾经一刀砍断北戎汗王的光辉事迹来。这是威胁,也是警告,让他不要再妄想着可以从她手中逃出生天。一旦追兵靠近,为了全身而出,她一定会不吝于这一刀。
蒋惟心中不甘,眼珠子转了又转:“你是女儿身一事,我二弟三弟皆知。如果我亡于你手,或是你以我为质想打下潞州,我想明殊将军原来是个女子一事很快便会传遍天下。”
“那又如何?”明殊冷冷道,“我是个女子,又如何?”
如何?蒋惟看着面前目光冰冷的女子,一时哑然。以女子身份在军营中过了数载,不止是欺君重罪,这名声也坏透了吧。天下人会如何看她,如何说她,如何议她?就算天子不追究,她以后还要怎么谈婚论嫁?想嫁于公主之子为妻,更是想都别想。
“便是女子,我也能做大盛的将军,执掌一军。”明殊信心满满地说。
若不是处境不由人,蒋惟能笑出声来:“荒谬,世间哪有女子掌兵之理。牝鸡司晨,国将大乱。只要被人知道你是女子,你且等着吧。”
明殊眉毛一挑,笑了起来:“且等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