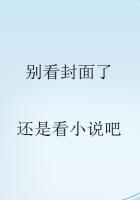梁非白到底隐忍着,没有说什么上火的话。
虽然一个上午下来他一直在隐忍不发,强忍怒火。
出来老街,胖子吃完东西恢复了力气,精神好得开始不停游说着去涠洲岛,什么那儿有滴水丹屏,礁石岩洞,天主教堂,圣母庙……
看梁非白无动于衷的脸色,显然涠洲岛不在他的计划之内。
修长的手擦完汗,他慢悠悠地转过身,眉目认真地看着我,轻起薄唇,“想去吗?”
“不想。”
有时间不如回去研究下案子,只要搞得定案子,之后就是让我上刀山下油锅都成。
胖子见游说不成,不再啰嗦,只道下午出发银滩。
车子一路开回酒店,放下我俩人,说定三点钟左右过来便开了走。
梁非白转身,深邃的眉头拧在一块儿,迷魅地看了我一会儿。
上楼的时候,他忽然身子一顿,让我先回房间,说着便走去了前台,对了,前台的一个女孩子皮肤白白嫩嫩,长相可人。
白一眼,先上了楼。
工作的事迫在眉睫,压堵在心上实在喘不过气,不敢掉以轻心只得又抽空拿出文件来研究,希望临时抱佛脚还来得及。
朗云是这一带的土地商,身家资产财倾天下就不用说了,只是他这为人方面……如果梁非白带我过来真的只是……想在饭局上将我当一件礼品送了,那我是从善如流,还是抵死不从呢。
不,他是……不会这么做的。
“叮咚——”门外响起了铃声。
哦,皮肤白皙的前台小姐。
“您好,请问是林小姐吗?”她笑起来,我才真正知道,什么叫笑靥如花。
“是。”
“这是梁先生交代给您的,请收好。”她递过来,一个欧莱雅的袋子。
来不及诧异,她便已转身走开,而我手里边的竟是沉甸甸的护肤用品。
呐,我又小人了是么。
可是看着那一瓶瓶,一罐罐的,这算什么?
偏头看了眼旁边紧闭的门,梁非白是什么意思,我摸不大清。
一会儿,他端来午餐,进门后就直接放在桌子上,冷淡惯了也不叫我,就干坐在客厅里等我自行出来。
酒店师傅的手艺还蛮不错的,尽管喝了那么大杯冷饮又吃了烧烤,当闻到那股子菜味还是没忍住大快朵颐。
身边的人却有些心不在焉。
即使吃得专注如我,余光里还是瞥到了他直勾勾地盯我的眼神,似乎有那么种“秀色可餐”的意思。
封闭的空间,无论多大,让两个仇人待着格局总归不能说大,我秉着看一眼不会少一块肉的心思,勉强镇定地把饭吃完。
全程无话。
“女生没有不爱美的。”他放下筷子,莫名其妙地突然说道。视线从门口的鞋架上挪回来,声音不高不低,不辨情绪,“别告诉我你是另类。”
原来是怪罪我简单地把他的好意“心领”了。
“女为知己者容,这几日懒得弄。”
眸色陡然暗沉一片,梁非白蹙着眉便凝过来,眸间的锋芒裸露无遗,“你是说,能让你自愿打扮的人,是聂子远?”
笑笑,从凳子上站起身,“我就是不打扮,他也看得过去。”
“哐”一声,他铁青着脸凌然站起,顺带带倒身后的椅子。
藏了一上午的怒气,终于舍得发泄出来了,“我警告你,今天一天少想他!”
看他勃然的样子,我意外发现自己心里竟无比地舒畅,不是自虐意识在作祟,而是知道他这一上午分明没有心思玩游,却硬是走完了这个景点走那个景点。对,下午还要去银滩。
看他带着火气走近,我赶紧跑,蹿进房间才敢喊,要杀要剐悉听尊便!
趁着休息时间,不敢怠惰,于是又拿出来文件,直到后来眼皮实在重得不行,这才上床闭了会儿。
醒来是让老爸的电话吵醒的。
“在外边没什么事吧?你妈让你出门在外自己小心点。”老爸一副转告的口吻,好像其中并不掺丝毫自己的关心。
“没事,我一切都好。我妈呢,有没有出状况?”
“你妈没什么,还不是老样子,倒是小聂,人来家里找了你一回,我说你出差怎么都没跟人家说一声的?”隔着电话,老爸的口气别样的温和。
距离产生美,原来这话用在亲人身上也适合。
挂断电话,不明白聂子远现在还能找我做什么,该说的都说清楚了不是吗。
两点半的时候,隔壁的人又先一步浪荡到我这儿,换了一身衣服人又鲜活起来,儒雅斯文的样子,谁能想到还是中午那个小试身手,河东狮吼的呢。
似是特意监督来的,高挑的身影往客厅里一坐,两腿一搭,就光在那儿拧眉看我忙进忙出。
换了身衣服,洗好脸梳好头,扎弄好头发,等包也准备齐全了,明明还剩下十分钟,有些人却已然摆出一张臭脸。
他站起来,几步走到门口,从鞋架上气势汹汹地拎回袋子。
“拿着!”语气里带上不容拒绝的味道。
僵持了会儿,我道,“真用不上。”
他又怒了。亏得这时候他还能拐着弯来发泄,怒极反笑道,“懒是吧?我来帮你。”
说着,大手一伸,蛮力将我扯进洗手间,跌跌撞撞地也不顾我磕门撞墙,死死地将我箍在胸前,便直接拧开护肤品瓶盖,抓着我的手擦拭起来。
“梁非白!”
“紫外线还很强,我是为你好。”
“放开!我自己会!”
“脸上的,自己抹。”说着放开我,一副完工的样子拍拍手走出门。
楼下。
梁非白戴着墨镜,倚门而立,一副爱等不等的样儿。
等到了银滩,胖子摄像师依旧驮着一老大的机子,换着角度地给我们摄。
银滩银滩,银色的沙子,在阳光的照耀下银闪闪的一片刺眼,祖国的大江南北,奇风异景,真是了不得的得天独厚。
碧海蓝天下,涛涛海水激荡奔腾,自由的浪花一丛丛地溢上沙滩,又一丛丛地退下,循环往复。
渐渐地,视线被脚下大片的螃蟹吸引,与前头梁非白拉开了距离。
“走了走了走了,咱快跟上吧,这没什么好看的。”胖子催促着,因为我和梁非白渐行渐远的距离,他很难调镜头。
望着地上一个个的沙洞,朝梁非白的地方赶过去。他总是这样特立独行,对于别人的缱绻,他素来不会花一点时间去逢迎。
“梁先生在干什么?难道他会水?”胖子的目光落在远处的小游艇上。
不乐意他这么说,“怎么,你小瞧人啊?”
“不是,我看梁先生买的那个游艇是激浪用的,这么激烈的运动看不出来,梁先生这样儒雅的人也会!”
听他这么说,我也诧异,梁非白是要在这里玩激浪?他什么时候会……想来这六年孤身海外,也学到了不少东西。
躺在沙滩椅上。那边梁非白已换上泳衣,朝这边招呼了声立马就跳进了海里。
看着那一片翻涌地异常凶悍的海面,心里边莫名的打鼓,按胖子的话说,梁非白看着斯斯文文,却要玩那样激烈的运动……
“看梁先生的技术,真不错。”还没一会儿,胖子便由衷地感慨起来。
梁非白也已经绕着海浪转了一大圈,此刻还在没命地遨游。在这惬意的时刻,遥望无垠的大海,突然觉得胸腔里有什么东西涌进来,或者有些事,也是时候放下了。
眼下梁非白在海上飘,胖子又趁机八卦道,“林小姐和梁先生真的只是普通朋友?”
银滩上的暖风热乎乎地吹,我笑他可真会没话找话,“如假包换啊。”
“男女之间没有纯粹的友谊。”
“那你今天不是大开眼界了?”
胖子哪里肯信,转身便贼笑了道,“你们俩个,肯定有一个没那么纯粹,要不就奇怪了。”
“哈哈哈,你要是这么说,莫非这天下的蓝颜,又或者红颜知己,都是在打‘朋友’的旗号陪心里人的?”
说不过我,胖子干脆换了话题,提议吃点海鲜。
在胖子去买海鲜的时候,梁非白还在海上飘游,等胖子回来的时候,我也瞥了眼,人正在那高高低低地随着海浪起伏,只是等我海鲜吃到一半,那道身影忽地就不见了……
“他掉水里了!”大喊一声,扔掉烤串,什么都来不及想,撒腿便跑过去。
梁非白的游艇附在海面上,仍看得见,只是人已经不见踪影,他不见了!海水……他在这海水下面!
“胖子!胖子!你快救他!快救救他!”
“啊,我不会啊!”
“梁非白!梁非白!”他不见了……
“你别担心,他不是会水吗,这点浪对他来说没事的。”
“梁非白!”我吼着,转身吼胖子,“他需要帮助!快叫人!”
大概被我丢了魂的样子吓到了,胖子终于嘶喊起来,“救人啊,溺水了!溺水了!大家快来人!救命啊!”
他这一喊,我再支撑不住,果然连胖子也觉得,梁非白即便会水也遭殃了?
这蓬勃不下的海水,巨浪一个比一个猛地击打过来。
怎么办,他该怎么办……
海边的救助队徐徐赶来。
大概两分钟的样子,那骄傲地征服着大海的男人,终于一动不动地被捞上来,平放在海滩上。
胖子急得眉头直汗,哆嗦着拨打110,我冲扑到梁非白身上,直到摸到他的人,脑里紧绷的神经才放下,一时间竟连他是死是活都没管,只觉得他又回到了我的身边,在就好……
“快呀,按压,人工呼吸啊!”有声音指点道。
挣脱出恐怖的噩梦,按声音说的,我开始一下一下地按压梁非白温热的胸膛,他怎么能死,他不能死,就是我死他也不能死!
吐出好几口水,他这才有点反应,眼一睁,彻底苏醒。
克制不住颤抖的嗓音,“梁非白,非白……”
他眨眨眼,眉头紧拧着,似难受的厉害,一会儿一只手费力地触上我的脸庞,摸到我的唇角,呵笑道,“吃什么了……”
他在笑,他还笑得出来!
我只觉得整个人还虚飘飘的抖得厉害,他却对自己方才千钧一发的情况毫不在意,我伤心气急,失控地吼他,“你要死就死远点!别死在我跟前!”
说完退开,凶狠地剥开人群,任后边的声音如何委屈,怎么沙哑,我只想跑开这一片笑话。
打车回到酒店,一路上只觉得头疼欲裂,本来一直自由的心忽然就被拦了下来,不知道跑,便感到一阵累。
不敢去想梁非白今天要真死在这里……
虽然我也曾不止一次地恶毒地诅咒他,祈求上天垂怜,让他阴沟里翻船,钱场失意,却也从不曾想过要他的命。
我承认自己的可悲,时至今日还不能否认,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爱死了他,撕心裂肺的爱!蚀骨钻心!却也无论如何因为伤痕累累而亲竖城墙,隔绝礼尚往来。
房外的门铃不知响了多久,到最后竟如催眠之曲,扶风入梦。
天黑的时候,门铃又闹腾了一阵,我睁眼看漫天星空,浩瀚的星辰渺小也可怖,看久了,缭乱人的眼花。
下床,走进洗手间,对着镜子里的人嫣然一笑,我真是蠢,真的。
我关自己一个下午,有什么用……
他还是会去激浪,在我看不到的地方,他还有生老病死,在某一个天涯海角。
这些跟你有关系吗,林年?没关系。
后来,枕边的手机响起来,我接通。
“开门,出来吃饭。”那醉人的声音,该死的,还带着蚀骨的温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