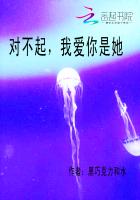“也许是这样吧,”他说道,“你们这些体面人物认为怎么做合适,怎么做不合适,这要看情况,我管不着。好吧,船长,我看您要抽烟了,我也不客气,陪您抽一袋吧。”
于是他便装上一袋烟抽开了。两人不声不响地坐着抽了好一阵烟,一时互相对视,一时停止抽烟,一时向前伸腰啐口唾沫。瞧着他们这些举动,真像看戏一样有趣。
“好吧,”西尔弗又开口了,“言归正传。你把找财宝用的海图给我,不要再开枪打那些可怜的水手,也不要趁着他们睡着了的时候割掉他们的脑袋。你照这么办,我们就给你们两条路,任你们挑选。要么你们就在财宝装上了船之后,同我们一道上船,那么,我就发誓保证,在一个什么地方叫你们安全上岸,说一不二。要是这个办法不合你的意,我手下有些伙伴因为受了气,结下了怨仇,他们可是粗野得很,那你们就可以留在这儿,随你们的便。我们可以把粮食分给你们,按人数计算。我保证只要看见头一条船,就给他们打招呼,叫他们上这儿来把你们接走。你也会承认,这是打商量嘛。更满意的条件,你休想得到,休想。我还希望,”他提高嗓门说,“这木头房子里所有的人都听到我的话,因为我对一个人说的,就是对全体的人说的。”
斯摩莱特船长从门槛上站起来,把他的烟灰在左手掌上敲掉。
“说完了吗?”他问道。
“每一句都说完了,嘿呀!”约翰回答道,“你要是拒绝我的条件,那就再也见不到我了,只好让枪弹见面。”
“好极了,”船长说,“现在你听我说吧。你们要是不带武器,一个一个地过来,我就给你们全都戴上手铐,把你们带回英国去,受公正的审判。你们要是不干,我告诉你,我叫亚历山大·斯摩莱特,我升起了国旗,我就要叫你们去见龙王。你们找不到财宝。你们也开不动大帆船,你们当中没有一个配得上开船的。你们也不能和我们打仗——喏,格雷就是从你们那边的五个人当中逃过来的。你们的船走不动了,西尔弗先生,你们停在背风的岸边,你会明白的。我站在这儿给你说这些话,这是你从我这儿所能听到的最后忠告。当天发誓,下次我再见到你,就要在你背上打一枪。去吧,小子。快滚开,快滚快滚,越快越好。”
西尔弗那副面孔可真是好看呢。他气得要命,两只眼睛都鼓出来了。他甩着烟斗,把烟灰抖出来。
“搀我一把吧!”他大声嚷道。
“我可不管。”船长回答道。
“谁来搀我一把?”他大吼道。
我们谁也没有动。
他像一条恶狗嗥叫似的,发出最下流的骂声,顺着沙地往前爬,直到他抓住了门廊,才勉强站直身子,拉起拐棍来。随后他就往泉水里啐了一口唾沫。
“等着瞧吧!”他叫嚷道,“我可把你们看透了。不出一个钟头,我就要捣毁你们这座破木头房子,像砸破一只酒桶似的。你们笑,老天爷,你们笑吧!不出一个钟头,你们就得上阴间去笑。死掉的就算走运了。”
他恶狠狠地骂了一声,便跌跌撞撞地走开了,在沙地上吃力地往前走,跌了四五跤,才被那个拿白旗的人搀扶着翻过了木寨,然后马上就钻进树林,不见踪影了。
第二十一章 袭击
西尔弗刚刚走得不见了,原来一直仔细监视着他的船长马上就向屋里转过身来,发现除了格雷以外,没有一个人还在守着岗位。这是我们头一次看见他发了脾气。
“集合!”他大声吼道。我们都垂头丧气地溜回来,他就说,“格雷,我要在记事本上给你记一功,你有海员的本色,尽了你的职守。屈劳尼先生,我对你真有点儿吃惊。大夫,我原来总想着你是服过军役的!要是你在封提诺伊就像这样值班,老兄,那你还不如躺在床上睡大觉呢。”
大夫那个小组全在后面几个枪眼那儿,其余的人都在忙着给备用的步枪装子弹。每个人都涨红了脸,当然喽,耳朵里听到的尽是些刺耳的话。
船长一声不响地看了一会儿,随即就说话了。
“伙计们,”他说,“我把西尔弗臭骂了一顿。我故意惹他生气,不出一个钟头,我们就会受到袭击。我们的人手不如他们多,这我用不着给你们说,可是我们打起来是有掩蔽的。刚才我还可以为我们作战是有纪律的呢,现在可不敢自信了。不过只要大家愿意,我毫不怀疑,一定能打败他们。”
然后他又巡视了几遍,据他说,他看到一切都就绪了。
在这所屋子距离较短的两边,东边和西边,只有两个枪眼。门廊所在的南边又有两个,北边还有五个。我们七个人总共足有二十支步枪。柴火摞成了四堆——这就算是桌子吧,每一边中间摆着一张这样的桌子,每张桌子上都摆着一些弹药,还有四支装了子弹的步枪,防守的人顺手就能拿到。屋子当中挂着许多短刀。
“把火灭了吧,”船长说,“寒气已经散了,我们的眼睛可不能让烟熏着。”
那只铁火盆被屈劳尼先生整个儿端出来了,烧过的余烬埋在沙土地里熄灭了。
“郝金士还没吃早点。郝金士,你自己去吃吧,回到你的岗位那儿去吃。”斯摩莱特船长继续说道,“打起精神干吧,孩子。你要完成任务,就得先吃饱。亨特,拿白兰地酒来,每人都给一杯。”
船长一面吩咐着办这些事,一面在心里拟订了全部防守计划。
“大夫,你把守门口,”他接着说道,“注意,别暴露自己,站在里面,从门廊里射击。亨特,你守住东边,喏。乔伊斯,你把住西边,伙计。屈劳尼先生,你是神枪手——你和格雷守住北边最长的这一面,这儿有五个枪眼,危险也就在这一边。要是他们能靠拢这里,从我们自己的枪眼里往里开枪,情况就不妙了。郝金士,你我对开枪都不在行,咱们就在旁边装子弹,出一把力。”
正如船长所说,寒气已经消散。太阳升到我们周围那些树顶上的时候,马上就直晒我们外面那片空地,把雾气一扫而光了。不久沙地就被晒得滚烫,木屋的木条上的松脂开始融化了。夹克和上衣都被甩开了,衬衫也敞开了颈部,袖子也卷起来了。我们怀着极度热烈和急切的心情,站在各自的岗位上。
一个钟头过去了。
“他妈的!”船长说,“这儿闷热得要死,就像无风带似的。格雷,你吹吹口哨,招点儿风来吧。”
正在这时刻,传来了敌人进攻的消息。
“请问您,船长,”乔伊斯说,“我要是看见有人,就可以开枪吗?”
“我是叫你这么做的!”船长大声说道。
“谢谢您,先生。”乔伊斯还是那么温顺地应声道。
暂时没有什么动静。可是船长回答乔伊斯的话却使我们大家都警觉起来,尽量注意听着,盯着外面——枪手们都把枪拿稳,船长紧闭着嘴唇,皱着眉头,站在木屋中间。
就这样过了几秒钟,乔伊斯突然打响了第一枪。他的枪声还没有落,围栅外面就从四面八方接连一枪又一枪打开了,就像一群鹅围着叫似的。有几颗子弹打中了木屋,可是一颗也没有打进来。后来硝烟散尽了,木寨和它周围的树林却像原先一样平静而空荡。没有一根树枝摆动,也没有枪筒发出闪光,表示敌人还在近处。
“你打中敌人了吗?”船长问道。
“没有,先生,”乔伊斯回答道,“我想是没打中,先生。”
“你说了实话,倒是很好,”斯摩莱特船长低声说道,“郝金士,再给他装上子弹。大夫,你那一边来了几个人?”
“我看得一清二楚,”利弗西大夫说,“这边放了三枪。我看见三道子弹的闪光——有两道在一起——另一道在西边较远的地方。”
“三枪!”船长应声说道,“屈劳尼先生,你那边打来了几枪?”
可是这却不容易回答。北边打来的枪很多——据大老爷的估计是七枪,格雷说是八九枪。东西两面都只打来了一枪。这就很明显了,敌人的进攻一定会在北面发展,而在其余三面,对方只不过是随便放几枪,表示他们的敌意,打搅打搅我们罢了。可是斯摩莱特船长并没有改变他的部署。他的理由是,假使叛乱分子进了木栅,他们就会占有任何一个没有防御的枪眼,往我们自己的工事里射击我们,像打耗子似的。
我们也没有时间多加考虑。突然间,只听一阵欢呼呐喊,一小群海盗从北边的树林里冲出来,直奔木寨。与此同时,匪徒们又从树林里开火了,一颗步枪子弹射进了门廊,击中了大夫的枪,把它打碎了。
来侵的贼帮像猴子似的翻过木栅。大老爷和格雷接连开枪,三个人倒下了,一个倒在寨围里面,两个往后倒在外面。但是这三个人当中,有一个与其说是受了伤,还不如说是吓坏了,因为他立刻又站起来,马上就钻进树林不见了。
两个送了命,一个逃跑了,四个冲进了我们的防线,站稳了脚跟。同时在树林的掩蔽下,还有七八个,显然是每人有几支步枪,不断地向木屋这边猛烈射击,但是都不起作用。
来犯的四个人大叫大嚷地跑着,直奔木屋,树林里的人响应他们,给他们呐喊助威。我们放了几枪,可是开枪的人手忙脚乱,看来大概是没有一枪打中了。片刻之间,那四个海盗就冲上了土丘,向我们扑过来。
水手长乔布·安德生的头在中间那个枪眼出现了。
“揍他们,一齐开枪——一齐开枪!”他发出响雷一般的吼声。
就在这同一时刻,另一个海盗抓住亨特的枪筒,从他手里夺过了步枪,从枪眼里往外拽,又猛然一击,把这可怜的小伙子打昏了,倒在地上。另外还有一个没有受伤的家伙绕着木屋跑了一遭,突然出现在门廊下,举起短刀向大夫砍杀。
我们的处境完全逆转了。刚才我们有木屋做掩护,向暴露在外的敌人射击;现在却是我们自己失去了掩护,无力还击了。
木屋里硝烟弥漫,这对我们的安全倒是稍有好处。在一片手枪互击的火光和响声中,双方大叫大嚷,乱成一团,这时候我听到一个响亮的呼声。
“出去,小伙子们,到外面去跟他们搏斗!拼短刀!”船长大声喊道。
我从柴堆上取下一把短刀,同时另外有个人也操起了一把,割破了我的指节,可是我当时并没有觉出来。我冲出门去,来到明亮的阳光之下。有个人紧跟在后面,我不知道是谁。在正前方,大夫正在把袭击他的那个匪徒追下土丘,正在我看到他的时候,他敲掉了那个家伙的刀,把他打得仰倒在地上,给他脸上拉了个大伤口。
“绕着房子跑,小伙子们!绕着房子跑!”船长大声喊道。虽然在那一阵骚乱中,我还是听得出他的声调变了。
我机械地服从他的指挥,往东面转去,举起短刀,绕过屋角往前跑。马上我就面对面碰上了安德生。他大吼一声,把他的腰刀举到头顶上,在阳光中闪闪发亮。我根本没工夫感到恐惧,可是因为对方马上就要砍下来,我突然往旁边一闪,在松软的沙地上没站稳,就一直滚下土坡了。
我最初从门口冲出来的时候,其他的叛乱分子已经拥上木栅,企图全部消灭我们。有一个戴着红睡帽的家伙,把腰刀衔在嘴里,竟站在木栅顶上,跨进一条腿来。中间相隔的时间极短,我重新站起来的时候,一切还是原来那样,戴红睡帽的那个家伙还没有完全跨进来,另外一个刚刚在木栅外面露出头来。可是就在这一瞬间,战斗结束了,我们获得了胜利。
格雷紧跟在我后面,他趁着那个水手长还没来得及再举刀砍杀的时候,先把他砍倒了。另外有一个家伙正在从枪眼外面往里开枪的时候,已经挨了一枪,现在正在地上躺着,连声呻吟,手里拿着的手枪还在冒烟呢。还有一个,我已经看到大夫一刀就把他干掉了。爬过木栅的四个匪徒,只剩下一个还没有收拾掉,他把腰刀丢在战场上,现在正在吓得要死,又往木栅外面爬出去。
“开枪——从屋里开枪!”大夫大声喊道,“小伙子们,你们也回屋里去吧。”
但是大伙儿都没注意听他的话,没有人开枪,最后一个进犯的敌人就乘机逃脱,和其余的人一同钻进树林里不见了。在三秒钟之内,来犯的一伙匪徒就只有五个被击毙的家伙留在我们这儿了,四个在木栅里面,一个在外面。
大夫、格雷和我飞快地跑进屋里,获得掩蔽。那几个幸存的匪徒丢下步枪逃跑了,很快就会回来。双方随时都可能重新开火。
屋里的硝烟现在多少散开了一些,我们一眼就看得出我们取得这次胜利,付出了多大代价。亨特被打晕了,还躺在他的枪眼旁边;乔伊斯也在他自己的枪眼旁边躺着,脑袋被打穿了,再也不能动弹了。屋子当中,大老爷搀着船长,两人都是面色苍白的。
“船长受伤了。”屈劳尼先生说道。
“他们跑掉了吗?”斯摩莱特船长问道。
“跑得动的都跑了,说实在的,”大夫回答道,“可是他们当中有五个永远也不会跑了。”
“五个!”船长大声说道,“嘿,这又好些了。他们损失五个,我们损失三个,结果我们就成为四对九了。现在的力量对比总比开始的时候好一些了。当时我们是七对十九,也可以说是我们以为是这样,那可真是难以对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