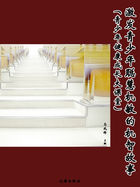军事法庭于星期二早晨开庭。整个过程很简短,只不过走了走形式,仅仅花了二十分钟。其实,也没必要多用时间,被告不得辩护,而证人只是那个被打伤的暗探和队长,还有几名士兵。判决书提前已写好。蒙太尼里已送来了他们所需要的表示同意的非正式通知,因而法官们(菲拉里上校、当地龙骑兵团的少校以及瑞士卫队的两名军官)要做的事情就极少了。大声念过起诉书之后,证人提供证词,判决书也签了字,随即庄严地向死刑犯宣读。牛虻默默无语地听着,当按照正常程序问他有什么话想说时,他只是不耐烦地挥挥手把问题岔开了。他怀里揣着蒙太尼里落下的那块手帕。昨天一整夜,他对着手帕又是亲吻又是落泪,好像那是个活人一样。此刻,他脸色苍白、表情呆滞,眼皮上仍有泪痕;但是,“处以枪决”的判决词对他似乎没有多大的影响。当这项判决念出来时,他的瞳孔有些放大,此外再无别的反应。
“把他带回囚室吧。”当所有的仪式都结束后,总督吩咐道。那个显然已快落下眼泪的卫队长在这个纹丝不动的人肩上拍了拍。牛虻微微吃了一惊,朝四周瞧了瞧。
“啊,对不起,”他说,“我走神啦。”
一种近乎怜悯的表情出现在了总督的脸上。论天性他并不是个残忍的人,内心暗暗为自己在这一个月里所扮演的角色感到有点儿羞愧。既然主要的目标已达到,他情愿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做一些小小的让步。
“你不用再戴镣铐了。”他望望牛虻那肿烂的手腕说。随后他又转身冲着自己的侄子补充道:“他可以待在他自己的囚室里。死囚的牢房又阴又暗,关在那里也只是一种形式。”
他咳嗽一声,挪动了一下脚,分明很窘迫,随后把正要带犯人走出去的卫队长叫了回来。
“等等,队长,我想跟他说句话。”
牛虻动也没动,对总督的话似乎毫无反应。
“如果你有话想转达给亲戚朋友……我想你有亲戚吧?”
没有回答。
“好吧,你考虑考虑,然后告诉我或者牧师。我会尽心办理的。你还是把口信交给牧师吧,他马上就来,夜里陪着你。如果还有别的要求……”
牛虻抬起了头。
“请告诉牧师,我情愿一个人待着。我没有朋友,不需要捎口信。”
“可你需要忏悔呀。”
“我是无神论者。我什么都不需要,只求得到安静。”
他的声音淡漠、平静,既不含蔑视也不含激愤;说完,他慢慢地走了。到了门口,他又留住了脚步。
“让我给忘了,上校,有件事我想求你。明天不要让他们绑住我或蒙住我的眼睛。我一定会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星期三早晨日出时,他们把他押到了院子里。他的腿瘸得非常厉害,走路显得很艰难,很痛苦,重重地靠在卫队长的胳膊上,但一切倦怠和顺从的表情已荡然无存。黑夜里,在一片死寂中,幽灵似的恐惧压倒了他,阴暗世界的幻象和梦境也萦绕着他,但是一旦黑夜过去,这些也一同消失了;一旦阳光普照,一旦有敌人在跟前激起他的战斗情绪,他就无所畏惧了。
六名执行死刑的枪手沿着布满常春藤的墙壁一字排开。在那次不走运的越狱中,牛虻乘着月色攀爬的正是这堵窟窟窿窿、摇摇欲坠的院墙。枪手们站好,每个人手里都提着自己的枪,简直无法忍住眼里的泪水。派他们来枪毙牛虻,给他们带来了无法想象的恐惧。牛虻和他那犀利的妙语、无穷无尽的笑声以及充满光明、富于感染力的勇气,似缠绵的阳光照亮了他们单调、沉闷的生活。现在他就要死去,而且死在他们手里,在他们看来这就等于扑灭天上的一颗明星。
院子里的那株巨大的无花果树下,他的坟墓正在等着他。那是夜间由一些不情愿的人挖出来的;滴滴泪水洒落在铁锨之上。他经过那儿时,含着微笑望了望那黑魆魆的土坑以及旁边枯萎的小草,深深吸口气,嗅嗅那才从坑里挖出来的新鲜泥土的芳香。
在靠近那株树的地方,卫队长停住了脚步。牛虻四下里瞧瞧,绽出极欢快的笑容。
“要我站在这儿吗,队长?”
卫队长无声地点了点头,喉咙里像堵了个东西,恨自己竟无法求情救下他的性命。总督、他的侄子、监刑的骑兵中卫、医生以及牧师都已经来到了院子里,这时表情严肃地走上前,但一看见牛虻那笑盈盈的眼睛里闪射出的轻蔑的光芒,便有些局促不安。
“早安,先生们!啊,尊敬的牧师,你也起这么早!你好呀,队长?这次见面比上次叫你愉快一些,是吧?我看你的胳膊还吊着绷带,那是我枪法太差的缘故。这些好汉比我的枪法准——是不是,伙计们?”
他扫视了一遍枪手们阴郁的面孔。
“反正,这次用不上绷带。喂,喂,你们何必如此愁眉不展!都站好,表演一下你们精湛的枪法。马上就要有艰巨的工作,会让你们应付不了,根本不像预先练习的那样。”
“我的孩子,”牧师走上前来,打断了他的话说,其他的人退到后边让他们俩单独谈,“再过一会儿,你就要去见造物主了。留给你忏悔的这最后几分钟,难道你就用来说这种话吗?我恳求你想一想,你身上带着这么多的罪恶,不求主赦免就死去,该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当你站在最高审判者面前的时候,想忏悔就太晚了。难道你要带着满口的俏皮话走向上帝威严的神座不成?”
“俏皮话,尊敬的牧师?大概只有你们才喜欢那一套令人厌烦的说教哩。轮到我们动手的时候,我们将用大炮轰,而不是这么六七支破枪,那时你就会看到我们俏皮话的分量了。”
“你们要用大炮轰!啊,不幸的人呀!难道你还没意识到自己已站在了可怕的深渊边沿吗?”
牛虻侧过脸看了看那敞开的墓坑。
“这么说,牧师大人认为一把我放进那里,就一了百了啦?也许,也许你们会在坟头上压一块石头防止我‘三天之后复活’吧?别害怕,牧师大人!我将像老鼠一样静静地躺在你们把我所放的地方。尽管如此,我们还会用大炮轰。”
“啊,仁慈的上帝呀,”牧师高声说道,“饶恕这个可悲的人吧!”
“阿门!”有位骑兵中尉用一种低沉的声音喃喃道,而上校和他的侄儿虔诚地在胸前画了十字。
牧师眼见再坚持下去也没指望收到任何成效,于是放弃了徒然的努力,摇着头退到了一旁,嘴里低声念着祈祷词。他们没耽搁时间,很快就把简单的准备工作做完了,牛虻自动站到指定地点,只是转过头来,朝着红黄色交融的晨曦观望了一会儿。他再一次请求不要蒙住他的眼睛,脸上蔑视的表情逼得上校只好被迫同意。二人都忘了,这会给士兵们带来多么大的痛苦。
牛虻含着微笑,面对士兵们站好,而士兵们手里的枪抖个不停。
“我已完全准备就绪。”他说。
中尉趋前一步,激动得有些发抖。他以前从未发过执行死刑的口令。
“预备——瞄准——射击!”
牛虻摇晃了一下,随即便恢复了平衡。一颗偏斜的子弹擦破了他的脸颊,几滴鲜血落在了白围巾上。另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膝盖上方。
硝烟慢慢散去后,士兵们定睛一瞧,只见他仍在那里微笑,一边用那只伤残的手擦脸上的血迹。
“你们的枪法糟透啦,伙计们!”他说道,声音异常清晰,使那些呆若木鸡的可怜的士兵们醒过神来,“再来一次。”
那一排枪手不约而同发出了呻吟声,身子也颤抖着。每个人都朝旁边瞄准,心里暗暗希望致命的枪弹不是自己而是旁边的人射出的。而现在牛虻仍站在那里冲他们微笑;他们只不过把刑场变成了屠宰场,那件可怕的事情还得从头做起。他们心里产生了突如其来的恐惧,垂下枪口,无可奈何地听着军官们愤怒的斥骂,用呆滞的目光惊慌地望着那个他们开枪射击但却没有打死的人。
总督冲着他们的脸晃着拳头,穷凶极恶地吼叫着,命令他们站好位置,端起枪赶快把事情了结掉。他和士兵们一样完全丧失了勇气,不敢用眼睛看那个傲然屹立,不肯倒下去的可怕的人。当牛虻跟他说话时,他被那讥笑声吓得抖作一团。
“上校,今天早晨你带来的这支行刑队不称职!让我试试,看我能不能让他们射得准一些。注意啦。兄弟们!把枪口抬高些,那位兄弟朝左边瞄瞄。老天呀,伙计,你手里拿的是枪,不是炒锅!都瞄准了吧?请注意!预备——瞄准——”
“射击!”上校抢先一步,发出了开枪的命令。要是让犯人自己发口令枪毙自己,那岂不是太不像话啦。
又是乱糟糟、缺乏秩序的几声枪响,接着行刑队便乱了队形,全都瑟瑟发抖,睁大迷茫的眼睛望着前方。其中有的士兵就没开枪,而是把枪扔到一旁,蹲在地上嘴里痛苦地低声念叨着:“我办不到——我办不到!”
硝烟慢慢散了,飘浮到空中与晨曦融合在一起。他们看见牛虻倒了下去,但也看到他仍然没有死。起初那一瞬间,官兵们全都石像一般站在那里,看着那团可怕的东西在地上扭动和挣扎;后来,医生和上校都大叫一声冲上前去,因为牛虻一只膝盖着地吃力地跪起身子,而且仍冲着士兵大笑。
“又没打中!再……试一次,弟兄们!看看你们能不能……”
他突然一摇晃,歪倒在了草地上。
“他死了吗?”上校小声问。
医生跪下来,用手摸摸那血糊糊的衬衫,然后轻声回答:
“我想是死啦——谢天谢地!”
“谢天谢地,”上校也说道,“终于死了!”
他的侄子这时碰了碰他的胳膊。
“叔叔!红衣主教来啦!他在大门口,想进来。”
“什么?不能让他进来——我不允许。卫兵是干什么吃的?主教大人……”
大门开了又关上,蒙太尼里已经站在了院子里,用充满恐惧的目光呆呆地望着眼前的情景。
“主教大人!必须请你原谅——这场景不适合你看!死刑刚刚执行完,尸体还没有……”
“我来就是要看看他,”蒙太尼里说。总督这时才发现他的声音和神情都像是一个梦游的病人。
“啊,我的上帝!”一个士兵突然喊叫了起来。总督急忙回头望去。天哪……
草地上的那团血肉模糊的躯体又一次开始挣扎和呻吟。医生慌忙蹲下身子,把他的头抬起放在自己的膝上。
“快些!”他不顾一切地大声喊叫,“你们这些野蛮人,快点儿吧!看在上帝的分上,让这一切结束吧!实在让人受不了啦!”
大股的鲜血喷射在他的手上,他怀里抱的那个肉体痉挛着,使他从头到脚也抖动了起来。当他疯狂地四处张望求援时,牧师隔着他的肩头伏下身,把一个十字架放到了那个垂死的人的唇边。
“以圣父和圣子的名义……”
牛虻靠着医生的膝盖支起身子,圆睁双眼,直视着十字架。
在一片凝固了的沉寂之中,他慢慢抬起被打断了的右手,将那个偶像推到了一旁。耶稣的面孔被抹上了鲜红的血迹。
“神父……这下你的……上帝……该满意了吧?”
他的头一歪,落到了医生的胳膊上。
“主教大人!”
由于红衣主教仍未从恍惚的状态中清醒过来,菲拉里上校又喊了一声,这次声音更大了。
“主教大人!”
蒙太尼里抬起了头。
“他死了。”
“已经完全死啦,主教大人。你离开这儿吧!这场景怪吓人的。”
“他死了。”蒙太尼里又重复了一遍,又看了看死者的脸,“我摸了摸他,他已经死了。”
“一个人身上挨了十几枪,还会怎么样呢?”那位中尉轻蔑地嘀咕道。医生悄声回答说:“他看见血,大概吓糊涂了。”
总督用手紧紧拉住了蒙太尼里的胳膊。
“主教大人,你还是不要再看他了。能让牧师送你回家吗?”
“是的——我这就走。”
蒙太尼里慢慢扭过头,离开那血淋淋的地方,牧师和卫队长跟在后边。在大门旁他停下来,精神恍惚、目光呆滞,诧异地又回头望了望。
“他死了。”
几小时之后,麦康尼来到山坡上的一间茅屋里告诉马丁尼,说他已经没有必要捐躯了。
第二次营救工作此时已全部就绪,因为这一次的方案比上一次简单得多。根据他们的安排,第二天早晨圣体节的游行队伍路过丘陵上的要塞时,马丁尼将冲出人群,从怀里拔枪向总督的脸开火。趁随之而来的大乱之际,二十位荷枪者会蜂拥攻破大门,闯入塔楼,把钥匙抢到手,然后进囚室把犯人背走,遇到挡道的就打死或击退他们。出了大门,他们将边战边退,掩护由一群骑着马、全副武装的走私贩子组成的第二梯队把牛虻送进山里的安全隐蔽地。在这个小团体里,自有一个人对此项计划一无所知,那就是詹玛。马丁尼特别要求过要对她保密。“她会很快为此事担忧死的。”他解释说。
当麦康尼走进花园大门时,马丁尼推开玻璃门,来到游廊里迎住他。
“有消息吗,麦康尼?你说说!”
麦康尼把宽边草帽向后推了推。
二人在游廊里坐下,谁都没有言语。一看见帽檐下的那副面孔,马丁尼就什么都明白了。
“什么时候的事情?”隔了老半晌,他才问道。那声音连他自己听起来都觉得异常呆钝、乏力。
“今天早晨日出时分,这是卫队长告诉我的。他在场目睹了一切。”
马丁尼垂下头,轻轻弹开衣袖上的一根散线头。
空,一切皆空;这也化成了一堆泡影。他原本可以在明天捐献出生命。现在,他一心向往的境界消失了,那宛若金色晚霞般梦幻里的仙境消逝于黑暗来临之际。他又得回到那个平平常常的世界里——那里有格拉西尼和盖利,有写密码和印小册子的事务,有党内同志的争论,有奥地利暗探乏味的阴谋;那种旧模式的单调的革命工作叫人心里感到厌倦。他的内心深处有一大片空荡荡的地方,如今牛虻一死,就再没有任何事情任何人可以充实那儿了。
他听到有人在问他问题,便抬起头来,同时感到纳闷,不知现在还有什么事情值得一谈。
“你说什么?”
“我说你应该把这消息告诉她。”
生活,还有对生活的种种恐惧,又重新反映在了马丁尼的脸上。
“我怎么对她开口呢?”他嚷嚷起来,“还不如让我去杀了她呢。啊!我怎么能开口,怎么能对她讲!”
他双手遮住眼睛。接着,他虽然没看见,却感到身旁的麦康尼吓了一跳,于是便抬起头来。詹玛正站立在门口。
“你听到了吗,西萨尔?”她说,“一切都完了。他们已经枪决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