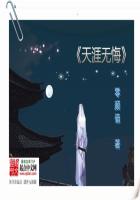牛虻的病体恢复得很快。第二个星期的一天下午,里卡多发现他穿着一件土耳其式睡衣躺在沙发上跟马丁尼和盖利闲聊。他甚至说要下楼走走,里卡多听了仅仅付之一笑,问他想不想先穿越峡谷去非索尔旅游一趟。
“你可以拜访格拉西尼夫妇换换心情,”里卡多又挖苦地说,“那位贵妇人见到你一定会很高兴,尤其是现在你脸色苍白,显得很有意思。”
牛虻把双手握在一起,摆了个悲剧性的姿势。
“哎呀!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她会把我当作意大利的一位义士,跟我大谈爱国主义。我应该假戏真做,告诉她我在地牢里被大卸八块,后又东拼西凑在了一起。她一定很想知道我在那个过程中有什么样的感受。里卡多,你认为她不会相信?我可以拿我的印第安匕首跟你医疗室里的那瓶绦虫打赌,她肯定会对我编造的弥天大谎信以为真。我的赌注是很大方的,你最好接受吧。”
“谢谢,我不像你那样喜欢凶器。”
“哦,绦虫和匕首一样凶残,随时能害死人,而且远不如匕首漂亮。”
“但很不凑巧,我亲爱的朋友,我不想要匕首,只想要绦虫。马丁尼,我得赶快走了。你负责管理这个任性的病人吗?”
“我只负责到三点钟。我和盖利到时候要去圣米涅多,波拉夫人将守在这里,等我回来接替她。”
“波拉夫人!”牛虻以一种惶恐的语气念叨道,“喂,马丁尼,这绝对不行!绝不能让一位夫人为我以及我的疾病牵肠挂肚。再说,让她坐哪里呢?她绝不愿意到这屋里来。”
“你是从什么时候穷讲究起礼节了?”里卡多大笑着问,“老伙计,波拉夫人是我们全体的护士长。自从穿短裙的时候起,她就开始照顾生病的人啦,而且比我所认识的任何一个护士都干得出色。还说她不愿进你的房间呢!啧,你要是指格拉西尼的那个女人还可以!马丁尼,如果是波拉夫人啦,我就不用留处方了。哎呀,已经两点半啦,我得走了!”
“喂,里瓦莱兹,在她来之前,把你的药吃下去。”盖利端着一只药杯走近沙发说。
“又是该死的药!”牛虻已到达康复期的阶段,正是让忠实的护士头痛的时候。“我已经不痛了,为什么还要让我服这种可怕的东西?”
“只因为我不愿让你旧病复发。波拉夫人来后,你要是发作起来,她就得给你服鸦片,这绝对不合你的心意。”
“我的好……好先生呀,疼痛要发作,是阻挡不住的;它又不是牙……牙痛,能用你的烂药水吓退。这种药水治我的病,宛若用玩具水枪救火。不过,我想你是非得达到目的不可。”
他用左手接过药杯。盖利一看见那些可怕的疤痕,又想起了以前的话题。
“顺便提一下,”盖利说道,“你怎么落下这许多疤?是在战场上吧?”
“喂,我不是告诉过你,那是在秘密地牢里发生的事情……”
“是啊,可那套故事适合于格拉西尼夫人听。说真的,这些伤大概是在跟巴西人交战时落下的吧?”
“不错,那时负了些伤,后来在荒蛮区域狩猎,又干过这样或那样的事情,伤疤就多了。”
“啊,对啦,你指的是科学探险途中发生的事情。你可以扣上你的衬衣,我的话问完啦。看来,你在那地方有过一段激动人心的经历呀。”
“哦,当然喽,生活在荒蛮的国度里,冒险是在所难免的。”牛虻轻描淡写地说,“而且不见得每次冒险都让人感到愉快。”
“话又说回来,我还是不明白你怎么落下这许多疤痕,除非是跟野兽恶斗过——就拿你左臂上的一片疤痕为例吧。”
“哦,那是在打美洲狮的时候落下的。是这样的,我当时开了枪……”
有人敲响了门。
“屋里不乱吧,马丁尼?不乱?那你把门打开。这真是太让你费心啦,夫人。请原谅,我就不起来了。”
“你当然不该起来,我来这儿又不是做客。西萨尔,我稍微来早了点儿。我想你们也许急着走呢。”
“我可以再待一刻钟。请允许我把你的外套放到另一个房间去。是否把篮子也提过去?”
“当心点儿,里面有新鲜鸡蛋,是卡蒂今天早晨从奥列佛多山弄来的。里瓦莱兹先生,这几朵圣诞玫瑰是送给你的。我知道你喜欢鲜花。”
她在桌旁坐下来修剪花茎,把花插进一只花瓶里。
“喂,里瓦莱兹,”盖利说,“把你刚刚开了个头的那个打美洲狮的故事给我们讲完。”
“啊,好呀!夫人,盖利正在问我在美洲的那段生活;我在告诉他,我的左臂是怎样弄得伤痕累累。事情发生在秘鲁。当时我们涉过一条河追猎一只美洲狮,我冲着那野兽开了一枪,可是却哑了火,原来弹药被水浸湿了。美洲狮自然没有等着我把故障排除,结果我就负了伤。”
“那一定是段妙趣横生的经历。”
“啊,还不赖!有痛苦当然就会有欢乐。不过,总体来说,那是一种灿烂的生活。就拿抓大毒蛇为例……”
他喋喋不休地把奇闻趣事一桩桩道来,忽而讲阿根廷战争、巴西探险以及狩猎中的宴席,忽而又讲怎样跟野人或猛兽遭遇。盖利就像小孩子听童话故事一样兴致勃勃不时还打断他的讲述,提些问题。他具有那不勒斯人的那种易受感染的天性,喜欢一切动人心魄的东西。詹玛从篮子里取出活来,一边低头忙于编织,一边默默地听着。马丁尼眉头紧皱,烦躁不安。他觉得牛虻那样夸夸其谈地讲述奇闻趣事,有点儿恬不知耻。他上个星期目睹了牛虻是怎样以惊人的毅力忍受着肉体上的痛苦,尽管由不得对他肃然起敬,可他打心眼里不喜欢牛虻以及他的一举一动和为人处世。
“那一定是一种辉煌的生活!”盖利带着羡慕的心情,天真地感叹道,“真不明白你怎么舍得离开巴西。有了那样的经历,再到别的国家去,一定觉得平淡乏味!”
“我认为,在秘鲁和厄瓜多尔的那段时光是最幸福的。”牛虻说,“那儿的确是山清水秀的地方。当然,天气是非常热的,尤其是厄瓜多尔的沿岸地区,让人有点儿打熬不住;可那儿的风景之秀丽,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我认为,”盖利说,“野蛮国度里的那种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比任何景色都更令我向往。在那里,一定能感受到自身的价值和人性的尊严,可是在我们拥挤的城镇里却永远也感受不到。”
“是啊,”牛虻回答道,“那是……”
詹玛把目光从编织物上抬起,望了他一眼。他霍然飞红了脸,打住了话头。接着便是短时间的沉默。
“该不是又犯病了吧?”盖利关切地问。
“啊,不是那回事,多亏你给我吃了我曾诅……诅咒过的止……止痛药。马丁尼,你是不是该出发啦?”
“是的,走吧,盖利,不然会迟到的。”
詹玛随在他们俩后边出了房间,不大一会儿端来一碗牛奶冲鸡蛋。
“请你把这吃下去!”她以温和的命令语气说,然后又重新坐下来做活计。牛虻顺从地按她的吩咐做了。
足足有半个小时,二人谁都没话说。后来,牛虻以非常低的声音说:
“波拉夫人!”
詹玛抬头望去。牛虻正在用手扯毛毯上的饰穗,眼睛低低垂着。
“你不相信我刚才讲的是实话。”他说道。
“我丝毫不怀疑你在编造谎言。”詹玛平静地说。
“一点儿不错,我一直在扯谎。”
“你是指打仗的事吗?”
“指所有的一切。我压根儿就没参加过那次战争;至于探险的经历,当然我的确冒过几次险,那些故事多半是真实的,但那并不是我负伤的原因。你既然看穿了我的一个谎言,我索性把其他的也招供出来。”
“扯那么多的谎,你就不觉得太浪费精力了吗?”她问,“依我看,不值得那样做。”
“有什么办法呢?你知道,你们英国有句俗话:‘不提问题,就听不到谎话。’我并不喜欢哄人,可人家问我怎么变成了残废,我总得回答呀。在讲述原因时,我索性编造出一些动听的情节来。你也看到了盖利是多么的高兴。”
“你宁愿取悦盖利,也不愿以实情相告?”
“讲实情!”牛虻抬起头来,手里握着已经撕下的毛毯饰穗,“你让我对那些人讲实情?我宁愿先把我的舌头割掉!”随后,他又显得有些窘迫和难为情,慌忙说道:“我从未给任何人讲过实情;不过,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讲给你听。”
詹玛默默地放下了手里的活。这个冷酷、神秘、讨人厌的男人,突然要对自己不太了解而且不大喜欢的一个女人吐露心中的秘密,这在她看来着实可悲可叹。
随之而至的是长时间的沉默,这使她抬起了头来。只见他把左胳膊支在旁边的桌子上,用那只伤残的手遮住眼睛。她注意到他的手指神经质地绷得紧紧的,手腕上的疤痕一跳一跳。她走上前,轻轻唤了声他的名字。他猛然吃了一惊,把头抬了起来。
“我忘……忘了……”他结巴着道歉说,“我正……正要给你讲……”
“是讲导致你残废的事故或别的什么原因。不过,如果会给你带来烦恼的话……”
“事故?啊,对,我负了重伤!不过,那不是一次事故,而是被一根拨火棍打的。”
她诧异地呆呆望着他。他用一只发抖的手把头发朝后捋了捋,笑吟吟地抬头瞧着她。
“你不愿坐下来吗?请你把椅子朝跟前挪挪。很遗憾,我不能为你效力。说真的,现在想起来,当时要是里卡多为我治伤,他一定会把我的伤势看作珍贵的宝库;他对破碎的骨头有着真正的外科医生所独具的爱好,而我觉得那一次我身上凡是能打碎的部件全都碎了——只除了我的脖子。”
“还有你的勇气,”詹玛轻声插话说,“也许你把勇气是列在不能打碎的东西里的。”
他摇了摇头。“不对,”他说道,“我的勇气是跟我身上别的部件一道胡乱修补起来的;当时,它被击得粉碎,和一只破碎的茶碗一样。最糟糕的正是这一点。啊,我刚才讲拨火棍的事哩。那是……让我想一想,那是大约十三年前在利马的时候。我曾对你说过,秘鲁是一个充满欢乐的国家,可是对于像我当时那样身无分文的人来说,就不那么美好啦。我去过阿根廷,后来又前往智利,大部分时间是在漂泊和忍饥挨饿中度过的。最后,我在一条运牲口的船上当帮手,从瓦尔帕莱索一路抵达了智利。在利马找不到工作,我就下码头碰运气——你知道,那些码头处于卡利欧海港。当然喽,所有的船港都有水手们聚会的乌七八糟的场所;过了一些时候,我被一家赌馆雇去当仆人。我得煮饭,在弹子台上计分,给水手们以及他们的女人端茶送酒,或做其他诸如此类的事情。那算不十分好的工作,但我很高兴,因为至少有饭吃,还可以看到人类的面孔和听到人类的说话声。你也许认为那不是什么优越之处,可我当时刚刚患过黄热病,曾一个人孤独地躺在一座凄凉的废弃草棚的外间屋里,那情景让我心有余悸。一天晚上,一位醉醺醺的印度水手在赌馆里寻衅闹事,因为他一上岸就把钱输了个精光,正没处撒气,老板命令我把他赶出去。当然,如果我不想丢掉饭碗,不想饿死,就得服从命令。可是,那个水手的力气是我的两倍——我那时还不满二十一岁,又患过热病,身体虚弱得跟猫一样。再说,他手里还拿着根拨火棍。”
他停顿了一会儿,偷眼瞧瞧詹玛,然后又继续讲述道:
“显而易见,他意在一下子结果了我。可是他的活干得有点儿粗糙,没有把我全部的部件都砸碎,使我得以苟延残喘。”
“哦,可是旁的人呢?他们就不能出面干涉吗?难道他们都怕一个印度水手不成?”
牛虻抬起头来,迸发出一阵大笑。
“旁的人?那些赌徒和赌馆里的人吗?唉,你不明白!我是他们的奴仆——他们的财产。他们自然要站在一边看热闹。在那儿,这种事情是惹人开心的快乐游戏。说来也的确让人开心,只要你自己没有充当游戏里的玩物就行。”
詹玛不寒而栗。
“那么,最后怎么样了呢?”
“这我就讲不出许多情节了。通常情况下,一个人在经历过那种事情之后,几天内是记不得什么的。碰巧附近的船上有个外科医生,人们大概发现我还没死,就把他请了来。他凑合着把我缝了起来——里卡多似乎认为他缝得非常糟糕,可这也许是同行间的妒忌吧。总之,待我清醒过来时,一位土著老妪出于基督徒的慈悲之心收留了我。听起来很离奇,是吧?她常常蜷缩在茅屋的角落里抽黑烟斗,一个劲儿朝地上吐痰,自顾自地哼歌。不过,她的心肠是蛮好的,说我尽可以安安静静地死去,没有人会打搅我。可我抵触情绪很强烈,做出了活下去的选择。挣扎着活下去是件非常难的事情,有时我觉得花那么大的力气着实得不偿失。不管怎么说,那位老妪的耐心是很惊人的;她留我在她的茅屋里躺着……有多长时间呢?……将近四个月;我时常像疯子一样说胡话,有时还似发怒的熊一般凶狠。我当时痛得死去活来,可我的脾气由于小时候过分娇生惯养被宠坏了。”
“后来呢?”
“哦,后来嘛……我挣扎起身,悄悄走掉了。不要以为我是体贴那个可怜的女人,不忍心接受她的恩惠,其实我早已麻木不仁了。我溜走,只是因为我再也无法忍受那个地方。你刚才还谈到我的勇气,你是没见我当时的那个样子!每天傍晚,约莫在黄昏时分,是我痛得最厉害的时候;下午,我独自一人躺在那里,观望着太阳渐渐西沉——啊,那是你无法理解的!如今我一看见日落,心里就感到不舒服!”
长时间的沉默。
“哦,后来我满世界乱跑,想看看是否能找个活干——再在利马待下去,我会被逼疯的。我一直流浪到库斯科市,而那里……真的,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把这些前尘旧事讲给你听;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甚至让你取笑都没劲儿。”
詹玛抬起头,用深沉和恳切的目光望着他。
“请别这样讲话。”她说。
他咬紧嘴唇,又扯下了一条毛毯饰穗。
“还要我说下去吗?”他隔了一会儿问道。
“如果……如果你愿意的话。恐怕回忆过去对你是件可怕的事情。”
“你以为我闭口不谈就是忘记了吗?那样更糟。不过,你不要以为我久久难忘的是事情本身。其实,我忘不了的是我曾丧失了自控力。”
“我……我觉得,我不太明白你的话。”
“我是说,我的勇气曾经到了尽头,最后我发现自己竟然是个懦夫。”
“每个人的忍受力自然都是有限度的。”
“是的。一个人一旦达到过那种程度,说不定还会故态复萌。”
“你是否能告诉我,”她犹豫地问,“你怎么会在二十岁的时候独自一人流落到那里?”
“经过非常简单:在这个古老的国家里,我原先过着优裕的生活,后来便离家出逃了。”
“为什么?”
他又爆发出一阵急促和刺耳的笑声。
“为什么?大概是因为我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初生牛犊吧。我在一个极度豪华奢侈的家庭里长大,备受娇惯宠爱,于是乎我就认为这个世界是用粉红色的棉絮和糖衣杏仁做成的。后来有一天,我发现一个我所信赖的人欺骗了我。喂,你怎么这样吃惊!怎么回事?”
“没什么。请你继续讲吧。”
“我发现自己中了别人的计,相信了一个谎言——当然,这是很平常的事情。可是正如我说过的,我那时太年轻和自负,恨不得让撒谎的人下地狱。于是我逃离了家,一头扎入南美逐浪沉浮,口袋里没有一文钱,不会讲一句西班牙语,除了一双白嫩的手和爱花钱的习惯,再无一点儿谋生的本钱。结果,我自然而然栽进了真正的地狱,矫正了我对假地狱的想象。那一栽可是栽得狠啊——整整熬了五年,杜普雷探险队来后,才把我救了出来。”
“五年!啊,太可怕啦!你没有朋友吗?”
“哼,朋友!”他说着,恶狠狠冲她转过身来,“我从来就没有过一个朋友!”
随即,他似乎对自己的激烈态度有点儿难为情,急忙又说道:
“你可不要把我的话太当真。我大概把情况极度夸张了。其实,头一年半的情况并非太糟。我年轻力壮,日子过得还是挺好的,一直到那个印度水手在我身上留下印记为止。自那以后,我就找不到工作了。说来也神奇,拨火棍只要挥舞得当,就会变成威力无比的武器;没有人愿意雇用一个瘸子。”
“你都干些什么活?”
“找到什么活就干什么。有一段时间,我替甘蔗园里的奴隶干杂活。为他们搬搬运运或什么的。但好景不长,那些工头一见到我就把我撵开。我的腿瘸得厉害,走路走不快,而且搬不动重物。那个时候,我的炎症(或者叫别的什么讨厌的病名)经常地发作。”
“过了些时候,我跑到银矿那儿找活干,但一无所获。那些经理们一听说我想当工人,便笑破了肚皮;而矿工们则对我拳打脚踢。”
“怎么会那样呢?”
“哦,大概是出于人的天性,他们欺我只能用一只手还击。最后,我忍无可忍,就踏上了流浪的道路,漫无目的地四处漂泊,希望能找点儿事做。”
“流浪?拖着那条瘸腿?”
牛虻抬起头,突然可怜巴巴地憋住了呼吸。
“我那时还饿着肚子。”他说。
她把头稍稍偏转开,用一只手托住下巴。他沉默了片刻,随后又开了口,但声音愈压愈低。
“唉,我在路上走啊走啊,直到差点儿发疯,却什么结果也没有。进入厄瓜多尔境内,那儿的情况更是恶劣。有时我为人家补锅——我是一个挺不错的补锅匠;有时为别人跑跑腿或清理猪圈;有时我则……唉,我也不知道都干了些什么。后来有一天……”
那只放在桌子上的纤巧、棕色的手突然紧紧攥了起来,詹玛抬起头关切地瞥了他一眼。他的脸侧对着她,她可以看见他的太阳穴上有一根血管在急促地乱跳,似铁锤在击打。她俯身向前,把一只手温柔地搭在他的胳膊上。
“不用再继续讲了,可怕的往事不堪回首。”
牛虻迟疑地盯着她的手,摇摇头,便又从容地讲了下去:
“后来有一天,我碰上了一个跑江湖的杂耍班子。你该记得那天晚上看的杂耍——对,就是那种东西,只不过更粗俗些、更下流些。而且,里面当然会有斗牛的节目。杂耍班子在路边搭起帐篷准备过夜;我到他们的帐篷前行乞。当时天气很热,我又饿得半死,所以……我在帐篷门口昏过去了。那个时候,我就像喜欢把胸脯束得紧紧的寄宿学校的女学生一样,有一种突然昏厥的习惯。他们把我抬进帐篷,给我喝白兰地和吃东西,等等。后来……第二天早晨,他们要我留下……”
又一阵停顿。
“他们想要一个驼背,或者一个畸形人,供孩子们抛橘子皮、香蕉皮或什么的,以博一笑……那天晚上,你看见那小丑了……我担任了两年那样的角色。
“于是,我就着手学艺。我的身体还不够畸形,但他们弥补了不足,为我安上一个假驼背,还最大限度利用这只脚和这条胳膊……好在当地人并不挑剔,很容易满足,只要有个活人供他们折磨就行了……小丑的衣服也起了很大作用。
“唯一的困难就在于我常常生病,无法演出。有时经理发起脾气,在我旧病发作的情况下仍逼我上场;我觉得,观众最喜欢的就是这样的夜晚。记得有一次,我演到半截就痛昏了过去……待我清醒过来,观众已把我团团围住,又是嘲笑,又是喊叫,还用东西砸我……”
“别讲啦!我再也受不了啦!看在上帝的分上,你停下来吧!”
詹玛站起来,用双手捂住耳朵。牛虻住了嘴,抬头看见她眼里闪着晶莹的泪花。
“糟糕,我真是个十足的白痴!”他压低声音说。
她走开去,站在窗前向着外边眺望了一会儿。待她转回身来,牛虻正斜倚在桌上,用一只手遮住眼睛。他显然忘记了她的存在。于是,她一声不吭地在他身旁坐了下来。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她才慢慢说道: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他一动不动地说。
“你为什么没有结束掉自己的生命?”
他带着沉重的表情诧异地抬起了头。“没想到你会提这样的问题。”他说,“那我的工作怎么办?谁能为我完成呢?”
“你的工作——啊,我明白了!你刚才还声称自己是懦夫呢!既然你经历了那样的磨难,还矢志不渝,你就是我所遇到的最勇敢的人!”
他又遮住了眼睛,激情满怀地将她的手紧紧握住,一阵似乎永无止境的沉寂笼罩在他们周围。
突然,一阵飞泉鸣玉般的女高音从楼下的花园里传来,唱的是一首不含韵律的法国歌:
喂,皮埃罗!跳吧,皮埃罗!
跳一会儿吧,我可怜的让诺!
舞蹈和欢乐万岁,
我尽情享受美丽的青春!
如果我哭泣或我叹息,
如果我忧容满面——
先生,这只是给你开个玩笑。
哈!哈,哈,哈!
先生,这只是给你开个玩笑。
一听到歌声,牛虻立刻把手从詹玛那儿抽回来,轻轻呻吟一声,身子向后缩去。詹玛用双手抓住他的胳膊,紧紧按住,就像对待一个正在接受外科手术的病人一样。待歌声一落,花园里又传来一阵欢笑和鼓掌声;牛虻抬起头,那眼神就像是一只遭受折磨的野兽。
“不错,是绮达,”他慢吞吞地说,“那是她和她的军官朋友们。那天晚上,在里卡多未来之前,她就想进这房间。要是让她碰碰我,我一定会发疯的!”
“可她并不知道,”詹玛低声反驳道,“她也想不到,她会使你难过的。”
花园里又爆发出一阵笑声。詹玛起身打开了窗户。只见绮达头上风骚地缠着一条镶着金边的围巾,手中高举着一束紫罗兰,正站在花园小径上,而三个年轻的骑兵军官你争我抢,想把紫罗兰拿到手。
“莱尼小姐!”詹玛叫道。
绮达的脸沉了下来,像布了一层雨云。“夫人?”她转过身来,抬起眼睛说道,显出一副轻蔑的样子。
“能让你的朋友说话小声点儿吗?里瓦莱兹先生身体很不舒服。”
那吉卜赛女郎扔掉了手中的紫罗兰花束。“都滚吧!”她厉声对那几位惊慌失措的军官吆喝道,“你们让我心烦,先生们!”
她慢步出门到了街上。詹玛将窗户关好。
“他们走啦。”她冲着牛虻说。
“谢谢。这样麻烦你,让我……我很过意不去。”
“算不了麻烦。”她的声音有些迟疑,立刻就被他听出来了。
“但是……”他说,“你的话没说完,夫人。你的心里还有个‘但是’没有说出口。”
“如果你能看透人的心,那你可不能为自己看到的东西感到生气。事情当然与我无关,可我不明白……”
“不明白我为什么嫌恶莱尼小姐?只有当……”
“不,我不明白你既然嫌恶她,为什么还要跟她同居。我觉得这是在侮辱她,侮辱一个女人和……”
“一个女人!”他刺耳地笑了起来,“那就是你所谓的女人?夫人,纯粹是开玩笑!”
“这不公平!”她说,“你没有权利当着别人的面这样说她,尤其是当着另一个女人的面!”牛虻把脸扭开,睁大眼睛躺在那里,望着窗外西沉的太阳。詹玛放下百叶窗,关上护窗板,不让他观看落日,然后在另一扇窗前坐下,又拿起了编织活。
“你想把灯点亮吗?”她隔了一会儿问道。
他摇了摇头。
当天色黑得看不清东西的时候,詹玛卷起编织物放进篮子里。她叠着双手坐了一会儿,默默地观察着牛虻纹丝不动的身影。朦胧的暮色罩在他的脸上,似乎减弱了那种冷酷、嘲讽和自负的神情,却加深了他嘴角处悲哀的皱纹。詹玛心潮起伏,浮想联翩,她父亲为纪念亚瑟竖起的一尊石头十字架形象逼真地出现在她的回忆里,那上面刻着一行铭文:
惊涛骇浪淹没了我。
在鸦雀无声的静寂中,一个小时过去了。最后,她起身轻手轻脚出了房间,回来时端着一盏灯。她迟疑了片刻,以为牛虻已经睡着。当灯光落在他的脸上时,他却转过了身来。
“我给你煮了杯咖啡。”她把灯放下说。
“先搁一会儿吧。”他说,“是否请你到这儿来一下?”
他握住了她的双手。
“我一直在思考问题。”他说,“你是完全正确的,我把自己的生活搅得乱七八糟。可你别忘了,一个男人并非每天都能遇见值得……爱恋的女人;我曾潦倒困顿,害怕……”
“害怕什么?”
“害怕黑暗。有时我不敢单独过夜,必须有样活着的、实在的东西在我身旁。我怕外界的黑暗,那里有……不,不!并非如此,那只是微不足道的地狱——我真正怕的是内心的黑暗,那里没有哭泣声或咬牙的声音,只有沉寂……沉寂……”
他的眼睛发直。她仍一动不动,几乎屏住了呼吸,直至他又开始讲话。
“这一切对你都很神秘,是吗?你不明白——多亏了你不明白。我的意思是说,我如果孤身一人生活,很可能会发疯……如果可以的话,不要把我想得太坏。我根本不是你也许把我想象成的那种邪恶之徒。”
“我不能替你做出判断,”她答道,“因为我没受过你那样的磨难。不过……我也陷入过困境,只不过形式不同罢了。我认为……我敢肯定……如果你是出于对某样东西的恐惧,去干一件的确很残酷、不公道或小肚鸡肠的事情,那你过后一定会懊悔的。还有——如果你在这件事上栽了跟头,我要是你,就会以为全盘皆输,该诅咒上天和死去。”
他仍旧握着她的双手。
“请你告诉我!”他无比温柔地说,“你这一生是否干过实实在在残酷的事情?”
她没有回答,可是却垂下脑袋,两大滴泪水落在了他手上。
“告诉我!”他激动地低语道,把她的手握得更紧了,“告诉我!我已经把我心里的痛苦全都倒了出来。”
“干过……干过一次……那是在很久以前。他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人。”
紧握着她的手的那两只手剧烈地抖动起来,然而却没有松开。
“他是一位同志,”她继续说道,“我听信了一种诽谤他的谣言——那是警方编造的司空见惯的谣言。我把他当作叛徒,掴了他一耳光。他走掉后就投水自尽了。事隔两天之后,我发现他完全是无辜的。这段回忆也许比你的回忆更为痛苦。如果做过的事情可以取消,我情愿砍掉我的右手。”
他的眼里闪现出一种她以前从未见过的稍纵即逝的危险神情。他猛然偷偷地低下头,吻了她的那只手。
她向后缩去,一脸惊慌的神情。“别这样!”她可怜地嚷道,“请你以后不要再这样了!你真让我伤心!”
“你以为你就没有伤过那个你害死的人的心吗?”
“我……我害死的人……啊,西萨尔在大门口,他终于来啦!我……得走啦!”
马丁尼进屋时,发现牛虻独自一人躺在那儿,旁边放着一杯动也未动过的咖啡;牛虻显出一副倦怠、无精打采的样子,嘴里自顾骂着脏话,仿佛他尝了咖啡,一点儿也不满意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