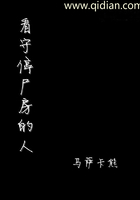将近日暮时分,湖阳公主一行人才匆匆赶回宫中,倘使再晚片刻,四角宫门便要换成夜防巡逻。湖阳公主自知今日出去时间太长,因此赶紧换了衣衫,心里已经做好被训斥的准备,打起精神赶到弘乐堂给太后请安。
双痕从内殿迎了出来,低声埋怨道:“公主,怎么这会儿才回来?一大早的就不见人影儿,还敢磨蹭到这么晚,仔细太后娘娘说你。”
对于这位陪伴母亲数十年的侍女,湖阳公主自小都是以长辈之礼相待,此时自知理亏,悄声道:“双痕姑姑,母后现在心情可好?等下若是母后说我,双痕姑姑可要帮衬着一些。”
“哎……”双痕笑着叹气,“行了,快进去罢。”
湖阳公主情知躲不过,只得忐忑不安跟随双痕来到内殿。果不其然,太后面色平静撵退了殿内宫人,然后让双痕去添香,淡声问道:“棠儿,你可知现在是什么时辰?”
湖阳公主忙道:“母后你别生气,女儿下午跟月儿在街上看热闹,一时玩得高兴多逛了会儿,所以误了时辰回来。”
“哦……”太后不动声色微笑,闲闲拨弄着手上的粉瓷茶盅,抿了一口,然后才漫不经心问道:“不知是什么样的热闹,这般好看?”
湖阳公主自是回答不出,支支吾吾,“母后——”
大殿内的气氛颇为凝固,宫人们更是大气也不敢出一声。此时入冬天气寒凉,双痕搬了一个火盆过来烤着,正要上前给公主解围,便听院外小太监唱道:“启禀太后娘娘,内阁侍读杜淳前来请安。”
太后只好打住话头,淡声道:“宣他进来。”
小宫女打起门口的翡翠珠帘,一名举止斯文的锦袍少年躬身进来,瞧见湖阳公主顿时眼中一亮,上前行礼道:“太后娘娘万福金安,给公主请安。”
“起来罢。”太后微微点头,问道:“杜淳,皇上在忙什么呢?”
“回太后娘娘的话。”杜淳微微躬身,举手投足间颇为儒雅飘逸,“皇上刚跟大臣们议了秋粮入库一事,说是今秋丰收,更应该多囤些上好的粮食存着,以备往后有不时之需。刚才大臣们领旨下去写折子,皇上还在醉心斋歇着,微臣准备出宫回家,正好过来给太后请安。”
太后淡笑道:“嗯,难得你如此有孝心。”
“太后瞧瞧——”双痕指了杜淳,岔开话题笑道:“这杜淳,像不像他父亲杜丞相年轻的时候?呵……,生得好模样儿、又有才学,去年一举就中了新科榜眼,听说京里有不少姑娘思慕着呢。”
“没有、没有。”杜淳慌张摆手,赶紧去瞧湖阳公主的脸色,“哪、哪有什么不少姑娘思慕?都是些无聊之人在随口瞎说,不能当真……”
“呵,怎么着起急来?”太后忍俊不禁笑出声,容色光彩照人,“双痕这也是在夸你啊,有也不是什么坏事,没有就没有罢。”
“像他这样,谁家姑娘会傻得看上他?”湖阳公主轻声窃笑,朝杜淳道:“双痕姑姑不过是顺口一说,你还拿着当真了。”
杜淳连连点头,“是是,公主说的很对。”
“你少挤兑别人。”太后侧首,看着湖阳公主道:“刚才还没说完,把你看的热闹稀奇说说,让母后也听听,大伙儿都跟着你乐一乐。”
“娘娘,奴婢忽然想起一个笑话。”双痕赶紧继续打岔,“就是那年腊月,皇上和公主把杜淳忘在漱玉轩,杜夫人急得快上吊的那回,娘娘可还记得?”
太后闻言一笑,“怎么不记得?还不都是棠儿惹出来的事。”
那年桓帝和湖阳公主都才八、九岁,当时杜淳是皇子侍读,年纪也差不多,平时总在一起读书玩耍。有天几个孩子偷偷跑去漱玉轩玩儿,回来时不想绕路,于是便商量着翻花窗,湖阳公主女孩儿力气小,费了半天也是翻不出去。杜淳见状,便折身翻回来蹲在地上,给湖阳公主做了个人肉墩儿,这才把她送了过去。
杜淳被地上瓦片划伤了手,又不愿让公主知道,只说自己肚子疼,让桓帝和公主先回宫去,自己歇会儿再走。谁知道桓帝兄妹玩得过头,都是有些疲惫,早忘了还丢下一个人,两人回去便倒头呼呼大睡了一夜。
杜淳晚上没有回家,宫人也不知道他去了哪儿,杜夫人急得差点没去上吊,杜府上下闹得人仰马翻。直到第二天清晨,湖阳公主猛地想起昨日落下了杜淳,猜测人可能还在漱玉轩,这才派人把他找回来。寒冬腊月,杜淳在风中哆哆嗦嗦冷了一夜,染上风寒之疾,结果发了三天三夜的高烧。
双痕提及旧事,笑道:“还好,没把我们榜眼的脑子烧坏。”
杜淳回道:“公主没事便好。”
“不就是踩了你一回么,总是当件功劳来说。”湖阳公主不领他的情,“那次因为害你后来生了病,我和皇帝哥哥都被母后训了,关着抄好几天的书,也不比你躺在床上好多少。”
“是。”杜淳并不生气,顺着她的话笑道:“都是微臣连累了公主。”
“娘娘——”双痕瞅了瞅太后的脸色,笑着劝道:“公主从小就有些淘气,不过是年轻贪玩、不懂事,现在心里已经知道错了,下次再也不会。”
“你还敢有下次?”太后睨了湖阳公主一眼,“皇室宗亲那么多的公主、郡主,就数你最不像话,都是母后平时太过娇宠你,没有一点规矩礼数!”
双痕假意叹道:“这般淘气,都快赶上乐楹公主了。”
“怎么会,我哪能赶得上小姑姑?”湖阳公主知她是在转移话题,趁势依偎到太后身边撒娇,“母后,当年乐楹姑姑追着小舅舅去了青州,比起姑姑那会儿,女儿可算听话的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