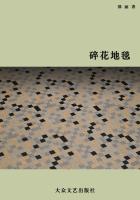游家驹得意地看着她们笑道:“二位小姐这就不了解总司令的为人了。总司令是最注重感情和义气的:凡是乡亲、学生、共过患难的人,他都要提拔重用,永远也不会忘记;尤其是对同乡同族,他更另眼相待。这两年从家乡来找他或是写信来求他的人,没有一个不是高高兴兴达到目的的。有些从外地写信要求寄旅费,总司令也十分慷慨大方,立刻批条子寄去。这一方面是让更多的人来广州投奔革命;一方面也是因为家乡的人可靠,到危难的时候也能扶保他,不会从后面打黑枪。俗话说:‘上阵还要亲兄弟,打仗全靠父子兵嘛。’你们只要到总司令部和校长办公厅去看一看,碰到的人差不多都是浙江口音,简直就像到了浙江同乡会一样了。你们数一数:总司令的秘书长邵力子,浙江人;秘书处长马文车,浙江人;私人秘书兼机要科长陈立夫,浙江人;他的哥哥陈果夫现在又是代理中央组织部长;军需处长俞飞鹏,是总司令的小同乡,浙江奉化人;我们的顶头上司,副官处长钱大钧,也是浙江人。至于下面的官长,浙江人就更多了。”
沈大戈听了,吐吐舌头,又不禁笑道:“只要是总司令的同乡就能做官,那要是他的亲戚本家,又该怎么安排呢?”
“当然更受重用了!”游家驹认真地说道,“不过,要是从前得罪过总司令的,即便是亲戚本家,如今不但不能得到好处,他还要记恨你一辈子哩!你们大概都听说总司令在家乡有个元配夫人,姓毛,是奉化岩头人,总司令对他家里这位夫人就像对冤家一样呢!”
“那是为什么?”她们一齐问道。
游家驹为了炫耀自己了解总司令的底细,故意显得神秘地看着她们笑了笑道:“这样的事情你们不要拿到外面去说。总司令在家的时候,小名叫瑞元,因为头上长过几处痢痢,人们就都叫他瑞元癞头。他从小就是很顽皮的,喜欢参加乡里的各种活动;那时他们家乡每逢年节,一些爱凑热闹的年轻人就集合起来‘打龙灯’。龙灯打到哪里,哪里的人们就要给他们送钱、送鞭炮、送年糕之类的礼品。不送就不走,有些光棍无赖的性质,别人也就不大看得起他们。有一年总司令也参加‘打龙灯’,正好打到了他丈人的家里——岩头。丈人家本是知书识礼的,一听女婿瑞元也在打龙灯的人里头,立刻气得跑出去指着他大骂道:‘你这畜生,真是活现眼,败坏了祖宗的门楣,还不快给我滚回去?’……从这以后,总司令就记了他老丈人的仇,回溪山再也不踏丈人家的门,对他的元配夫人也没有一点好脸色了。”
沈大戈问:“听说总司令送到俄国上学的那个孩子,不就是元配夫人生的吗?”
游家驹点点头道:“那也是刚结婚那两年的事。后来总司令到外头谋生活,就连家也很少回去了。他至今也不喜欢那边的人。”
沈大戈替玉慧写好了信,就交给游家驹道:“你看看行不行?”
游家驹接过看了一遍,高兴地点头道:“很好,很好。剩下的事情都交给我,总司令有了回话,我就立刻来报告你们。”
游家驹兴冲冲地回去后,玉慧心里仍半信半疑,但又怀着期望。三天过去了,游家驹还没有露面,玉慧几乎要完全失望了,但到傍晚,游家驹兴冲冲地出现在她们面前,他的神情特别昂奋地说道:
“恭喜二位女士,大功告成了!这几天总司令特别忙,我好不容易才找到机会,把信呈给他。起先他只说交给秘书处长去办一下;后来听我介绍了几句慧同志的情况,他又重新看了一遍信,接着就连声点头说:好,好,这很好!马上就提起毛笔批了一张条子,让你立即到总司令部的随军剧团去。”
游家驹说着,拿出一个印着“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大信封递给她们。
信是写给随军剧团的负责人李元龙的。沈大戈接过信,急忙抽出信纸同姚玉慧一起看:那上面用毛笔很潦草地写着几行字,字体长而且瘦,就像是一些柴枝权权桠桠构成的。玉慧看着李元龙的名字,不禁感到惊讶地问:“李元龙不是‘中山舰事件’被抓起来了吗?怎么现在又去办随军剧团了呢?”
“前几天总司令又亲自下令把他放出来的。”游家驹道,“他是总司令的学生,总司令表示还照样相信地,让他担任总司令部的警卫团长,可他说什么也不肯再带兵,只想去做宣传工作。总司令也不好勉强他,就特准他成立一个剧团,随总司令部的政治部一起上前线。要不,慧同志怎能有这样巧的机会呢!”
沈大戈又不解地问:“那‘中山舰事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究竟是总司令神经过敏,还是共产党真的有阴谋?”
游家驹沉吟一下说道:“这件事也许永远是个千古之谜。我曾经问那天指挥队伍行动的范师长,他回答说:‘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是以校长的意思为意思,校长让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可是校长公开说:‘这件事我决不能统统讲出来,你们要了解事情的真相,只有等我死了以后看我的日记。’连校长和范师长都是这么说,还有什么别的人能搞得清楚呢?”
“好一个千古之谜!”沈大戈冷笑道,“一场‘中山舰事件’的‘误会’,你们总司令排挤了共产党,气走了汪精卫,自己又兼了组织部长和军事部长。再要出一个什么事件,只怕我们这些不是CP分子的人也该倒霉了!”
游家驹笑着解释道:“话不是这么说,总司令也有总司令的难处。你看前些时广东的局面,谁也不肯听总司令的,他要是不采取一点非常行动,谁能承认他的领袖地位?北伐的军事行动谁能统一指挥?这样做他也是迫不得已,是为了革命的一片苦心。他自己也再三向黄埔同学们发誓:‘我校长将来如果反革命,你们学生都可以来杀掉我!’他说这些话的时候,确实是很真诚的。”
“这些话只有你们孙文主义学会的人才相信!”沈大戈轻蔑地笑道,“他要是真当了反革命,只有他来杀别人,别人谁敢去杀他?怪不得有的人说:刘备的江山是哭出来的,你们总司令的江山是赌咒发誓赌出来的!”
“你这张嘴真厉害!”游家驹表示退让地笑道,“怪不得你的名字叫大戈,真是唇枪舌剑,我算是说不过你了。”
玉慧虽然也和沈大戈一样,对“中山舰事件”的突然发生和结束有些茫然不解,对总司令的时左时右的举动也感到有些惶惑,但此刻实在顾不得去多想这些,她只是为很快就能到北伐前线而格外激动,同时对游家驹的热情也充满了好感。她完全沉浸在喜出望外的激动心情里。她想象着湘粤道上的行军,想象着北伐战场的炮火,想象着同李剑和齐渊在前线的重逢,更急切地期望着这个时刻早早到来。
离别广州的日期终于临近了。在他们出发的前一天傍晚,游家驹和沈大戈包了一只珠江上的蛋户酒家,特地为玉慧壮别饯行。这种蛋户酒家,也是广州所特有的游览宴会的地方。蛋船有大有小,有的舱中可以摆一桌酒席,也有的可以摆两桌或三桌的。有的蛋船又名叫花艇,白天在江面上摆渡,晚上还可以住人。玉慧和李剑来到广州后,当他们第一次在傍晚来到长堤的珠江边一带散步时,就曾被这南国水上的美丽景色所迷恋,他们感到这明丽深湛的珠江比巴黎的塞纳河更使人亲近和神往;后来只要有闲暇,他们就总喜欢到这江边来度过南国之夜的美好时光。有时也乘坐这样的花艇在江面上游览,李剑的许多充满革命激情的诗章,就是在这些美好的时刻奔涌出来的。那些划艇的几乎都是妇女:有的是梳一条长长的大辫子的年轻姑娘;有的是身后用布兜背着一个孩子、挽着发髻的中年女人。她们都是那样健壮有力,身体的线条柔和而又坚韧,穿着墨色拷纱短衣裤,露出那紫铜色的两条胳膊和两条大腿,再加上她们那饱满的胸脯,和那棕色的椭圆脸上的一对大而深的黑色的眼睛,那是一幅多么动人的劳动妇女的肖像。玉慧可惜自己不是画家,她真想将她们的形象描绘下来,让那些在国外嘲笑中国只有东亚病夫和小脚女人的人们看看发生了革命变化的中国,妇女们都会成为这样健美有力。
今天他们乘坐的也是一只这样小巧玲珑的蛋艇。虽然是船上,但是一切设备都很齐全。船舱便是客厅,两旁有雕花的栏杆,中间摆着一张擦得发亮的油漆方桌,显得十分洁净。厨房在船的后部,各种山珍海味和精细的美点都可以从那里做出来。
因为游家驹听沈大戈说过,玉慧的性情十分清高,不喜欢同素不相识的人应酬,因此他也没有再邀请别人,席上只是他们三个。但点的菜却十分丰富,都是广州那些著名酒家里具有地方特色的名菜。比如什么鸡茸燕窝、五彩明虾、椰油咖喱鸡、荷包玉菜鸭、金鲤自鸽、红焖花菇、八宝酥蹄、潮州鱼丸等。点心则有粉皮蟹饺、凉冻粉羹、蜜饯金瓜、水晶酥饺、凉冻菠萝酪、粉皮水晶包。总之,琳琅满目,应有尽有,足够十来个人吃的。虽然玉慧再三要求他不必弄这么多的菜和点心,但游家驹为了表示自己的豪爽与阔绰,坚持着要船上的厨娘把所有拿手的名菜都做出来,他似乎恪守着这样一个信条:在女人的面前切不可小气,这是要取悦她们芳心的一个重要环节。
大约是这几天总司令部所属的许多机关都要陆续向前线出发,因此同他们一样,在珠江的蛋船酒家上举行饯别宴会的人也特别多。人少的就在一只船上,人多的还有用几条大船连在一起,摆着四、五桌以及六、七桌酒席的。那些船上都非常热闹:有的猜拳行令,大声谈笑;有的击鼓传花,把酒吟诗;有的带着留声机,播放着《葡萄仙子》之类的流行歌曲;也有的请了唱南曲的盲妹,聆听那莺声燕语缠绵婉转的粤曲。沿着长堤从白鹅潭到东山的这一带江面上,到处浮动着蛋船的红红绿绿的灯光;随着江上飘荡的和风,到处充满了热烈的欢歌笑语和觥筹交错的喧闹声。
看着这样的情景,玉慧的心中不觉很有些感慨:这时候,齐渊和李剑他们,不知在前线的什么地方?也许他们正同士兵们一起,在荒山野岭的草丛中露宿;也许正在艰难崎岖的行军路上,经受着饥渴和炎热的折磨?想到这些,玉慧看着那满桌的山珍海味,就感到实在有些难以下咽。她对于周围那些蛋船酒家上猜拳行令、欢歌笑语的喧闹声,也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反感:那些真正为着北伐革命的事业,在前线同军阀队伍奋勇搏斗、流血拼命的士兵们,喝着路边的泉水,吃着粗糙的干粮,很少有人在想着他们,而眼前这些在后方居住着高楼大厦、享受着锦衣玉食的军官们,从未听见过前线的枪炮声,一个个却俨然以北伐革命的英雄自居,在这里歌舞升平、怡然自得,仿佛前线的那一切胜利和功绩都是他们所创造出来的。这种鲜明的对照,该是多么不公平啊!
游家驹见玉慧看着周围默默沉思,以为她是因为即将离别这舒适的城市而闷闷不乐,便端起装满了法国红葡萄酒的高脚玻璃杯,满面笑容,望着玉慧和沈大戈说道:
“来,让我们一起为慧同志的出师北伐,共饮一杯!”
玉慧和沈大戈都端起玻璃杯来,游家驹郑重地站起来祝酒道:“古时有花木兰、梁红玉这些巾帼英雄,今天的慧同志也应当算上一个。我们要为她上前线奋勇作战、马到成功干杯!预祝她早日凯旋,国民革命胜利万岁!”
玉慧表示感激地也站了起来,举起玻璃杯同游家驹和沈大戈端着的杯子碰了一碰,然后抿了一小口酒。
沈大戈比她的酒量大,端起玻璃杯把一杯酒都喝干了。游家驹感到十分高兴,又急忙拿起酒瓶来为她斟上了满满一杯。
沈大戈又端起那杯酒,向玉慧笑道:“慧姐,人们常说,同船一渡,五百年修。我们同房数月,可真是几万年修下的缘分了。今天我借花献佛,敬你一杯,为你就要到前线去,为那两位真正的北伐英雄——你最尊敬的表兄齐渊和你最亲爱的李剑同志,干杯!”
听着沈大戈提到李剑和齐渊的名字,玉慧的心中也深受感动,觉得是一种很大的安慰。她高兴地端起酒杯,感激地说道:
“大戈,你说了一句很公道的话。真正的北伐英雄,是那些正在前线浴血苦战的将士,我们只不过是去作他们的后盾。让我们一起来为前线的英雄们干一杯!”
接着,她激动地举杯同沈大戈和游家驹碰了一下,端到唇边一饮而尽。
游家驹喝干酒后,一面拿起酒瓶为她们斟酒,一面表示抱歉地说道:“刚才怪我失礼了,怪不得慧同志不肯赏脸。我们不应当忘记了在前线奋勇流血的北伐英雄,特别是还有慧同志两位最亲爱的人。现在我来重新敬一杯,还请慧同志赏光。”
“我的酒量实在不行了,游副官,大戈是完全知道的。”玉慧的脸颊确实已经泛红,她急忙含笑推辞道。
“慧姐真是很少喝酒的。”沈大戈向游家驹嘲笑道,“不像你们那些挂斜皮带的,整天醉醺醺的搞惯了。”
“你这就太冤枉人了!”游家驹急忙放下酒杯,认真地分辩道,“我们在总司令身边办事的人,平时也是很少喝酒的。谁要是敢喝得醉醺醺的,那在总司令身边一天也留不住了。”
沈大戈不以为然地笑道:“看你把你们的总司令说得就像圣人一样,那你们这些总司令的部下自然也都是模范革命军人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