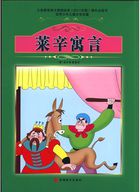12
那夜,他烦躁地睡不着,折腾得田俊凤也睡不成。忽然,她猛坐起来,定要追问有什么事。他瞒不过了,也确实憋得难受,想释放下,便把事情如实说出来。她惊张地“啊”了一声,瞪大眼睛直吼:
“你疯啦,这是犯法的!”
“去去去!外面的事你不懂,少管!”
“不是我要管。是咱爷怕你迷了心性,让我管的!”
没错,爷爷临终前是这样交代的。他咝地倒抽口气,打了个冷战。不由得想,爷爷说她是“旺夫命”,或许正是这意思?应该是。一个把男人逼向疯狂贪婪的女人,即使很聪明,但是做得很愚蠢。因为她可能不是在“旺夫”,而是在“毁夫”,最终也毁了自己。他歪着头想了想,觉得是这理儿。
“那钱呢?在哪儿?说呀,在哪儿?”
她直撅撅地逼问。他木愣着脸懒得回答,朝梳妆台瞟了一眼。她看见了,那上面放着他的公文包。她光着身子跳下床,滋溜拉开鼓囊囊的黑皮包。慌了点儿,成捆的钞票扑扑腾腾兜在台面上,一大堆。她惊得大瞪眼,乳房簌簌直抖,竟蹦出句没头没脑的晕话:
“这这……若出了事,会判、判几年?”
“滚你的!说什么来着?败兴!”
她见他发了火,自知失口,不敢再顶撞,委屈地抽咽起来。她一哭,他软了,意识到自己不冷静。因为他明白,这钱若“出了事”是够判刑的。这使他心里发毛了,身上嗖地起了层鸡皮疙瘩。他很感晦气,事还没办呢,竟冒出句这话!他有种不祥的预感。人在脆弱时,都会产生这种诡谲的潜意识。它构成一种心理暗示,对某种行为选择产生影响。
他犹豫了。
田俊凤躺进被窝里,侧过身子不搭理他,仍在哭。他更没了脾气,反倒想:“也许她没错,自己发烧了?”也是,她不鼓动他冒险走极端,而是制约他保持审慎。这有什么错呢?“我不是怕你出事么?”田俊凤边哭边嘟哝,“若出了事,咱妈咋整?我和孩子咋整?要是爷爷在天有灵,让他评评理,我错了吗?”
他低下头不吭声了。是,若让爷爷“评理”的话,指定会说她是对的。爷爷读过《易经》,曾给他讲过阴阳制衡的义理。说女人是以阴柔的妇德,去克制男人阳刚的烈性。这话,他至今仍记得清。他突然冒出个玄想:“也许,上帝造出男人和女人,正是通过这样的阴阳制衡,使人类达到中和状态?”但这只是一闪念,他没再多想。只是叹了气,后悔不该发火,便拍了下她的肩膀:
“你睡吧,让我再想想。”
他强制自己镇定下来,自我警戒着:“太乱了,太乱了!得静下心再理理,再理理!”他靠在床头上,点上支烟抽着。哲学科班的训练,使他习惯于逻辑思维归纳、推理、判断那一套。不大会儿,他“理”出头绪来,对动用公款跑官买官这档子事,归纳”出四种可能性:1.可能跑成事也没出事(如愿以偿);2.可能跑成事后却出了事(先甜后苦);3.可能没跑成事也没出事(白跑白送);4.可能没跑成事又出了事(鸡飞蛋打)。他扳着指头一掐算,嘟哝了句:“对,只有这四种可能。”
这很沮丧。因为只有一种可能是他愿意看到的,其余三种都不愿看到。也等于说,他是以四分之三的失败概率,去为四分之一的胜算冒风险。“值不值呢?是啊,值不值呢?”他这样反问着,动摇了,困惑了。
他一连抽了几根烟。
田俊凤睡着了。他时不时地瞟她一眼,心里老想着那句愣话:“若出了事,会判几年呢?”他不敢往下想。那堆钞票,仍在梳妆台上堆着。他感觉刺眼了。好大一笔钱啊,它能为他往上爬提供资助,也能让他走向不归路。胆儿大者,也许只看到有利的那一面。他胆儿小,更多的是恐惧发生不测,为此惶恐不宁。他捏着半截烟头,抽上两口便摁灭,紧接着再点着———不停地摁、不停地抽,完全是下意识的动作。他的思维处于混乱状态,以至搞不清想抽烟还是不想抽……总之,他害怕了。第二天,他把那钱如数退给了财政所长。不过,他也跟老夏学了点儿乖巧,把事情弄得神不知鬼不觉,再次把财政所长糊弄住了。
“这钱,还拿去吧。”他故意说得很轻淡。
“咋的?不是说,今天要去谈招商项目吗?”
“黄啦!那项目黄啦,不用再去啦。”
13
几天后,倒不是什么项目黄了,而是他接任书记的事“黄了”。新任书记叫赵文轩,曾当过县委书记许由化的秘书。这一说,都明白是咋回事。但组织部长跟他谈话时这样解释:“你当镇长时间短,接任书记呢,条件不太成熟。从大局考虑,让文轩同志接任,更稳妥些。”
赵文轩比他大几岁,从年龄上说是“成熟”些。这算个说法。可在本次调整中,刘集镇的镇长王敢闯比他小两岁,当镇长还晚半年,却接任了书记。怎就“成熟”了?组织部长说:“这是根据工作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嘛。”他只说“工作需要”,也没说清如何需要,把宁立本打发了。
他压根儿瞧不上王敢闯。那小子仅是中专毕业,开会讲话都没个条理,常常让下边的人听不出头绪,没法记笔记,有时还念错别字。就这水平,竟能接任书记,而他却“不成熟”。他很憋气。懊丧地回到镇里,跟老夏诉说一通。
老夏也很泄气。自己的推荐意见没采纳,挺没面子的。他低着头抽了一阵子烟,不时地瞟他一眼,那眼神像是说:“弄到这一步了,再说这些顶屁用?”又像是对他很失望:“还说呢!我把什么都替你想了做了,可你关键时候掉链子,不上道呀,怪谁?”但这话没说出来。直到一支烟抽完了,才不紧不慢地说:
“是啊,你说得没错。王敢闯那小子,论德论才论实干,都不比你强啥。可就是……”老夏说到这儿停顿了下,又点着支烟,“可就是,你比他好像缺点啥……”
“缺、缺点啥?”
“胆!”
他身子摇晃了下,鼻子咝地一酸,有种想哭的感觉。他骨子里瞧不起王敢闯,可人家居然上去了。他是感到气愤,想跟老夏倾诉一下,谁知没得到同情,反倒受到奚落,这更难受。他想为自己辩解,说不是没胆,而是想堂堂正正做人,不屑于使那手段。对,是不屑。
他突然想到“不屑”这个词,好像占领了道德制高点,自觉有些清高的凛然。可是,他看着老夏责备的眼神,却忽地泄了气。他知道,老夏是嫌他窝囊,因为周围人对王敢闯多是赞叹的口气:“这小子真行,你看上得多快。噌噌几下子,就当上书记啦!”至于,他是通过什么门道或手段上去的,一般不深究这个。人们多是看重博弈后的结果,而不是博弈中的品格,甚至忽略了信仰和手段的冲突。“不管怎地,人家上去了,这就叫本事!”人们大多这样认为,老夏也是。而他对此却说“不屑”,是否有点儿另类?
那个“不屑”的词儿,他没敢说出来,好像自己没本事,却拿“不屑”打掩护,这样反倒显得更蠢笨,也更窝囊。他揣测着,王敢闯八成是使了“跑送”的手段。他很容易想到这一点,因为他也曾试图去跑去送,只是犹豫了下没出手。这时,他竟嫉妒王敢闯胆大,能使出“那本事”,而暗愧自己胆子小,没“那本事”。
他委屈地垂下头,像做错事的小孩儿,不敢抬眼看老夏。直觉那眼光含着鄙视,就像盯着一个无能的笨蛋,一个让人泄气的笨蛋。
14
他在青龙镇当了五年多镇长才接任书记。此时,王敢闯又跨进一步,当上了县交通局长。这就是机遇。你这次慢了一步,接下来步步赶不上。
渐渐地,他对王敢闯也不得不服了。
这小子肚里墨水不多,可往上边跑项目、跑资金什么的,特投门儿。当上交通局长没几年,从北京到省里、到市里都混得路路通。有时,往上边“跑”什么大项目,书记、县长连门都进不去,带上他去打关节。他往门口一站,朝里头打个电话,门卫立即放行。书记和县长趁着他的面子,跟在屁股后头,夹着公文包缩着脖子溜进去。就这本事,书记、县长都服,你服不?
那几年,他给县里弄来不少投资项目(资金)。有了钱,自然能干成事。全县一级公路里程居全省首位,凭这个,他后来被提拔为副县长。从正面说,领导不是指定要重用他,而是看他着实有能耐,能弄住事。对此,县里不少干部也这样认为:“就得用王敢闯这号人,能弄住事!”
确实,不少人见到王敢闯都竖起大拇指来。这使宁立本越发难受。尤其是,当他看到他很神气地坐在主席台上,或在县电视新闻里频频露脸,或被周围的人们簇拥着恭维着,心里更有种说不出的滋味。嫉妒?还是自愧不如?好像都有点儿。
王敢闯倒是义气,当上副县长后,仍把他当哥儿们看。他是胜利者,对落败者当然不会有嫉妒,甚或,更愿摆出“苟富贵,勿相忘”的样子。每逢见面,他仍会拍着他肩膀称老兄。他呢,会下意识地趔下身子,感觉不舒服。
他开始自卑了。进而怀疑,自己是否真的不行呢?进而琢磨,到底“不行”在哪儿呢?有时,他把自己的“不行”归因于父亲。从小老打他,把他打得没了胆儿。但他又不甘自认“不行”,尤其是当着别人的面,他更愿摆出“不屑”的样子。意思是,我不是不行,而是没把那当回事。
“嗤!争个副县级又怎的?都是身外物。”
他对别人这样表白,倒不是自命清高,至少显得不窝囊。但糟糕的是,他即使“不屑”,别人还替他“屑”呢。“你哪点儿比王敢闯差?凭啥他连蹿几步,你仍原地不不动?”接着会鼓励,你也得跑跑呀!光闷着头干活儿,能行?”言外之意,是说他愚笨或木讷了点儿。当然,话不会说得这样直白。一般会变个说法:不是说他“笨”,而是说他“实”,这好听点儿。
“你呀,太实在啦。”
“实在……不好吗?”
“好是好。就是……太实在啦。”
按说这话是好意,替他抱不平呢。但如今说谁“老实”或实在”,似乎暗含有“笨”的意思。也许是价值观的混乱,是非都成了糊涂账,以至把好多词性也搅混或颠倒了?他听着这些话,直觉像褒扬,细品又像贬谪;仿佛帮他打架,本来是好意,却失手扇了他一耳光,他只觉脸上热辣辣的,还没法说。是啊,说什么呢?
15
“那些年,我一直觉得王敢闯是个谜。”宁立本说,“他打哪儿来恁大本事啊?几乎没办不成的事,没打不通的关节,像有什么魔法似的。”
他说着捡起一颗葡萄丢进嘴里,一边仔细品嚼着,一边就像在揣摩那个“谜底”。我也很感好奇,朝他眨巴着眼反问:“是呀,哪儿来恁大本事呢?真是谜!”但他没马上回答,却接着讲起王敢闯后来的事。
他说,王敢闯后来出事了。不知打哪儿捅出的娄子,他被突然宣布“双规”。进去没几天就透出消息,说他吐出了一堆行贿受贿那些事,涉案金额高达两千多万。这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被列为省里的特大案件。当然,那么多钱不是全装腰包了,也送出去不少。他“咬”出一串受贿的,从北京到省、到县都有;窝案,扑扑腾腾抓进去了一批人。
“天哪,两千多万!”我不禁惊讶。
“你震惊了吧?我当时也很震惊。”他说,“想想,我去找许由化才拿两万,都吓成那样子,人家出两千万都不眨眼!呵呵,自愧不如啊!”
他说着拍下大腿,又摇着头笑了笑。他的表情很复杂,我琢磨不透这笑意味着什么。是自嘲真的“自愧不如”?还是嘲笑王敢闯的胆大妄为?或是对这些丑陋现象无奈的摇头?我真的琢磨不透。眼下,人的心态就这样怪怪的:既鄙夷、愤懑有些人投机钻营捞便宜,又嫉妒、自愧没那本事吃了亏。我揣摩着,在他拍腿、摇头、不置可否的笑里,是否也隐含有这些复杂的心理成分呢?
他很快收起了笑脸,接着刚才的话头,带着调侃的口气问我:“你猜,王敢闯的谜底是什么?”我正在琢磨他的笑呢,略走了神,一下子反应不过来。他见我木愣着脸没反应,便大笑了两声,然后自问自答:“哈哈,那谜底其实就两个字!”
“哪两个字?”
“‘胆’和‘钱’!”
他接着解释说,王敢闯之所以有那么大本事,说白了就是胆子大,敢把大把来路不明的钞票往兜里装,也敢往外边甩。有这个,还愁打不通关节?我“咝”地倒抽口气,仿佛豁然顿悟了似的。可转念一想,这“谜底”其实没啥神秘的,不就是拿钱开道么?这招数,也实在没多少技术含量,斗下胆的事……这时,我不由想到他给县委书记送那两万块钱,这么简单的事,他居然跟搞科研课题似的,归纳、推理、判断,竟捣鼓出那么多逻辑推论的“概率”。是不是有点儿可笑?
我瞟了他一眼,却没笑出来。不不,我是觉得不该笑。因为王敢闯的下场,恰好印证了他捣鼓那些“概率”也没错。不妨说,是种理性的审慎。这该嘲笑吗?我于是严肃起来。这时反觉王敢闯有点儿愚蠢,他为满足某种功利欲望,不惜提着脑袋去冒风险,值吗?起码不理性。
这便是王敢闯的悲剧。他因犯罪数额巨大被判处死刑。
谈到王敢闯的死,他的脸色阴沉下来。他说,他对王敢闯的死很痛心。到这份儿上,他当然对他已没了嫉妒,都判死刑了,还嫉妒什么呢?当他对王敢闯没了功利攀比的嫉妒,当他以纯净的人情去看待王敢闯的不幸,便转向了对他的同情。因为他跟王敢闯有深交的,这时感情的因素占了更大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