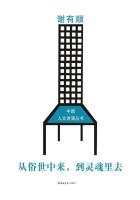让人物越出环境的正常稳态,进入“第二环境”,目的是为了让人物的情感越出正常的稳态,进入“第二心态”。当人物处于第一环境时,环境结构与情感结构互相开放,均处于一种平衡状态,一旦环境发生结构质变,则必然迫使情感结构的表层失去稳定平衡。但是情感结构不像环境结构那样易于瓦解,外来的信息不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情感结构不会发生层次质变,因而第二环境往往有某种极端的性质,巧合的性质,把老虎送到武松面前,把白骨精送到唐僧面前,把薛宝钗送入贾宝玉的洞房,把林黛玉与贾宝玉强行分开,让一个普通工人马丁.伊登爱上上层资产阶级的小姐,让乞乞科夫去买死去的农奴的灵魂,这种极端有时是情境的极端,有时情境虽不极端,但是动作效果却很极端。这是因为动作效果是经过情节的连锁性作用而放大了的,强化了的。这在情节性很强的小说中特别明显地表示出来,中国古典小说十分强调一波三折,一次打不破,再来第二次,两次打不破就来第三次。就是为了达到那个打破平衡的极限,所以才有三打白骨精、三打祝家庄、三气周瑜、三看御妹、三难新郎、三笑、三请诸葛亮、三进山城、三上桃峰,诸葛亮甚至要六出祁山七擒孟获、九伐中原,都是效果的连锁强化。非情节性小说追求的不是动作效果,而是内心效果。外在条件的微量变化引起的内在情感调微也是层层放大,层层强化的,目的是进入“第二心态”。契诃夫在《文学教师》中让热爱着妻子的丈夫因家中“狗”的气味逐渐在潜意识中增长了厌倦,在鲁迅的《伤逝》中,涓生和子君的分歧从小油鸡和小狗阿随开始,然后在不知不觉中放大最后导致分裂。这种积累是在潜意识进行的,而不是在外部动作中进行的,因而不易被主人公乃至读者察觉。
在极端情境中揭开人的情感结构有两种结果,一种是超稳态的结构,表层和深层绝对平衡,铁板一块。如阿Q、唐.吉诃德、好兵帅克、哈姆雷特。不管什么样的环境变异,外来打击都没有打破阿Q情感的超稳定结构,一切客观上的失败都在这个超稳定结构中转化为主观的胜利,不管怎样的屈辱都不能改变他的自我麻醉以及情感和意志的自我封闭。甚至毫无道理地枪毙他,他也没有惊醒过来、大叫一声:冤枉!死到临头,也没有痛苦,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只有风头没有出足的遗憾,为在口供上圆圈画得不圆而产生一种失落之感,为唱不出一句戏来而恼火,而且还要吹牛,还要自我欺骗:二十年后又是一个……好像他很英勇,死不死完全不在乎似的。
这种情感结构的超稳态与小说美学的历史发展有关。这种表层与深层,第一心态与第二心态的高度统一的喜剧性的特点是把一个主要特征从头到尾地强化到每一个层次、每一个方位上去。这种喜剧性带着古典的单纯性。现代喜剧小说,如黑色幽默小说中的人物就不那么“表里如一”地单纯,人物的情感一系列层次很少是统一在一个单一的特征上的。从文学的古典美来看,不管情感有多少层次,其特征越统一,审美价值越高;而从文学的现代美来看哪怕情感只有两个层次,二者越带变幻性,越具审美价值。人类在历史进化过程中逐渐发现,人的这个自我(主体)不那么简单,并不永远是一元化的,相反,在不同层次上的自我情感有某种多元化的色彩。人好像有一个“总我”,在不同层次上。人又有不同的“分我”。弗洛伊德和荣格的学说更进一步提出在人的无意识中潜藏着一个更深刻、更原始,隐蔽着更多文化成规的自我。从这一点来说,一切把人物情感表现得单纯,纵深层次差异微不足道的作品,哪怕是现代的,当代的,都具有古典美的色彩。
越是到现代,对人物内心纵深结构的探索越带自觉性。
因而就产生了一个历史的动向,那就是人物的情感层次差距越来越悬殊,关于人的概念越来越变得复杂,人越来越不能满足于那种对表层心理结构的把握和凝思了。在表层感知思索中的那个我变得不可靠不真实了,而那个在意识以下的我却变得可靠而真实了。法国评论家让.罗贝尔说:最终我们必须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转入雅克.拉康的“我思,我不在,我在,我不思”。用阿尔托的话作补充,就是“人借助灵犀认识了自己,然而即使在此时,他也没有完全把握住自己”。无意识和潜意识自本世纪三十年代自觉地进入文学领域,风靡一时。对无意识,文学家早已有一种朦胧的猜测,韩波早说过:“我是另外一个人”,现在不用躲躲闪闪了,拉康说:“无意识是另一个人在讲话”。这个无意识中的人,“是一个被社会磨灭、拒绝、消过毒的人,被弄成哑巴的受害者。他受着制约,他顺从,然而他渴望反抗。他有待于被表现,他应该去表现并自我暴露”。
当然,人物情感结构的深层探索不应该是孤立的抽象的,它通过社会环境因子而调动和调节,因而人物情感结构的深层探索、社会环境的深层探索和作家自我的深层探索是同步地协同地起作用的,离开了社会环境,离开了人的社会历史经历,人的深层情感是很难充分地得到揭示的。
人的情感在不同层次上的分化,不但使人的自我丰富了,而且为小说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更广泛的可能性。人的情感在纵深层次上的变异,带动着人的知觉、想象、记忆、意志、判断和推理的变异,这就使人物的心理关系,也就是社会关系处于更加复杂、更富动态性的立体网络之中,这个网络的每一个层次在失衡、调节、重建平衡的过程中,起作用的因子更丰富,失衡的机遇更多,引起的反应更奇特,调节的机制更复杂,牵涉的环境和主体心理层次更多,这样就为拉开人物之间的心理距离,为人物生活在不同的感知和想象世界中提供了更广阔的天地。因而在现代小说中人物比之古典小说,在心理距离方面无疑是更加遥远的。为什么西方的当代小说,那么反复地表现人的孤独感,除了社会环境的原因以外,从文学形象的结构来看主要就是心理距离扩大的历史趋势在起作用。在我国当代小说中也一样,在莫言的《红高粱》、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中,人物之间常常有一种“聋子的对话”之感。好像是巴比伦人在造通天塔的过程中被上帝搅乱了语言,不能进行思想交流一样。这不但是生活在起作用,作家的情感在起作用,而且也是小说的形式审美规范的历史变迁在起作用。
当然,现代小说的这种特色不是凭空产生的,在古典小说中早就萌发者现代美的胚芽。例如施耐庵把武松的环境加以调动,放进去一头活老虎的因子,这就使武松的性格纵深层次分化了,读者看到:在体力和勇气上都堪称超人的非凡的英雄而理深层结构却非常平凡:首先武松打老虎不是主动的,而是不相信店家的劝告,怀疑人家的好心,为人家吓唬他留他是为了赚钱。待到看了县府的布告,确信真的有虎,又爱面子,不肯回头。后来又麻痹了,睡大觉,老虎来了,仓促应战,又心慌意乱,犯了个战术错误,使唯一的武器——哨棒失去了使用价值。只好赤手空拳拼了,产生了一种暴发力。把老虎给打死了以后,这个打虎英雄却连死老虎也拖不动了。当他又遇到两只“老虎”,不知其假,反而胆怯起来:这下子完蛋了。所有这一切都是心理纵深层次的悬殊性分化,都是现代、当代美学意识的胚芽,当然还不是一种自觉的美学原则。施耐庵在写武松、鲁智深、林冲、宋江、杨志时不自觉地遵循发展了这种审美规范。可他在写晁盖、吴用、李逵、关胜、秦明、花荣、卢俊义等绝大多数人物时都违背了这个原则,因而武松等人物从美学原则来说是面向未来的,我国小说美学中的现代美学意识正是在其中无声地孕育起来。这种孕育的特点是无意识的,不自觉的,因而也就是不充分的,就连《红楼梦》那样的杰作也不能例外。曹雪芹虽然写出了贾宝玉林黛玉的某些心理的纵深层次,但就整体来说,他并没有自觉地将人物心态的纵深层次加以系统的辨析,使之分化,拉开其间的差距,使人物心态的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显得悬殊,因而他毕竟只是古典小说审美规范的体现者。有些研究《红楼梦》的学者用现代小说的审美规范去硬套,在分析贾宝玉的性格时,把性格发展阶段性作为纲领,正面地展开,这就忽略小说艺术的古典美的特殊性,难免有胶柱鼓瑟之嫌了。
小说美学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必然在横向充分拉开不同人物的心理距离的同时,拉开同一人物的不同心理纵深层次的距离,这就使小说审美空间充分地立体化了,每一个人物情感结构的立体化成为众多人物心理系统的立体化的重要条件。不论是张贤亮,还是刘索拉,不论是张辛欣,还是莫言,无不得力于此,就连表面上看来古典美色彩最浓的高晓声在他最成功的作品中也对而表现出现代美学原则的巨大威力。高晓声明确说过,他平反了,进城开会,一打听,旅馆五块钱一天,他当然可以拿到公家去报销。他转而一想,换一个农民来检验一下,看看他的心理结构如何变化。于是一个表面上老实、善良、自卑的陈奂生在付出那五块钱以后,变得不那么老实、善良、自卑了,他暴发出一种报复心和破坏欲,到床上去滚一滚,到沙发上去跳一跳,巴不得把它弄坏了才称心。
在古典小说美学走向现代小说美学的过程中人物的自我逐渐多重化了,双重人格、“两面人”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探索的稳定范畴,而托尔斯泰则在《复活》中写聂赫留朵夫进入卡秋莎卧室时明确概括出在人的心灵深处有神性和兽性的斗争。这种互相矛盾的二重组合,不是静态的平面的,而是在动态的纵深层次中分化的。在《复活》第一部第五十九节中,托尔斯泰这样写道:
有一种极为常见而且流传很广的迷信,认为每个人都有他独特的确定的品性,认为人有善良的,有凶恶的,有聪明的,有愚蠢的,有精力充沛的,有冷漠疲沓的,等等。其实人不是这样。……人好比河:所有的河里的水都一样,到处都是同一十样子,可是每条河都是有的地方河身狭窄,有的地方水流湍急,有的地方河身宽阔,有的地方流水缓慢,有的地方河水清澄,有的地方河水冰凉,有的地方河水混浊,有的地方河水暖和。人也是这样。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切人性的胚胎,有的时候表现这一些人性,有的时候又表现那一些人性。他常常变得完全不像他自己,同时却又始终是他自己。
托尔斯泰笔下的聂赫留朵夫就是这样的。他第一次和卡秋莎发生感情时,他还是一个纯洁的大学生,但等他入了伍,他的情感纵深层次的兽性就因客观环境的变化而暴露了出来。在宏观的人生经历中是这样,在微观的情感细胞中也是如此。托尔斯泰在写完上述那段话以后接着写聂赫留朵夫去监狱探望玛丝洛娃(卡秋莎)时就严格遵循了情感层次分化的美学原则:
原先他在出庭以后,在初次探望卡秋莎以后,体验过重获新生的庄严和欢乐心情,可是如今这种心情完全过去,在最近一次会晤以后,已经换了一种恐惧的心情,甚至憎恶她的心情。他已经决定不再离开她,也没有改变只要她乐意就跟她结婚的决心,然而这在他却显得沉重而痛苦了。
聂赫留朵夫的微观感情层次被表现为:庄严和欢乐——恐惧,憎恶——沉重而痛苦。情感的深层与表层是如此不一致,他变得不像原来的他了,可是更深刻地显示了他和她的特殊心理层次。
托尔斯泰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创作上都无愧为古典小说美学走向现代小说美学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