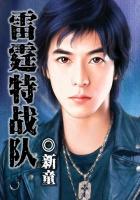內篇逍遙遊
神遊寥廓無所拘礙、是謂逍遙遊。莊子欲歆動學道之人,故首以此名篇。內、外、雜篇,猶前後續集爾。初無異義。按漢藝文莊子五十二篇,郭象固已辨其巧雜十分有三,今所存三十三篇。東坡蘇氏又黜讓王、盜跖、說劍、漁父,而以列禦寇接寓言之末,合為一篇,其說精矣。然愚尚謂刻意、繕性亦復膚淺非真,宜定為二十六篇。內篇皆先立篇名,而篇中意不出此。外篇與雜篇惟摘篇首字以名之,蓋內篇命意已足,外篇、雜篇不過敷演其說爾。
北冥有魚,其名為鲲。鲲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北冥南冥非泛言北海南海,乃海之南北極處,以其廣遠杳冥,故曰冥。鲲,《爾雅》云:凡魚之子總名鲲,故內則卵醬,讀作鲲。《魯語》亦曰:魚禁,鲲鮞皆以鲲為魚子。莊子乃以至小為至大,此便是滑稽之開端。鵬不載經傳。《島夷雜誌》云:崑崙層期國常有大鵬,飛則遮日,能食駱駝,有人拾得鵬翅,截其管作水桶。鲲言大不知幾千里,鵬言背不知幾千里,質之大者化益大也。怒而飛,鼓怒作勢,方能起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者,運、動也。颶將起則海氣動,故徙以避之。《魯語》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展禽曰:今玆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皆知避其災。是歲海多大風,冬煖,是其事也。天池者,海水際天處,猶日浴咸池之池。池,為魚烏所泊之所,鵬所泊在此池也。曰南冥者,天池。又曰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蓋為冥海二字猶未盡極遠之義,又申之曰天池,則方見是海水際天處,以見鵬飛從海之極北過海之極南,如此其遠也。篇首言鲲化而為鵬,則能高飛遠徙,引喻下文人化而為聖為神,為至則能逍遙遊。初出一化字,乍讀未覺其有意,細看始知此字不間。
《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齊諧》者,齊人諧諺之書。孟子曰:齊東野人之語,則齊俗宜有此諧之言。日者,諧諺之書所言也。莊子自多怪誕,卻謂齊諧,為志怪亦是滑稽處。擊,打也。鵬氣勢飛上,波浪打起,其高三千里也。搏,隨風園轉也。扶搖,旋風也。風勢相扶搖擺而上,所謂束海扶搖之枝亦取此義。九萬里者,言北冥至天之里數,若中土至天頂則又不止此數。按《考靈耀》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每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圓周一百七萬一千里。以圍三徑一言之,直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為二十八宿周圍直徑之數。又二十八宿之外,上下東西各有萬五千里,是為四遊之極,謂之四表。據四表之內并星宿內,總有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徑。天中央正半之處,則一十九萬三千五百里。地在於中,厚三萬里。春分之時,地正當中。自此漸漸而下,至夏至之時,地下萬五千里,地之上畔與天中平。夏至之後,地漸漸向上,至秋分,地正當天之中央。自此地漸漸而上。至冬至上遊萬五千里。地之下畔與天中平。自冬至後地漸漸而下,地常升降於三萬里之中。四遊之說元出《周牌》文,渾儀家未有未知然否,但其以天度紐筭里數似為可據。又鄭玄註《周禮》,以句股求表景,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三十步五尺,三寸六分為天徑之半者,乃日下距地之里數耳。去以六月息者,鵬起北冥而徙南冥,經行半周天之里數,故止消半年而息,以見鵬飛亦合天度也。上只言鵬徙之遠,此又證其飛之高,先安頓九萬里一句,在此後面卻從而解說。
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息,氣也。野馬,塵埃,喻遊氣也。橫渠張子曰:氣坎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綑縊,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歟。晦庵朱子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遊氣之紛擾也。蒼蒼,遠望之色。已,止也。此不過解說九萬里一句。恐人認遊氣蒼蒼,便以為是天體之極處,疑無有九萬里。故言太虛中如野馬塵埃者,乃造化生物以此氣相吹者也。人囿此氣中而不自知,但遠望則蒼蒼然。今仰而觀之,其蒼蒼然者,是天之正色邪,抑上面猶遠而無所至極邪?自蒼蒼而上,尚無窮極,是以鵬去得九萬里。至於自上俯視下亦如此。蒼蒼然者則為有形之地矣。止於此矣,不可復去矣。蓋言蒼蒼之上非如蒼蒼之下去不得也。漢都萌云:天了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瞽精絕。故蒼蒼然,正與此合。則已矣三字,說者多作而已矣,連過看遂致上下文意不貫。
且夫
轉接處多用且夫,請試言之等,讀者若知此機括,亦使文字不斷。
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均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關者,而後乃今圖南。
坳堂,堂上地助處。芥為之舟,芥流轉如舟也。培,積也。青天,非自下所見蒼蒼然者,九萬里上方是青天。上文言蒼蒼非正色,則青為正色,可知六經未有言青天者,只言蒼天。蓋止據所見者言也。又解說鵬之所以必飛上九萬里者,要藉風力之大方能遠徙。以水喻風,以舟喻鵬,水不厚則負大舟無力。風不厚則負大翼無力。故九萬里高則風在下,力厚盛得許大,背負青天則天路空闊無有妨害。鵬惟培得此風方可圖南。乃今者,將徙之時。下文且適南冥則遂徙矣。此一節說餛鵬變化之異,引《齊諧》者所以證其飛上九萬里,野馬以下所以申明可至九萬里之理。
蜩與鷽音渥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
蜩,蟬類形黑,而五月鳴者為蜩;形斑而七月以後鳴者為蟬;形青者為蛁蟟音貂料,其類不一。俗總謂之蟬,或蜣蜋,或水蟲,或糞中躋螬所化。鸒鳩,鸒本山鵲之名,以其類山鵲故名黌鳩。月令鳴鳩拂其羽。疏引郭璞云: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今江東呼為鶻鵃音骨嘲。《月令》仲春鷹化為鳩,《王制》仲秋鳩化為鷹,《左傳》爽鳩氏。杜註鷹也。亦以二物相化,故鳩可名鷹。二蟲能化而小,故以與餛鵬相形。決起,盡力而起,猶決戰之決賭此氣力也。搶,衝突也。榆枋,二木名。時則不至而控於地,有時榆枋亦不能至則控止於地,言二蟲飛不能高也,此設為蜩鳩笑鵬之辭。凡人之以小見而笑大道者,何以異此。
適莽蒼者,三滄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
莽蒼者,一望之間莽然蒼然也。果,能腹飽之貌。果,勇也。腹飽則勇,餒則怯矣。二蟲,蜩鳩也。人所適彌遠,則積糧彌多。鵬翼彌廣,則積風彌厚。二蟲又何足以知之。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
二知字皆平聲,綴上知字起下,莊子文法多如此。二蟲之所以笑鵬者,只為所知之小不及鵬所知之大耳。因借小年大年以喻小知大知。
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
菌,地蕈也。大曰中道,小曰菌。菌之生以朝計,故曰朝菌。蟪蛄亦蟬類。鄭氏《通志略》云:寒蠻正名蟪蛄,九十月其鳴悽急。小山云:蟪蛄鳴子啾啾,歲暮子不自聊是也。莊子所謂蟪蛄不知春秋者,則是四五月小紫青色者耳。冥即南冥。靈,靈龜也。麟鳳龜龍謂之四靈。冥靈者,冥海之靈龜也。朝菌與大樁,蟪蛄與冥靈,是舉一植一動對說,則冥靈非植物明矣。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者,《史記》曰:龜千歲尺二寸。二箇五百總千歲之數也。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者,拆椿字為二箇八百,乘之以十則二箇八千之數也。滑稽杜撰偶然出此,殆亦亥字二首六身之類。而愚弄千載之下,莫有能悟。蓋凡如此者,人例以寓言目之,而不知所謂寓言亦必有所依倣。近似讀莊子者,勘破此等,則其怪誕之術窮矣。彭祖、衆人,又人之小年、大年也。以衆人而匹彭祖,則衆人可悲矣。此言年之小大懸絕亦如人之小知大知也。
湯之問棘也是已:
引湯問棘一段便是蜩鳩笑鵬之比。
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光去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為鯤。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大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鎢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
羊角者,搏扶搖之形。《夢溪筆談》云:恩州武成縣有旋風自西南來,望之插天如羊角,官合居民悉卷入雲中。又《志林》云:眉州人家畜數百,魚深池中三十餘年,忽一日,天清無雷,池有聲如風雨,魚盡踴起,羊角而上,不知所往。二事所紀皆得莊子本意。絕雲氣者九萬里,高則截雲氣在下矣。斥者,斥鹵之地。書所謂海濱廣斥是也。鴳,駕也,內則爵鸚蜩。范疏引公食大夫禮,以鴳為駕。李巡云:鴑囗是鷃,即駕駕,即囗。《月令》季春,田鼠化為駕。是鴳亦化之小者。故以比蜩鳩。又就海濱討箇小小變化之物,引證蜩鳩笑鵬之說。夫鳩之化也,已失其鷙擊之習,蜩之化也,僅脫於汙泥之中,低飛榆枋,無復遠見,其竊笑,固亦無怪。殆猶窮鄉下士,烏識大人君子之?前斥鷃雖賦質微小,不出蓬蒿,然生於海濱,宇宙之大,風月之浩蕩,亦飲見而熟知之矣,乃亦妄訕大鵬。其於人也,遊聖人之門,而下愚不移自暴自棄者歟。自湯問棘以下數語,收拾前面。殆盡前引齊諧志怪,此引湯問棘,又似實事。前言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此又實其廣數千里。前言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此又實其背若大山。前言搏扶搖而上,此又添羊角二字形狀之。此一節說蜩、鳩斥鴳變化之小而反笑鵬之九萬里。凡言九萬里者四,大意只解說此句。要見天池距天實有九萬里。太虛寥廓,神遊無礙,以破世俗淺漏之見,而豁其逍遙之胸次。
故夫
前一段是先設一箇譬喻,此一段卻從人身上議論。
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
此一等是小見之徒與蜩鳩斥鴳何異。
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並音朔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
猶然,笑貌。猶與囗字義同。前一等人是以小笑大。宋榮子卻笑前一等人是以大笑小。且者,不特能笑前一等人,且能如下文所云也。未數數,不汲汲也,樹,立也。宋榮子不惑於人之毀譽,而內外之分,榮辱之境了然胸中,以為吾之自守,如此足矣。此一等人雖不汲汲於世,猶未能卓然自立也。
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出一遊字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
泠然,風清之意。善者,善之也。旬有五日者,半月之期,比之半年一息者異矣。致福者,待風而後能行,風起則是其福。未數數然者,不汲汲於得風以為福也。乘車者主也,御車者佐也。天地之正氣,即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人所得以生者,道家謂之先天一氣。六氣者,陰陽風雨晦明。厥陰風木、少陰君火、少陽相火,太陰濕土、陽明燥金、太陽寒水,皆謂之六氣,名殊而實同。散在天地間,而具於人身者也。以正氣為主,六氣為御,即老子三十輻共一轂之義。列子固勝宋榮子矣,然猶有所待。此一等人猶未盡化。若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神遊無極者,無非取之吾身,又何待於外?至此則無不化矣。下文卻指能如此之人。
故曰:至人無己音紀,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舊解以此三句為上文結句,不知乃是下起句。上既次兩等人化之小者,此卻次三等人化之大者。大而化之謂聖,聖而不可測之謂神,至者神之極。三等亦自有淺深。無功則事業且無,何有名聲。無己則并己自亦無,何有事業。下文逐一證之。許由聖人也,藐姑射神人也,四字至人也。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醮爵二音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懽,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闕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鹪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許由隱於箕山。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有許由塚。立,起也。尸,主也。闕然,不足也。堯言許由起則天下治矣,我乃猶主此位,自視不足,不能及許由也。名者,實之賓。實為主而名為客也。吾將為賓乎,不肯務名也。鹪鵪似黃雀而小,又名鹪囗,一名桃雀,即《詩》所謂挑蟲,俗謂能生鵰。偃鼠即鼹鼠,大鼠也。歸休乎君,休息也。堯即許由訪焉,許由謂堯其歸而息此讓天下之事乎。語尾復稱君,以致其珍重之意。此說聖人無名,故曰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徑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音莫姑射宋廣平《梅花賦》音夜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鍾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八字為一句。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磚萬物以為一,世蘄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囗糠,猶將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
莊子所言人姓名或實或虛,肩吾連叔不可知,接輿即楚狂者。故下文云:吾以是狂而不信。往而不反者,一向說將去更不回顧也。逕,門前路。庭,堂外地。大有徑庭者,徑與庭相距本不遠,今接輿之言比之尋常言語大異,如徑庭之大遠不比尋常徑庭也。藐姑射之山,見《山海經》淖約,淨潔貌。處子,處女也。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言所居而化也。是其言也,猶時女也。此八字當連作一句讀。其指接輿也。猶即若也。時,此也。女即處子也,因上淖約若處子而言,接輿言神人之如此處女也。如下文所云:言字下著一也字,是他句語軟活處,若作兩句讀,誤矣。旁礡,轉石聲。言其能轉動萬物也。蘄乎亂,求乎治也。弊弊,疲困也。塵垢囗糠,猶將陶鑄堯舜,堯舜所得者,神人之所棄也。此言神人無功,明曰有神人居焉。又曰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旁礡萬物以為一,世蘄乎亂,皆言功也。
宋人資章甫而適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四子不必究其姓名。汾陽,堯所都。堯見四子於藐姑射之山,歸汾水之陽,而窅然若喪其天下。蓋見四子而自失也。卻先說一箇譬喻,越人斷髮文身,何用宋人之章甫。四子隱逸山林,何有堯之政治?此言至人無己,四子不知有己者,堯見四子亦失其在己者。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可容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裒上之以為瓢破之為二,則瓠落無所容。
瓠讀仍本字。瓠雖大,剖之為瓢,則其瓠淺落而盪漾,所容不多矣。
非不呺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掊彼口切擊碎也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乎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漂絮者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音稅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音拜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思也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蓬字正與江湖字相對,言不浮遊江湖而此心猶局於山林草萊之中也。此言一器之用而未化,若以之浮遊江湖則化矣。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音拳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狂乎?
狸狌,鼬鼠也,狀如鼯,赤黃色,大尾,能啖鼠,俗乎鼠郎。郭璞云:江東名鼪。
卑身而伏,以候敖者;
敖平聲,物之遊遨者,雞鼠之屬。
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毗赤切,
入於機中,如受刑辟。
死於罔罟。今夫斄音厘又音茅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
狸狌小,能捕而反遭害。牛大不能執鼠,而得全其生。
今子有大樹,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
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此言一木之用而未化,若樹之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則化矣。
此篇以逍遙遊名,而終篇貫串只一化字。第一段言鲲鵬蜩鳩斥鴳之化大小不同,故其飛有高下。第二段言人之化亦有大小不同,故其為逍遙遊有優劣。第三段言人能因無用而化為有用,則亦可以逍遙遊。夫天之所賦各有定分,豈可強同蜩鳩斥鴳於鯤鵬哉。而人則無智愚賢不肖,皆可以階大道。然亦有自視若蜩鳩斥鴳者焉,故於篇終曉之曰:人雖如呺然難舉之瓠,擁腫卷曲之樗,苟能因其資質用之,隨事而化,豈失其為逍遙遊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