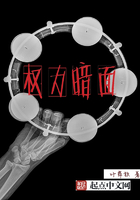“呵——”半个时辰过去,一直守在厢房门口的蒋云言有些困意。
他使劲眨了眨眼,顺便舒缓了下自己因整日采草药而酸疼的腰。
前日阿墨才刚刚可以下床,半夜里突然掀了他被子,双眼放光、一脸神秘地问他:“阿言,你想不想治好咱么爷?”
美梦被搅,他本是满脸怒气得瞪着他,可一听说有机会能治好主子的病,原本蓄满力气挥出的拳头都变成了蒋云墨肩膀上赞许的一拍。
想不想治好自家主子?
他当然想!
他们跟随主子一起出兵多年,金戈铁马,疆场杀敌,几次陪着主子死里逃生,而司华容虽贵为皇子,却没有一丝一毫京城纨绔子弟的架子,反倒常常和他们一个烤架前大口喝酒,一个营帐里抵足而眠。
这样的主子,怎么能不让他们真心相待?
所以听了阿墨的计划,他几乎是立刻抓了衣服跟着去了后山,用了整整一天一夜的功夫采了满满两个柳条筐的草药。
想到这里,蒋云言再次回头看了一眼厢房。往日里总是阿墨滔滔不绝,口若悬河。没想到今日自己也跟着坐立不安起来。
他揉了揉胀得发痛的太阳穴,自言自语道:“希望唐小姐能治好主子。”
而厢房内,唐小姐真就在‘医治’司华容。
手起针落,唐夏满意地看着眉头皱起却仍旧一声不吭的司华容,冷嗤道:“你还没死,用不着嘴硬。”
随即左手食指中指迅速切上他的右腕上,细细听脉。
上次司华容强行把唐夏带到屋顶上时,她曾经悄无声息地把过这个人的脉:脉象沉弱,细微如蛛丝,可见其所中寒毒之深。
然而当时的司华容,从把她带上屋顶,到凌空飞跃,身上都没有一丝一毫的虚弱感。
如今再次切脉,脉象比之从前更加微弱。
可他身上的气息,竟然是一如既往的沉稳,没有一丝扰乱!
这个人,狠!
唐夏低头轻笑,随后松开左手,拿了桌案上的青釉茶盏问道:“几年了?”
问的自然是中毒的年岁。
毒素已至心肺,蚕食经脉。她相信换了任何一个人,恐怕早就已经不在世了。
“八年。”桌案对面的司华容心虚道。
刚才唐夏霍然出手,他心里立刻升起了浓浓的不快。身中寒毒多年,他的体温相对常人要低,加上他向来不喜他人触碰,若是平日里不小心接触到其他人,总会给他炙热难忍的感觉。
因而刚才唐夏第一次试图给他把脉时,自己竟一时失态,居然连气墙都用上了。
然而就在唐夏切脉的一瞬间,随着二指轻轻放在他的手腕上,他竟仿佛有丝丝暖流顺着经脉游走,最终挑起他心里一种从没有过的感觉。
他不喜欢。
尤其当他再次看向眼前一身素衣的少女时,自己竟然品尝到一丝心虚的味道。
但司华容很快便恢复了一如既往的冷静。他跟着灌了一杯茶,看着杯子里嫩绿的茶叶打着转道:“八年。”
唐夏意外地挑了挑眉。
真狠。
她轻呷一口手中冒着热气的铁观音,正对上对面司华容乌黑深邃的眸子,第一次略微带上了兴趣地开口:“有笔新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