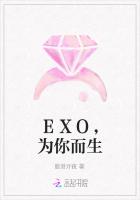有时候她透过眼角发觉月明偷偷的打量她,他细长的凤眼很好看,虽然戴着眼镜,仍遮不住他的满脸英气。
她还不敢肯定那是不是爱,但坐在他的身边她很满足,她知道自己很好看,许多人说她像外国回来的洋妞,她一直忙于学习,忙于农活,忙于家务,她很少有时间照镜子。甚至她不清楚自己的模样。
婧怡的妈妈是甘肃人,有四分之一的维族血统,高鼻子,大眼睛,皮肤雪白,60年代初甘肃闹饥荒,婧怡妈妈一家饿的出不了门,大伯和婧怡爸原本带粮食,腊肉去甘肃农村换家纺土布,看到此景,他们拿出所有携带的粮食、腊肉救了妈妈一家人。
大伯和爸爸离开的时候外婆外爷祈求他们带走他们唯一的女儿,否则也是等死。
后来婧怡舅舅也来狼家坝入赘。
他们的目光有时候也碰在一起,一旦发生触碰,立即闪开。过一会她会发觉他又偷偷的看她,她的心狂跳的快飞出来了。
他终于给她开始讲大学的生活,月明告诉婧怡他喜欢踢足球,每天晚餐后第一件事就是去足球场,晚上冲个凉水澡倒头就睡。
月明温柔的看着婧怡笑着。
“你如果去我们学校一定是校花。”
“什么是校花。”婧怡心里知道校花的意思,但她还是想确认一下。
月明用指头在婧怡脑门儿上弹了一下。
“笨蛋啊笨蛋,”他俏皮的撅起嘴巴,目不转睛的笑看着婧怡。
他有吻吻这个可爱的女孩的冲动,他知道,婧怡很喜欢他。
婧怡刚洗过头,坐在凳子上湿漉漉的头发一直快要伸到地上,洁白的脸颊上微微透着桃红。面上一层微微的汗毛勾勒出她圆融的轮廓,浓密的睫毛在面颊上投下两道扇形的阴影,随着呼吸似乎如蝶羽一样在轻轻颤动。
这也是他继续留下来的一个理由吧!
他举起手去摸婧怡刚洗过的披在背上的长发,就在手快触摸到头发的时候突然停住。空气突然凝固了。
沉默了片刻,他收回伸出去的手,咧咧嘴,一副大人教训小孩子的口吻“好好学习,听到没有,要上大学。”
她看到他眼里的泪光,“你上大学哥哥去车站接你,带你去看足球赛,给你买许多好吃的。”他的声音有点哽咽。
她幸福的点点头,幸福的泪水落了下来,他望着她,她感觉到被幸福包裹的那种昏阙。
许多年后当她回想到此刻的时候依然泪流满面。她知道那是爱,那是陪她一生的唯一的爱。
家逸经常上楼来陪月明,婧怡就远远的坐在窗边看书,家逸和月明坐在楼板上下棋。
月明住的屋子的楼板每天婧怡都要擦两次,她把它们姊妹用的最好的蚊帐给月明挂上。
晚上她趴在楼上呆呆的看月明在后院冲澡,他朝婧怡举起两个手臂,轧起肌肉,做出一副健美运动员秀肌肉的POSE。
他和家逸每天晚上都要从二楼后楼道上爬到屋后的树上练习爬到远处的树上,有一天家逸爸爸兄弟俩甚至带家逸和月明进山转了2天才回来,婧怡知道月明做好了随时出走的准备,她的心碎了。
这样的日子过了差不多一个月,婧怡的中考通知书也到了,她的成绩达到了中考分数线,两家人和月明坐在一起讨论她该上哪所中专的时候,婧怡嘟着嘴吧,硬硬的回绝了家里要她上中专的想法。“我要上大学,要像月明哥,家逸哥一样上大学”
夏天狼家坝有一半时间在下雨,婧怡时不时和爸爸去田里照顾一下庄稼,然后就整天在家里和家逸,月明呆在一起,镇上家逸的许多儿时的朋友经常来找家逸玩,这时候月明就轻轻的移到婧怡家的板楼上。
现在月明已经很随意了,婧怡关了大门,月明就悄悄的下楼,帮婧怡妈妈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他在后院把婧怡家的柴火用刀劈齐整,用绳子绑的整整齐齐的码在厨房里,用腻子和泥巴把房子的窟窿都补起来,然后用白灰把两家人的房间都刷的雪白,亮堂。甚至不嫌脏去牛圈翻粪,还和家逸一起动手给两家人打了吃饭的桌子和小凳子,上了油漆,光光亮亮的摆在堂屋。
“你是哪里人?”婧怡的妈妈打心眼里喜欢这个小伙子,虽然她知道自己的女儿配不上这个小伙子,但她还是忍不住想问。
“陕西武功的,离西安不远,阿姨知道杨凌吗?我们就在杨凌附近。”
“杨凌不知道!但知道西安。”
“我们家离西安不远,每年过年我们就去西安玩。”
婧怡妈妈虽然知道自己的想法是一个奢望,但仍然想知道一些事情。
“家里几口人啊!”
“我和我姐姐,姐姐已经出嫁了,爸爸在县政府上班,妈妈是医生。”
月明突然心酸起来,如果自己大学能毕业,就回来娶这个妹妹,那怕妹妹在家里务农,但现在的情况是,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能够活下来,自己被通缉后,东躲西藏,妈妈的身体不好,不知道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想到这里,他的头沉了下来,心情降到最低点。
他给婧怡的妈妈点点头,去屋后洗了手,上了楼。
婧怡躲在墙后面,一直听妈妈和月明说话,她心里很忐忑。
整个下午,楼上没有一点动静。
妈妈杀了一只大公鸡,炖在锅里。
“你上去把他叫下来吃饭。”妈妈把菜端到桌子上,两家人围坐在桌子旁边。
“他怎么没有动静了?”大伯轻轻的问。
“他想她妈妈了,他想家了。”
月明呆坐在婧怡的床上,眼睛红了一大圈,头发有点长,散乱的蓬着,看见婧怡上来,他头也没有抬,像木头一样动也不动。
婧怡的知道他的痛苦,她好想过去搂住他,安慰他,但她没有勇气。
“无论怎样,只要我活着,我一定来找你。”他抬起头,泪水已经浇透了他白净清秀的面庞。
“你要好好学习,上大学后,除过学习其他的事情不要多管,我一定来找你。”
婧怡心里如千百个小刀在割,她看见自己所爱的人流泪,自己也哭成了泪人,她瘫坐在楼板上,妈妈在楼下轻声唤婧怡,月明站起来,用毛巾擦擦脸,用梳子把头发梳整齐,然后给婧怡把脸上的泪擦干净,伸出手,把婧怡抱起来。
“好孩子,这里就是你的一个家,没有地方去了你就来这里。”大伯把一块鸡肉夹到月明碗里。
什么是爱情,婧怡在上大学的时候曾经读过一本名为《情与爱》的书,书上再三阐述:爱=情,爱+**,二者缺一都不完整,但在婧怡和月明的这段感情里,不掺杂一丝的**,当许多年后婧怡成为大众情人,每当孤独的夜晚,她怀抱着月明曾经枕过的枕头,思念泛滥成灾的时候她都没有想到过**,甚至偶尔有点往那方面想她都会感觉自己亵渎了月明,那是怎么一段感情,清透,干净,湛蓝的如海水。
从那天以后,月明一下就蔫了,他甚至开始抽烟,婧怡去他房间他正在午睡,满脸的疲惫,眼角的泪痕还没有干透,指甲剪的很短,失去了往日的那份细腻,有点粗糙,她一直盯着月明的脸,发觉他嘴唇上有点发乌,她紧张的凑上前去,想看个明白,突然月明睁开眼,直愣愣的望着她,婧怡害羞的低下头,片刻之后就勇敢的抬起头,望着月明,时间凝固了,他们就这样微笑着,对望着。
婧怡感觉他们会永远这样呆下去,晚上,当家逸和月明去屋后的山上散步,婧怡跟在他们的后面,她恍惚觉得月明会一辈子留在狼家坝,她会一辈子陪着他,幸福一辈子。
月明呆在狼家坝很憋闷,他的活动空间只限于室内,这对于酷爱驰骋绿茵场的月明来说开始也难以接受,回想学潮始末,他有一种被利用,被欺骗的感觉,他们的初衷是好的,当局政府腐败如此猖獗,没有一种声音说出来,这样国将不国,因为他在学生会,经常在校刊上写一些评论时政的文章,大胆且幽默,无论出发点还是旁引博征都另辟蹊径,让人读了有茅塞顿开之感,很受学生的欢迎。
性格开朗,酷爱运动,晚会上他的一首吉他弹唱“白桦林”迷倒男女生一大片,加之体型高大,相貌英俊,很直率,所以德高望重,身边有一大帮朋友和粉丝,许多由他发起的活动可以说一呼百应,学潮中他顺理成章的成为学生领袖。
在高中的时候,他暗恋过一个女同学,后来不了了之。
大学生活丰富多彩,他也没有多余的心思和时间去想情感方面的问题。
他学的是工科,班上也就两个女同学,倒是在学潮中,北京外院的几个女生一直跟在屁股后面,特别的川都的那个胖嘟嘟的小女生,在他们绝食静坐的时候,一直时时刻刻守在他的身边,当他虚脱,昏倒以后也是她组织人把他送到私人诊所,使他躲过军警的搜捕。
当他身体稍有起色,她又通过天赋同乡找了一辆汽车护送他们到陕西汉中后搭上去川都的火车,一路上,她对他百般照顾。使他很感动。
但一路嘴巴不停的唠叨也使他烦透了,汽车上,火车上24小时都是她一个人高亢尖利的嗓音,他感觉她做妈妈更合适,每次吃饭都是由她先尝味道,调好以后才递给他,甚至是他的衣扣都是她动手扣好,她一点不忌讳别人,要他换裤头,她也不怕别人怎么看,把他的洗后的裤头挂到汽车后视镜上吹干。
在他离开北京的前夜,另一个高校的学潮领袖找到他,他们要出逃国外,问他愿不愿同往,英雄主义支配着他,有难应该和同学们一起担当,他拒绝了出逃的邀约。
到了川都以后。女孩的妈妈拒绝月明去她家,在川都火车站,女孩子哭的一把鼻涕一把泪,引来许多人的侧目,尽管月明留了胡子,但街道到处都是通缉海报,月明无可奈何的等着警察来抓他。
一个大学生模样的小伙子拍拍他的肩膀,抓住他的膀子,大叫:“表哥,你郎个又逗女娃娃耍撒。”这小伙子就是家逸,他认出了月明。
家逸认识许多家乡来川都拉货的货车司机,他带着月明找到狼家坝狼家司机,介绍“这是我的同学月明。”月明的名字就由此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