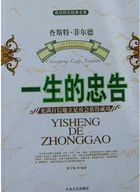雪晗宫。
恪淑媛蓝菲絮在正殿,脊背挺直,双手合十,握着一串佛珠静静祈祷,闻得有人进殿,却不转身,只缓缓念道,语调波澜不惊:“南无,阿弥多婆夜,哆他伽多夜,哆地夜他,阿弥利都婆毗,阿弥利哆,悉耽婆毗,阿弥唎哆,毗迦兰帝,阿弥唎哆,毗迦兰多,伽弥腻,伽伽那,枳多迦利,莎婆诃。”
宁子娴驻足凝听片刻,方缓缓道:“你竟然也念起了《往生咒》么?”
蓝菲絮手势一滞,须臾,又恢复如常:“贵妃娘娘。”
宁子娴缓缓走过纹丝不动的蓝菲絮,于殿中的正座上坐定:“淑媛是在为刘嫔仪念么,嫔仪为淑媛与贵嫔做了不少事,到头来依然难逃一死,只不过,原来淑媛心中还有一丝良心善念。”
蓝菲絮闻言一哂,缓缓张开眼睛,注视着宁子娴沉静如水的面容,似笑非笑:“良心?臣妾早已没有了,难道娘娘还有么?”
见宁子娴不置可否,蓝菲絮徐徐而道,“娘娘也懂得《往生咒》么?是否娘娘也曾送过谁上路?”
宁子娴淡淡一笑,发鬓的双凤衔珠金步摇垂下的朵朵牡丹状的金串珠在烛光辉映中微微一闪,似逼视的眼眸:“本宫虽然未被贬谪过,但多多少少也有过失宠,最黯淡的时候,霁月殿内,都能听到殿外檀树桐花开落的声音。”
蓝菲絮恬和一笑:“子女双全、家世盛宠,尊贵如娘娘者,亦是会有失宠那一日,那么,于臣妾而言,又该怎么办呢?”
“所以,报不得仇的你,便要将本宫一并除去么?即便你能顺利拥立那些个母家毫无背景的皇子继位,你道庄妃与令妃便能轻易放过你么?便是如此,本宫可是听说了,云家的王妃可不是吃素的。”
蓝菲絮嗤的一笑,穿堂而过的冷风吹起她鬓边的几缕碎发,有飘然出世之姿:“宫中,只有永恒的利益,并无永久的情谊。今日的盟友,来日便是针锋相对、明枪暗箭的敌人,不说庄妃与令妃是素来和娘娘亲近,那又如何?她们二人,若来日可以登临太后之尊位,即便心知肚明娘娘是为臣妾陷害,又能怎样?难道将帝位拱手相让?于她们而言,牢牢握在手里的才是最最要紧的,左不过逢着娘娘的忌日便为娘娘哭上一遭。寿康宫,世上只有一座,难不成还要建到娘娘的陵墓去不成?”
顿了顿,又道:”便是凌云,若是知道自己能有机会,云家第一个不会打扰臣妾做什么的。“
芷息闻言,沉了脸色道:“淑媛,请注意你的言辞。”
蓝菲絮冷然一笑:“我已是半只脚踩进黄土里的人了,又在乎这些做什么?”
宁子娴柳眉一扬,缓缓一转手腕上的碧玉莲花镯子:“你又怎知何芳春会供出你来?”
“以娘娘的手腕,又怎会让何芳春缄口不言?”蓝菲絮冷哼一声,转眸旁顾,清水玲珑穿玉步摇上的錾金流苏沙沙的打在她的额边,有冷清曲折的光泽一转,“从娘娘进殿那刻起,臣妾的命,就早已是注定的了。”
“求死,并不难。”宁子娴深深凝眸望着殿外如海般的深沉夜色,静静道,“难的是敢于抛弃自己的家人赴死。何芳春的父亲何邺简可是从二品的江苏盐道,本宫方才已经下令,革除他的职位,着刑部严审,出不出得了刑部,是本宫说了算。淑媛若是放得下自己致仕的父亲一把老骨头不会被本宫押入京城,便大可一死了事。”
宁子娴的话,犹如一盆冰水,彻头彻骨地浇过来,漫便全身,蓝菲絮猛地一震,手里的佛珠串竟“啪”地坠地,原来,线竟已被扯断,那颗颗佛珠便如落于玉盘的珍珠一般,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跳跃着四散而去。
宁子娴翩然起身,语调冰凉,直把那股寒凉之气送入蓝菲絮的肌理:“还有,你若放得下简适……”
“贵妃娘娘!”蓝菲絮一个激灵,惶然垂泪道,”你到底想要怎样!”
宁子娴紧紧迫住蓝菲絮含泪的双眸,眉眼间是不可抗拒的威严与凌厉:“何芳春死前,告诉本宫,本宫慢了一步,终究还是会输。那么,淑媛能否告诉本宫,你们还有什么谋算,若你识相,本宫便饶过你的家人,放过你的情郎!一个为了你可以在本宫面前摇尾乞怜、甚至以毒害皇上来换取本宫的信任的眼线!”
蓝菲絮细白如贝的牙齿微微颤抖,双手紧紧抓住华美的裙裾,想必今日她是用心装扮过,一身华服娇俏竟衬得她颇为清丽。
不过片刻,蓝菲絮终是缓缓跌坐在地上:“刘云心被发落慎行司,臣妾的计谋被彻底打乱,为免夜长梦多,臣妾指使了宫人,在太子日常练习骑射的弓上涂了一层毒药,一旦毒药渗入肌理,便只有死路一条。皇上病重未醒,太子却骤然早夭,娘娘嫌疑最大,自然迟早被废。”
宁子娴一惊,狠狠便要一掌劈过去,掌风一转,却生生停在了半空中,细细一想,终是压了怒气,疾声吩咐芷息道:“赶紧去东宫取走那把弓!”
蓝菲絮虚弱地一笑:“臣妾真是不明白,贤妃一直视娘娘为最大的对手,娘娘若要得到帝位,必得除之后快,左不过何芳春已经死了,臣妾也招了,为何娘娘要如此行事,难道真的与贤妃……哦,不,是皇后,情同姐妹么?”
宁子娴悠然一笑:“谋取帝位,自然不必在意圣旨是否出自皇上之手,前朝尽皆被本宫掌控,就算皇上留下遗诏让凌睿即位,本宫也决不让那遗诏昭示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