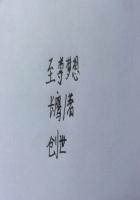梁蕊也回复了笑靥,两个姐妹并肩来到里间,在创伤药物与绷带陈杂的里间放着三张伤员床,最中间的一张床上躺着个十八九岁的少年,头缠绷带,身上穿着伤员专用但略显不合身的白衣白裤,在周遭白色的衬托下,他那头脖间路出的肌肤颜色显得略深,眉眼处倒是清秀,隐隐显出一股天真之气,如熟睡中的孩童一般。
海珠一看到男子便愈发的紧张起来,几欲逃跑,硬是被梁蕊拉了腕子去强赛到少年的衣襟中,梁蕊放了手,海珠本可抽离,可当她按上如石头一般硬的胸膛时,自己的手却怎么都抽不出来了,她能感觉到男子的心跳,更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跳,两个频率却是不一,扑通扑通的,当真是七上八下,海珠面上如火烧了一般,僵在原地无法动弹。
旁观的梁蕊摇了摇头,知她心思,便帮着除了少年的上衣,露出宽广而结实的深色胸膛。海珠在惊异男子的身体区别于自己的同时更惊异梁蕊能如此从容利落地脱去男子的衣服。
当梁蕊要去拉男子下装时,海珠似乎感觉到了有什么不妙之处,赶紧阻止,而自己却又愣在当场,不知如何是好。
梁蕊嗤嗤地笑着,帮着海珠轻轻地拥上了少年。
“怎样?”梁蕊问她。
“好硬,他的肉是石头么?要是打上两拳,疼的估计是我。”渐渐地海珠放了开来,不再紧张,也会开个小小的玩笑话。
“呵呵。”梁蕊一笑,随即发现了什么不对,狡黠又现于眉眼,一副隔岸观火的表情。
正自探索中的海珠忽然感觉身下一动,暗叫不妙,抬眼望去,却是撞上了少年朦胧不解的目光,海珠一时间只觉头皮发麻,愣在当场。
梁蕊轻踢了她一下,方才如梦初醒,丢下少年立起,面红耳赤,说不出的窘迫,恨不得挖个洞钻了进去。正想移步出去,却听那少年问道:“这是哪里?”
梁蕊回答道:“这儿是桂城凌秀千堤啊。”
少年一摇头,似要摇去迷糊,口中念叨:“凌秀千堤?”
梁蕊奇怪,问道:“怎么,你不记得了?”
“记得什么?”
“你不记得你昏迷前的事了吗?”
少年握拳拍了拍脑袋,随即低头沉思,口中呢喃:“昏迷前。”
良久,少年抬头看了两女一眼,竟含着泪花,忍不住呜咽起来。
海珠心中一紧,她所担心的还是发生了。她从小受到严格的礼法教育,隐约觉得自己千万不能被男人碰,不能被瞧去了肌肤,否则便算失了贞洁。她以为男子也是这般,刚才极强的好奇心战胜了自己的道德底线,本就自觉惭愧,现在见到少年委屈的样子,将心比心了一下,竟觉自己闯下大祸,懊悔万分。反倒不觉得自己衣着单薄,露出的肌肤恐怕比那少年还甚,也是她是主而少年是客,万万没有客欺主的道理。
海珠踌躇起来:“到底该道歉呢?还是该走呢?”她的一双纤脚没穿鞋子,此刻踱来踱去,就似踩在了针毡上。
她却不知少年思索回忆,想起昏迷前的种种遭遇,孤独和委屈渐渐涌上心头才至落泪。
梁蕊倒是猜得明白了些,端来准备好的药食与清水于少年,宽慰几句,亲切地问着少年昏迷前的经历。
少年思得一会,这种事情本不好意思说与素不相识的人听,但自己此刻已算是孤独一人,又受尽委屈,相识的人反倒比不上不相识的人,再一观自己的状况,像是承蒙了眼前两人搭救照顾一般,好感便油然而生,边吃边喝便把事情的经过完完整整的说了一遍。
这少年名叫夏宿,那一年他上幻剑山的时候才七岁……
南林有“三剑两刀一堤”的六合正宗,说的便是六个江湖正派。百年前这三剑却是还得加上一剑,当时的四大剑派:流零域,五行真观,明门和幻剑庄。四大剑派各持所长,彼此不分伯仲,却因百年前的“五骨元兵之变”波及南林,各派均有损伤,其中最严重的便是幻剑庄,整个庞大的山庄被毁得一空,只幸存了唯一的弟子。五骨之变后,那名弟子欲开山复兴,可百年来,幻剑一门终是人丁稀少,不复当年之盛。尽管如此,幻剑一门的真传还在,虽早被移除了四剑之列,却没有人敢小视。
幻剑山传至今日却是多散少聚,一班同辈师兄弟,一旦掌门易毕,其余落选之人大都离山而去,自谋生路。掌门关自元共收了五个弟子,大弟子马玄和二弟子马煌是两亲兄弟,三弟子张杰,四弟子是他的独生女关絮菲,五弟子就是夏宿了。
夏宿只记得他小时候住在一落大院子里,父亲是这间大院里的管家,却从没有见过母亲,父亲极其严厉,不让问。当他七岁那年便被送上了幻剑山,父亲亲自送他去,没有告别,没有不舍,只是一如既往的严厉,只是一个利落的转身,只是一个健壮如山的背影……
夏宿从小跟院里的武师习得些剑术,初时颇得师父关自元喜爱,也因为跟小师姐关絮菲年岁相仿,二人青梅竹马,出双入对,便更得师父师娘喜欢。幻剑门的剑术分为两派:重剑和气剑,相传练到极境,一可劈山斩岳,一可凭空御剑。只可惜神功经过世间劫难的遗漏,已不复相传。而两派的练法却又互相背离,万万不能集于一人之身,再加之这些年门派人丁稀少,掌门便多在门内找寻伴侣。关自元练的是重剑,而他的夫人方悦则是气剑的高手。关自元让女儿关絮菲练气剑,而让其余男弟子练重剑,目的自然是要从中挑出乘龙快婿和下一任的掌门。
夏宿本来占了极大的优势,只是几个师兄弟年岁都不大,懵懵懂懂,不知其中利害。等年纪稍长,练了更高境界的重剑,夏宿却一直停步不前,这才知道他体质特异,只能练些粗浅的基础内功。师父师娘虽然还是喜爱他,但和之前已经大大不同,关自元不再让他练剑,而是请了铸号的师父来教他铸剑,也做些日常的杂物。
夏宿和关絮菲长到了十八九岁,对于男女之事渐渐开始明白了些,关絮菲让他去向师父师母提亲,夏宿便去了。可那一心想振兴门邦的师父如何能够答允?便处处为难。夏宿不谙世事,不明其中诸多道理,关絮菲却机灵得多,帮他出谋划策。可女儿哪里斗得过经历丰富的爹娘,一来二去,自然落了下风。
说到这儿还好好的夏宿忽然摇头叹气,迟迟不语,海梁二女听了半截没听出个所以然来,只是急急催他快讲。夏宿喝了一口水,又是深叹一口,才续道……
那日师父用剑术为难他,说是接了十招便答应他。若不是出于无奈,关自元自然不会用徒儿心里最大的痛苦去刺激他。说也凑巧,自夏宿被安排做些杂物起,他下山采购,在山前小河的一处湾洼处认识了一位在此盖房捕鱼的老渔翁,总来这里买鱼,他见老人孤苦伶仃,便常送些靠自己讨价还价多买出来的好吃的给老渔翁。时间久了,两人成了老少朋友,老渔翁知道了几乎关于他的所有,而他却并不知道关于老渔翁的事……就在他和师父比剑的前几天,老人传他了几招怪异的剑法。老人叮嘱他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使出来。
关自元见徒儿爽快地就准备接他十招,略微诧异,但他自认只消半招便能将这先天不足的徒儿打得倒地不起,只是实在不忍心,便决定让他过了六七招再一举击倒。夏宿也知道他一招都接不了,可他却又从不会退却,说是硬着头皮上也未尝不可。只是刚一出手便知道师父是在故意让他,心中感激。可即便关自元让得明显,夏宿却还是接得颇为吃力。勉强接完了八招,夏宿已是气喘吁吁,站立不定,关自元一摇头,这一招便要令夏宿的希冀永远破灭。可他自认夏宿无论如何也不能抵挡的一招却被那小子用什么奇怪的招式接了下来,虽然这一招只有四五成的功力,但关自元对自己徒弟知根知底,从夏宿使的招式看来,也并非本门招式,九招未能击倒他,心中大怒,最后一招便使了十成的功力。夏宿情急当中情不自禁地使出了老渔翁教他的怪招,才记得误了老渔翁的叮嘱,但眼下师父狠命一招袭来,似是要自己死一般,心中大骇,便只能拿那怪招全力相挡,希望保住性命。
关自元十招去尽,却不见夏宿颓然倒地,只在那颤巍巍地笑,口中不断吐出鲜血,勉力地站直。怒气去了些的关自元才对自己第十招下的杀气有些懊悔,但见徒弟尽然挡住了,这是其他弟子万万不及的,而夏宿用得又非本门剑术,懊悔立去。虽然在场只他们两人,却也不好反悔比试之前的约定,口上答应着夏宿,心中一百个不愿意。
伤还未好的夏宿兴奋地去找关絮菲说事儿成了,两人欢呼雀跃,一同商量着如何筹备……
那天夜里,夏宿去见了关自元,说到之前他答应的一事。关自元没有立刻就许了,而是告诉夏宿说:“你师母犯了风寒,我正好煎了一副药给她。”夏宿一下就明白过来了师父要试试他的孝心,于是便恭恭敬敬地端药送了去。
他那师母方悦才三十七八的年纪,模样身段都保养得极好,如二十末上的少妇。那夜方悦房间的灯点得极柔,见得夏宿端来了汤药,慵慵懒懒地坐起,从素被中露出了平日夏宿从没见过的薄薄轻纱,下面是若隐若现的曼妙身姿。正处青春期的夏宿忽觉得一股热浪从脚底直冲脑门,冲得他面红耳赤,步履艰难地把药碗端得近了,竟洒出了些到手上,烫的差点拿捏不住。方悦让他先尝尝,看烫不烫,苦不苦。夏宿自然乖巧地喝了一口,又烫又苦又腥,如实报了,师母方悦却不喝,放在一边,让夏宿坐下,谈论些关于关絮飞。夏宿自然以为这事成功已八九不离十,便跟师母畅谈起来,到了后来,越说越高兴,仿佛眼前之人已从他的师母变成了丈母,再过得一会,夏宿已经高兴得晕晕的,丈母似乎又变成了关絮飞的摸样,再到后来,夏宿已然记不清了……
待夏宿被一声:“救命啊,来人啊!”惊醒之时,却发觉自己正压在衣衫不整的师母身上,而呼喊之人正是她的师母。夏宿只见师母惊恐万状的模样,知道自己闯了大祸,正不解之时,房门已经被人一脚踢开,随着一声清脆的:“娘亲!”,关絮飞首先提剑而入,紧接着是师父关自元和三位师兄,一见是夏宿,大伙儿都愣在门口,夏宿更是懵了,他脑子里一片空白,视线也渐渐模糊了。
他已经不记得关絮飞那恼怒不解的颤声责问:“为什么?为什么!”到底问了多少次,也不记得师父和师兄是怎么打他的,他只知道自己要被他们打死了,也合该被他们打死,只是至死也不会想明白自己到底为什么那么做。
他只记得他还没死,被放进了一个麻包里,全身都疼极了,泪水也不知流了多少,最后听得一声:“哼,师父宅心仁厚,饶你一命,以后你再不是幻剑山的人,滚!”,夏宿是爬出麻袋的,因为他的两只脚和一只手已经被打断了,而仅有的只够入门的幻剑山内功也已被废去。他只想活命,他没有其他的去处,他只知道在河湾低处有个认识的老渔翁。
他爬了一夜,天亮的时候终于爬到了老渔翁住的河湾,当他看到老渔翁向他走来时,便再也支持不住,昏死过去。之后再醒来,便是在凌秀千堤梁蕊和海珠的屋里。
整个过程夏宿讲的浅显而直接,他根本不会去考虑每件事的前因后果,就算是考虑了,大概也想不明白,就连师父师母间接的拒绝他都看不出来,所以便不会往深了去想。而说到亵渎师母一事之时,也没有任何的不好意思,因为夏宿觉得自己不可能做那样的事,语气中透露出了愤怒与不解。
海珠跟夏宿差不了多少,对于其中一些事情也是非常不解,自设问自回答几番发觉说不通后便开始安慰郁闷的夏宿。
梁蕊倒是明白得很,他知这其中的一些利害关系,更知道夏宿为什么会亵渎了他的师母,只是梁蕊还不便说,况且她也有一处不明白的地方。梁蕊把眼睛睁得又圆又大,凝着夏宿问道:“你真的不记得你怎么来这儿的吗?”
夏宿摇头。
海珠接问:“你也不记得你怎么救我们的了?”
夏宿一惊:“啊?我救了你们?”
梁蕊一点头。
夏宿只觉这件事无比荒唐,嗤地一笑:“怎么可能,我一个断手断脚的人,连只猫儿都怕打不赢……”夏宿的声音忽然断了,笑容也僵住了,因为他发现自己的四肢完好无比,而且活动自如,连一点疼痛都没有。
这会夏宿自己都觉得这件事很蹊跷了,便问二女事情的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