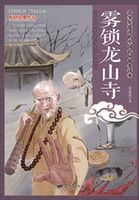以我的食指与它的碰触点为中心,金属面孔上的肌肤竟然泛起了一圈圈不可思议的涟漪。更难以置信的是,我的手正在逐渐地下沉。我完全感受不到已没入它体内的那部分肉体,仿佛已不再属于自己,而暂时还剩余在外的身体也正被一股巨大的引力凶猛地拉扯着。任何的震惊和恐惧在事后的回忆中,总是会被削弱的,或许这是人类大脑的一种自我保护模式,但每次当我重提到这个场面时,肢体就不禁颤抖起来,大颗大颗晶莹的汗珠接二连三地沿着额头、喉咙和侧腹下滑,犹如毛毛虫们拖着刺痒的尾巴在我身体上爬行。
我竭尽全力地挣扎,却宛若沼泽里的罹难者一样越陷越深。我试图放声呼喊求救,虽然明明知道附近不大可能有人(即使有,也很少会愚昧到像我这样自找麻烦的地步),但嘴巴只是徒劳地张翕着,嚷不出只言片语。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肉体一点点地消失,感觉自己就像是一只被人类剥去了头盖骨正津津有味地蚕食着的猴脑。只不过食客的匙子是从上而下:大脑皮层——胼胝体——松果体——四叠体——脑桥——延髓,我则是由某一只手开始。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被吞噬的肉体越来越多。我已感觉不到自己那颗由于惊恐而跳得快要蹦出胸腔的心脏,因为此刻我只剩下一个无助的头颅孤零零地晃动在冷酷的金属脸蛋儿上。风吹动它那一根根狰狞的发丝拂向我充满绝望神色的面孔,仿佛一尾尾凶猛地吐着黏稠信子的毒蛇。我们的嘴唇贴得很近,鼻子紧紧地挤在了一起,它的每圈眼眶里镶嵌着的只是一片淡红色的透明金属,散发着空洞而死寂的阴森。
用不着多久,我连视觉也消失了,只有眉毛以上的那一圈脑壳还呆在外面静候着被吞噬。什么都看不见、听不到、嗅不到、舔不了和摸不着而又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苟延残喘在一个完全无法扭转的绝境中。这种感觉不知道你是否能够理解,但它已超出了我的语言表达范围。我的大脑绝望地渴求着五感的回归,希望借此能平复汹涌澎湃地动荡着的混乱思绪中的冰山一角。但当它们真的重新降临的时候,我却发现自己身处一个更匪夷所思得令人不安的境地:明明已被彻底吸进了金属怪物的体内,眼前的一切却和外面的景致没多大区别,唯一不同之处在于——奄奄一息地躺在泥泞上的分明是一个人类。而他的累累伤痕却和我在金属怪物身上所看到的完全一模一样。
他的脸庞清秀,加上因大量失血而泛着苍白的色泽,凄美得动人心弦。嘴角悬挂着的微笑像枝梢上摇摇欲坠的枯叶般疲软无力地颤抖着,却有一种令你难以抗拒的催眠般的诡异。
“你好,我叫做明。”传统得几乎必然的开场白,虽然他的语气平淡,声音微弱,却又充盈着威严和让人不禁想要亲近的魔力。
“奘。”我试图冷静,不过,费了很大的劲才挤出这么一句简单的回答。明:“你的满腹疑惑和不安,是可以理解的。若然你需要我为此而向你道歉的话,我很乐意说上一句——对不起,给你添麻烦了。不过,我确实一直也没有打算要求你的任何帮助,因为我的伤势对于你们的医生来说,是没治的。”
我:“你是从EDEN来的吗?”虽然处于惊魂甫定的状态,而且素来没有听说过有任何人会从那个世界来或者能到那个世界去,但是将云洞现象和那只金属怪物连在一起看,就不难产生这种联想。
明:“是的。”
我:“那么,我们不如尝试一下联络那里的医生,或许还来得及。”SODOM的居民是无法估算出云层上的世界里的物事究竟优越到何等地步的,所以,我相信许多在这里难以办到的事,在EDEN来说,都是易如反掌的。
明:“我和你同样没有办法联络到上面的世界,除非管理这个宇宙的程序愿意。”这后半句简直就是废话,就像谁都知道你的老娘是女人一样。
明的眼神虽然泛着痛楚和疲惫,却有着难以置信的锐利,竟然轻易地看穿了我的所想。“你错了,它并不是你们以为的那样无所不能,而且,我的母亲也并非一个女人。”
这句话的确使我感到了诧异,不过今天遇到的怪事已经够多了,没有必要为区区一句话而大惊小怪,当务之急是如何才能救他。“那就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吗?”
明:“刚才没有,现在或许有了,而且正在进行中。”他正在做的只不过是和我聊天而已,难道说我的语言具备起死回生的威力?
明:“不,你甚至可以不用说话。我们的交谈只是起打发等待救援或者死亡的时间的作用而已。”虽然难以理解,但是他的镇定自若使我不得不相信这句话的真实性。
明:“我可以解释得清楚一些——你在外面的时候,无论干什么,都不可能对我有任何的帮助。我也没有料到你能进来。而当你进来了,用不着再干什么,我已有了一线生机。”
我:“还是没能弄明白自己到底对你有什么帮助。”
明:“掉下来的并不只有我一个。”
我:“你是说,在SOD0M里有从EDEN来的能治愈你的人?”明:“或许。但当你在外面的时候,是无法联络他们的。”他用手指了指周围:“因为我们是靠它来通讯的。之前它和我同样虚弱,无法运行。直到你进来,给它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从那一刻起,求助的信号已经发出去了。”我:“它是一种通讯工具?”明:“通讯是其中一项功能,并非最主要的。”我:“那它究竟是什么?”
明:“元神。它是EDEN里每一个社会成员与生俱来的如影随形的一种物事。”我:“你们那里每人都有一台?”明:“是的。不过我们通常使用‘只’作为它的量词,而且每一只都是不一样的。”我:“只只不同?”明:“不仅仅外貌,最重要的是每一只都具备一项特有的技能,称为——不二法门。”
明在继续关于元神的解释中涉及了许多EDEN特有的物事。我打算根据他的口述用自己的语言整理成一个易于你理解的介绍。
首先,我已经说过——我所处的宇宙最上面的是EDEN的地板。也就是说,云层在EDEN居民的头顶下,而地板则高高贴在他们的脚底上。所以,当我在描述EDEN的过程中使用“上下高低”这些词汇时,你或许会听得不太习惯。
EDEN的人类已不再和我们一样通过性交来繁殖。那里的婴儿是从一棵形态和你们地球上某种名为娑罗的常绿乔木差不多的而体积庞大的玩意儿上结出来的,他们管它叫生命树。婴儿挂于枝梢直到完全成熟后,才坠落到地面下。一个人步入老年,就必须跑回树底上去自我了断,充当肥料。以下这句是明的原话:“于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完全没有负担的社会里。”
还有一棵和生命树几乎一模一样的玩意儿,叫智慧树,不过它结出来的不是人类的婴儿,而是元神的雏娃。
每当生命树结一个婴儿,智慧树就出一只元神。这婴儿长大成人,相应的那只元神也同时亭亭玉立地落地。他成为老人到生命树上自尽时,他的元神也衰弱得非当智慧树的肥料不可了。
和元神相对应的人类也称为该元神的肉身。明的元神名为——BELIAL,那么,明就是BELIAL的肉身。肉身和他的元神的感觉是相连的,元神通常按其肉身所想来行动。
肉身可以进入它的泥垣宫里(就是我和明现在所处的地方)指挥它,也可以于其体外在一定的范围内操控它。明:“只有该元神的肉身才能驾驭它,所以BELIAL能将你带进来是在我意料之外的。看来,它打算让你成为新的肉身。以前,EDEN里的人类只有一种死亡形式——老了自杀。因为,那里已不再有任何的疾病。所以元神们都是随着各自的肉身的老化而逐渐趋向衰亡的。但这次我却是史无前例地身受重创,更换肉身后,它就会从破败不堪变作焕然一新了。
并不是任何一个人类都适合充当任何一只元神的肉身的,在EDEN的每一个人都只能驾驭与自己同时坠落到地面的那只元神。不过,既然你能进入BELIAL的泥垣宫,也就是说,你恰巧具备了做其肉身的资格。”
当元神处于物质状态的时候是半生物半机械体。它也能纯粹以能量的形式蛰伏在其肉身的脑海里。作为BELIAL的新肉身,我随时可以将它收进自己的头颅里。不过,现在我还不打算这么干,因为正依赖着它联络那些能够妙手回春的人们,而且呆在泥垣宫里,明的伤势也会比处于外面的恶劣环境中恶化得慢一些。
BELIAL的感觉已转作与新肉身连接,所以外界对明不存在任何的侵扰。在泥垣宫里,我接触到的景致还是那一片人迹罕至的湿软的洼地,而明却处于除了我和他自己之外再也没有任何物事的清幽中。
明:“元神随着肉身的衰亡而毁灭,在以前,肉身的更换是素未发生过的,但现在看来,只要在旧肉身死前找到健康的新的肉身,那么,该元神就能继续生存。所以,你进来了,就等于是对我最大的帮助,因为即使我真的不能获救,也已经没有什么遗憾了。”
我:“你真的认为元神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吗?”
明:“因为只要BELIAL还健在,它就能继续背负我尚未而即将实现的梦想。”现在回想起来,他的这句话未免显得有些狡猾,所谓BELIAL继续背负的,实际上就是硬往我这个新肉身的肩膀上塞了一个重担。不难看出,他就是为了那个梦想才会落得这般田地,所以我简直不敢想象作为一个接班人,自己会有什么样的下场。
写下这些你正在阅读的文字的时期的我,过着的就是一种小心翼翼地为了完成明的遗愿而疲于奔命的痛苦生活。城镇、村落、丛林、旷野……潜伏的危险无处不在,只要稍不留神,它们就会觑准时机,猛地扑出来,用寒光闪闪的尖爪锐牙将我撕碎嚼烂。
你或许会想知道——我从明的手中接过这个沉得要命的包袱后,第一次面对危险时是如何惊惶失措、手忙脚乱地侥幸逃脱;或者是我在至今为止所遭遇的最严峻的那场战役中是怎样费尽思量地化险为夷。可是,我可以老实地告诉你:暂时我还不打算告诉你这些。虽然,它们在我的记忆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要重新翻开这一幅幅布满了自己的斑斑血迹的残酷画面,却叫我不禁腻烦。最重要的是,这类事情若回顾得太多,恐怕自己会失去继续面对那些接踵而来的危险的勇气。不过,我也知道这是无法避免的,总有一天自己还是会原原本本地将它们记录下来。
现在,我要向你讲述的是明在云层上面的那个世界的某些经历。
不要以为它们是无关痛痒的,恰恰相反,这才是我所处的宇宙即将面临的一次惊天巨变的关键。
但在这之前,我还是得不厌其烦地再三提醒你:由于我即将诉说的事发生在EDEN,那和你们的地球是不一样的,所以,当你读到“上下高低”这些词汇时,请不要滞留在某种惯性的思维方式之中。
明大清早回到部里的第一件事,就是和同事们一起有条不紊地排列在大厅中高声唱颂赞美管理这个宇宙的伟大程序的动人诗篇。EDEN里所有的居民都有一份安稳的职业,而且获得的都是同等的工资,无论你在哪个部里的哪个课。大家平等地分工合作,没有上司和下属。所以,只需专心自己分内的工作,用不着像你们地球上的某些人那样为了往上爬而拼命地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他们甚至从不在部里和别人说上任何一句与工作无关的话语。
那个亭亭玉立在跟前背对着自己的有着美妙的声音和浓密的黑发的姑娘,明就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因为他们在工作上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虽然每个工作日之始明都必然在这里偷偷醉心其臀部的丰满与粉颈的细腻,平时他们也常会于走廊和食堂中不期而遇。
当歌颂的仪式完成后,明就得回到新闻课去展开他一天的工作。办公桌面下空空如也,明以双肘为支点,两条前臂向当中倾斜,十指交叉紧扣,再将鼻子搁在这个牢固的等边三角形的下面,承托起半个脑袋的重量,等待着下班时刻的降临。八小时以内,明偶尔也会改变一下姿势,那就是得去上厕所和吃午饭的时候。
明是唯一一个负责界内新闻的。EDEN里的居民们过着的是每天几乎一样的生活,不会发生什么意外,因为在元神的保护下是很难遭受不测的,只有别的元神的攻击才可能对一只元神造成伤害,从而危及肉身。不过,这个世界里素来没有过一丁点儿的暴力事件。他们时时刻刻在言谈举止甚至思想上循规蹈矩。
负责界外新闻的同事倒是多达五百七十二人,而且个个都忙得不可开交,因为另一个世界可不像这里一样太平。厚实的云层虽然阻隔了两个世界的通讯,EDEN上的人类却依然能洞悉下面所发生的一切,或许因为沙微前谷采集的不仅仅是资源,还有各式各样的情报。他们所看到的SODOM是这样的:贫乏,落后,野蛮,腥臭,放荡,血淋淋,物欲横流,饿殍枕藉,到处是毒品、娼妓和性病,人类相互强暴、残杀甚至烹煮的画面随时会跃入眼帘。不过,我由诞生至云洞现象之前,在SODOM里呆了这么久,别的不敢太肯定,人吃人的现象倒是一次也没有见过,后来有幸遇见的亦不多,当然,也很可能是由于自己素来孤陋寡闻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