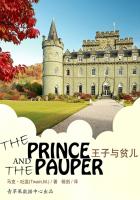我们出了竹林,沿着小路往山上走。她走路总低着头,像要从路上寻找到一些微小的不易察觉的细节。而我则时不时地抬头仰望,想看看那些绿树上面是否闪耀着金光——那些幽灵的眼睛。
山路上一片寂静,我们很少说话,也碰不到什么人。林子里不时传来砍柴的声音,却看不到一个人影。
正走着,草丛里突然腾地飞起两只黑色的大鸟,扑棱着翅膀,发出骇人的叫声。我们都吃了一惊,往发出响动的方向望去,那里一片空寂,鸟儿已幽灵般没了踪迹。
蝶若说:“小阿羊,要是我们真找到了那个山洞,见到了传说中的山鬼,你怕不怕?”
“有什么好怕的!山鬼又不会平白无故地吃人。”
“你说,这蓝山上到底有多少我们不知道、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
“你指哪些方面?”
“所有的。”
“那就不好说了。”我说,“蓝山这么大,离天那么近,谁知道山上除了树和草,鸟和兽,还有别的什么。”
“小阿羊,我相信蓝山上的确有山鬼,这个世界上也一定有幽灵。我以前是口信心不信,现在我是真信了,你呢?”
“我还是不确定。要是今天我们看见了我就信。”
“看不见你就不信吗?”
我不说话,只是微笑地点了点头,心中却有些犹疑。
蝶若笑了起来:“小阿羊,你这么说自己也会糊涂的。”
“可我觉得自己精明着呢。”
“你看,我们站在蓝山上,看到的只有树,根本看不见山下面的村子,也看不到村子里我们家的房子,更不消说人了,你能说他们不存在吗?”
我狡辩道:“想那么多干什么?做人的最高境界是‘难得糊涂’!”
“越扯越远了!”蝶若说。
我们继续往山上走,不知不觉已经快到山顶了。小路曲曲折折,坑坑洼洼,一直都是这样,两边的树木、茅草并没有因地势增高而有所变化。有时漏下天光,恍若星星一般,银白发亮,有时头顶都是密密匝匝的枝丫和叶子,透不过一丝风来。
路边的山坡上,草铺得很厚实,仿佛不是从土里长出来的,而是与山坡原本是一体的。我想,如果真像他们说的那样,当年蝶若的爸爸把土地爷的头扔在了山坡上,那说不定它现在还在哪一棵草下面呢。可是,这么茂密的草丛,哪里才是它的藏身之所?
蝶若说:“小阿羊,你听——”
“听什么?”我听到柴刀砍柴发出的声响,“每天都有人在蓝山上砍柴,这没什么奇怪的。”
“不是,你再听。”
我凝神谛听,像漆黑夜里的猫想要捕捉夜晚的细枝末节。
“你在说话?”
“不是不是,你注意听——咕咕,喔呜……听见了吗?好像是什么动物的叫声。”
“山鬼?”
“你听见了吗?”
“没有。”
“你再好好听听。”她认真得有些执著,“咕咕,喔呜呜……喵呜……”
若在别的时候,另外的场合,我可能会被她逗笑,但当时她那么投入,我只得同她一样,置身于她的视听之中。
确乎有别的声音隐隐约约地传来。是什么声音呢?像小孩的哭声,又像幼兽的啼叫,或者是鸟鸣。都有点像又都不像。
我说:“是野猫的叫声?”
“不像。”
“虫鸣?”
“不是,”蝶若挥了挥手,说,“好像是……”
“猫头鹰!”
“猫头鹰?”蝶若说,“你见过猫头鹰?我们这里有猫头鹰吗?我只在课本上看到过。”
“真的像是猫头鹰的叫声。”我说,“猫头鹰我见过几回,就在这蓝山上。”
“怎么发出这样古怪的叫声!”
“听大人们说,它是不祥之鸟。”
“可书上说它是益鸟!”
“科学知识并不能完全解释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现象。大人们说,猫头鹰是报丧的鸟。如果猫头鹰老是叫个不休,就说明有人要死了。”
“真的吗?”
“我妈说,我爷爷去世前的几天,蓝山上总是传来猫头鹰的叫声。有一天夜里,飞来一只大鸟,落在我家门口的桑树上,大家都没太在意,半夜时它叫了起来,声音很是吓人。我爷爷就是在那个夜晚离开的。我爷爷死后,那只猫头鹰就飞走了,蓝山上也消停了。家里人都说它替黑白无常勾走了爷爷的灵魂。”
“我从来没见过猫头鹰,以前也没听到过它的叫声。”
那声音越发地清晰了,渐渐变大,我们越往前走,就离它发出的声音越近。我确定无疑,这就是猫头鹰的叫声。它的声音比我以前听到的还要洪亮、还要有穿透力;比猫叫恐怖,比小孩的啼哭声粗犷。
我曾和几个伙伴到蓝山上掏鸟窝,捉一些羽毛漂亮的雏鸟。我们有一回就捉到只小猫头鹰,比小猫略大,浑身散发着臭气,但它的羽毛的确很好看。小猫头鹰并不叫,很安静很温顺。但当我们快到蓝山脚下时,蓝山上传来了大鸟的叫声,无比凄厉,像丢失了孩子的女人。我想它应该是在哭,边哭边叫着自己孩子的名字。手中的雏鸟听到妈妈的叫声,开始在我手里挣扎,张了张小嘴,发出和别的鸟儿一样的声音。
我说:“你想不想过去看看?要不我们循着声音去找找吧。”
我们几乎忘记了上蓝山的最初目的,而是被猫头鹰的叫声所吸引。蝶若跟在我的身后,脸上洋溢着兴奋的红光。这时,桀若的病给她带来的不快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她不再像个暮气沉沉的大龄女孩,而是恢复了活泼的天性,一举一动都和她本来的年岁正相吻合。
“猫头鹰啄人吗?”她问了个好笑的问题。
我说:“我只听说过猫头鹰勾魂,没听说过猫头鹰啄人。”往前走了几步,我又说:“我想,恐怕它是会啄人的,像所有的鸟一样,不过是在惹急了的时候。”
“书上说猫头鹰吃田鼠,它应该会啄田鼠吧?”
“那就好,我们都不是田鼠!”
我和她都笑了。在蓝山上,她的笑声像初生的春芽,新鲜,娇嫩。
我们离那个声音越来越近,它好像就在近旁的某棵树上,或者在芭茅丛中,可是,我们连只鸟儿的影子也没见到。猫头鹰躲到哪里去了?我们看不见它却听得到它的叫声。
“小阿羊,你快看!”我正在树与树的枝丫间找寻,这时蝶若压低了嗓门冲我喊了一声。
随着她手指的方向,我看到前面不远处的芭茅丛中,显现出一个洞口。洞口的枯树枝上,停着一只冷峻的猫头鹰。它看上去和一只成年的猫差不多,大小也不相上下。全身麻灰一片,夹杂着一些花白的斑点,两只眼睛十分犀利,像藏在身上的两把刀。
它和我们之间相隔不过五六米远。这大约是一只年老的猫头鹰,对周遭的事物显得有点淡漠。它对眼前的一切都视而不见,径自引吭高歌,颇有些孤独的气象。
“别再往前走了。”蝶若悄声说,“受到惊吓它就会飞走!”
“这么大的猫头鹰我还是头一回见。”我说。
“确实好大,和书上画的不一样,花头花脸,怪吓人的。”
它叫时一动不动,好像连嘴巴都没有张开似的,叫声从它的身体里扩散出来,在四周飘荡。
说它是不祥之鸟,并非全无道理。单单是这样的怪叫,已经足以让人毛骨悚然。恐怕只有寒夜里的鬼叫,才会这样阴气森森。幽灵和山鬼,在人们的心目当中,憎恨和讨厌的程度大约也要排在它的后头。
蝶若说:“它看上去像不像山鬼?”
“不知道,我没有见过山鬼,不知道它长什么模样。”
“我看差不多!”
“你见过山鬼?”
“没有。”
她轻轻地嘘了口气,额头上布满一层细细的汗珠。她拉着我的手,用力捏了捏。“太可怕了!”她说,“它真的是猫头鹰?”
“不是猫头鹰还能是什么?”
“我说它是山鬼,是幽灵,是恐怖的东西!”
情绪一上来,她说话的声音不觉提高了八度。那只大鸟受到惊扰,扑打着宽大的翅膀一飞而起,即刻便已消失不见。不知是躲到了幽深的丛林中,还是飞向了更远的地方。
蝶若突然紧紧抱住我,把头埋进我的怀中。她的手心全是汗水,凉凉的。过了好久,她还在不住地瑟瑟发抖。
我安慰她:“没事,蝶若!那只是一只鸟,它已经飞走了。”
“我总觉得它不像鸟。”她说。
“就是一只鸟,一只年老的猫头鹰。”
“我讨厌猫头鹰!”
她没有痛哭流涕,睫毛上却湿漉漉的,有些泪水凝结成细小的微粒,挂在上边。她当然害怕,从她脸上变幻不定的表情就看得出来,但她竭力克制着,不让自己哭出来。她是个倔强的女孩子,即使家中遭遇那样的不幸,她也很少哭哭啼啼。
当时,我们躲在屋后面看道士给桀若下阴时,她还那样大胆,那大胆中当然不乏好奇,可她毕竟不像别的同龄女孩,娇滴滴的,经受不住生活中些许的压力。
然而,我还是太粗心了。她趴在我怀中,起先还颤抖不已,后来就慢慢平静了。当我感到她在嘤嘤啜泣时,她早已哭成了个泪人儿。
“好蝶若,你别哭了!”我不会哄女孩子,但眼见她哭成这样,只得设法去哄她。
她哭着嘟哝:“都怪你!带我来看什么山鬼!”
“怪我怪我,都怪我。”
“也不能怪你。”过了一会儿,她停止抽泣,眼泪还挂在脸上。“要怪只能怪那只猫头鹰。”
我给她擦干了眼泪,用一只手搂着她。我本来已经很瘦了,但怀里的蝶若比我更瘦弱,让我心中顿时生出无限的怜爱之意。
“那是个山洞吗?”蝶若问我。她指着刚才那只猫头鹰停歇过的地方。
“好像是。”
“莫非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山洞?”
“不知道,我想没有那么巧吧!”
“管它是不是,”蝶若皱着眉,“是也好不是也罢,我都不想一探究竟了。再说,就算我们证实了蓝山上的确有山鬼和幽灵,又能如何?我们又治不好桀若的病!”
“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就是啊。”
她离开我的怀中,那一种幸福的温暖与柔软的感觉依然还在,令我回味无穷。
“小阿羊,我们不要寻找了,什么也不要找了。”她抬起头望了望星空,星空却被树叶遮挡住了。“我们回去吧”,她说。
我也望了望天空,试图穿透绿色的华盖,看到一些闪闪烁烁的东西,然而,什么也没有。“天就要黑了。”蝶若说。
是啊,天就要黑了,我们该离开蓝山了。夜晚的蓝山自有它的诡异,蝶若的爸爸已经领教过了。人们在天黑之前回家,正如天将亮时,幽灵要躲开天光,寻找自己的藏身之所一样。再过些时候,幽灵就该出来活动了。山下的桀若,是不是又要同幽灵说话了,看似一个人自娱自乐,眉开眼笑?
我这样想的时候,蝶若已经拉住了我的手往山下走去。她走在前面,另一只手不时地拨开挡在路上的枝枝丫丫。
我们走到那条小路上没多久,碰到了一个下山的村民。
他走在我们前面,背着一大捆干柴,弄得哗啦哗啦动静很大。柴刀别在他的腰上,走路时刀把与木柴的一端相互撞击,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我们一前一后地跟在他后头,静静地没有说话,脚下步履轻盈,几乎没有声响。
走了一会儿,前面的人突然停了下来,大声嚷道:“哪个跟在我后头?鬼鬼祟祟的!”
蝶若和我都没有回答,而是朝他走了过去。
他把柴靠路边放下来,舒展了一下筋骨。
“原来是你们两个。你们跑到蓝山上来做什么?”
我认出了他,他是住在村东口的单身汉。平日里没有几个人同他搭讪,其实他是一个喜爱唱歌、说话风趣的人。
蝶若走在我前边,她向那个人打了声招呼,叫了他一声“伯伯”。
“小阿羊,是你带蝶若到山上来的?”他朝我挤挤眼,一脸坏笑,“老实讲,你是出于什么居心?”
“我有什么居心?我们就是去山上玩耍了一会儿。”
“蓝山上有什么好耍的?哦,对了,树林中还是很幽静的。”
“那又如何?”
“如何?你问我如何,我倒想问你!你以为我不知道,别看你人小,其实心里头鬼精鬼精的。”
蝶若说:“你莫乱说,小阿羊是好人。”
“他是好人?总有一天,你会知道他到底是不是好人。”
“哪一天?”蝶若问。
“哪一天?”他不说了,只是怪声怪气地笑。
后来,他不笑了,换了一副正经的样子问蝶若:“你们究竟上蓝山做什么去了?天快黑了,你们就不怕碰到怪物!”
“我们去寻找一个山洞。”蝶若说,“蓝山上能有什么怪物?”
“蓝山上的怪物多得很,到处都是。你说的是什么山洞?”
“村里的人都在疯传,说这蓝山上有个很深的山洞。洞里有尊土地神,还有一个山鬼。”
“听谁说的?”他不屑地说,“简直胡说八道!”
他说,蓝山上的山洞确实很多,都是七十年代人工挖凿的,但从没听说过哪个洞里有山鬼。他每天上山打柴,也从来没碰见过山鬼。他还说,当年上蓝山放牛的人当中也有他,他们一大帮小孩子喜欢钻洞子玩,大约钻了二十来个,但每一个洞里都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连只耗子或蛤蟆都很少见。至于说蝶若爸爸在洞里见到了山鬼,把土地爷脑袋扔进茅草里的事,更是子虚乌有。
最后,他问道:“你们见到山鬼了吗?”
蝶若摇摇头。我说:“我们什么也没见到,只看到一只猫头鹰。哦,对了,还有你。”
“猫头鹰?什么猫头鹰?”
“就是报丧鸟。”
“你们看到了报丧鸟?完了完了,你们的家人要倒霉了!”
“什么意思?”蝶若问。
“你们不知道?谁见到了报丧鸟,谁家就有人要升天了!”他的眉宇间变得模糊起来,“唉,轮到谁就是谁,躲不过的,这是天命。若说不是,我天天在蓝山上,怎么从没见到过报丧鸟?不仅没见过,就连它的叫声都没听到过。”
蝶若说:“你说的可是真的?”
“你若信就是真的。”
蝶若双手按着胸脯,面色苍白。她用牙齿紧紧咬着嘴唇,她的嘴唇发青发白,失掉了原先的血色。
我说:“蝶若,别信他,他在瞎说。”
蝶若不说话,丝毫不理会我,我真担心她那样会把嘴唇咬破。
“怎么说话呢,小阿羊!”那人一点不通情理,“我讲的可都是实话,全是老祖宗传授下来的经验。”
“我们走吧,蝶若。”我懒得理他,拉起蝶若就走,“我们快些离开这里,回家或者去竹林中的小木屋。”
“没用的,小阿羊,除非你把那只鸟收拾了,否则灾难迟早都会发生。”单身汉说,“你们可是实实在在地撞上了。”
“你何必这样咄咄逼人!”
我拉着蝶若,一路小跑,好像不是要逃离蓝山,而是要躲避一场生死厄运。虽然我们已经气喘吁吁地跑到了蓝山脚下,但始终觉得那个人的影子和声音一直尾随着我们,鬼魅一般,难以驱散。
我真怕再听到任何鸟儿的叫声,更怕那嘈杂的鸣叫中,夹杂着一两声猫头鹰的叫声。
蝶若颤颤巍巍地说:“小阿羊,我害怕!”
我紧握着她的双手,说:“别怕,蝶若。这些都是假的,什么也没有。幽灵、山鬼、大鸟,还有那些传言,没有一样是真实的,全都是假的。”